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呈现了十分迥异的“人性图景”,这被称作“斯密的两张面孔”,也是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斯密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认识的亚当·斯密,很可能是那个写作《国富论》的、远近闻名的经济学家,他推崇开明的利己主义(self-interested individ⁃uals)、对自由市场和“看不见的手”极为执着,提倡政府越小越好、人类追求“自利”的行为终将引向公共福祉(common good)。然而,在晚近几十年的斯密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目光转向曾受忽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甚至于有学者主张,《国富论》只是《道德情操论》的理论延伸。这一研究趋势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学界长期对斯密怀有的片面印象。
“经济人”是斯密经济学体系中的人性假设——个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关注“自利”,借此促进分工从而实现国民财富增长(人性完全是自利的)。“道德人”是斯密伦理学体系中的人性假设——将“同情”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基础的情感主义(人有不可化约的道德冲动)。“道德人”(homo moralis)和“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呈现着相互冲突的人性观。
斯密的“经济人”,单看上去是致力于市场经济与国民财富研究的人性假设,但其“背后还有一个极为体系化的理论底色和规划草图,那就是道德情感论”。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her)教授认为:“从‘道德人’到‘经济人’是(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如此,便是从斯密思想的整体[1]哲学视角,以充足的文本解读和多维度的引证深入斯密的思想世界,重释《国富论》的真义和现实观照。
一、斯密与中国
20世纪初,斯密的《国富论》经由严复译作《原富》引入中国(约1901—1902年),开始了其在中国的思想之旅,冥冥中连接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和中国启蒙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斯密出版《道德情操论》(1759年)的十余年后,其名震学界的《国富论》才得以现世。而在国内,《道德情操论》首个中译本(1997年)的诞生相比《原富》却将近晚了一个世纪。到上世纪末,中国经济获得一定发展后,斯密那本论述“道德情感”(moral sentiments)的著作才逐渐受到国人的广泛关注,这是与英国本土恰恰相反的接受过程。如果说严复的启蒙主义是对晚清“世变之亟”的回应,涌动着国族救亡与富强的危机意识,那么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仍需继续“启蒙”,回到“本真”的斯密。
二、“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共融
“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位社会科学家”——这是Fleischacher教授审视与澄清斯密思想的关键。一方面,斯密将“自利的追求隐含着公共福祉”统一于“希望他人尊敬认同自己”,“自利”隐含着善待他人的道德观念(二者统一)。另一方面,斯密在运用自身道德哲学引领我们与他人同情共感时,为哲学理论如何能够指导科学研究提供了绝佳典范:通过转向社会科学,揭开人类生活的细节,而不仅仅依靠哲学的抽象。
第一,澄清斯密在经济领域中呈现的“自利”。“诸多宣称斯密所支持的‘自利’,控制着所有人类关系这一理念,是对《国富论》的严重误读”。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斯密思想深受道德情感主义支持者哈奇森、休谟的影响;二是斯密明确反驳过以霍布斯、曼德维尔为代表的“人类动机自利中心论”;三是斯密思想的“道德人”与“经济人”能够互相支持。
在斯密看来,良好的社会人际关系通常都是基于私利的(self-in⁃terest),因而能得以长久,这种“自利”是弱意义上的而非强意义上的自利自私。“贫穷可以(也往往)是一种恶”,“道德人”追求物质财富的“自利”是合理而有益的,人们为“改善自身境况”而寻求必需品(维持生存并符合相应习俗之“体面”),可以“与朋友欢聚与慷慨相待”,从诗歌、音乐、戏剧等作品中获得道德陶冶,甚至其它无甚价值的某些欲望“即便不值得过度追求,但也无需躲避”。
更为直接的佐证是,斯密在《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都曾将曼德维尔那种“蜜蜂王国”式的利己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斯密的“自利”并非那种夸大个人利益追逐的人性预设,而是更关注在利益追逐中感受与诉诸他人的能力。结合斯密在《法理学讲义》中的内容,这种“自利”基于“交换”和“契约”(试图说服对方),从而促进共同追逐相似目标的结果。因此自利容许合作,这种合作“既是自然的,也同时是我们自身利益所要求的”。
第二,澄清斯密道德哲学中的“同情”。斯密道德哲学的主旨就在于关注“How can we make moral judgement?”——我们如何做道德判断、分辨是非善恶。他的回答是,同情是人的社会化的心理机制,通过想象中他者的“旁观者”视角(impartial spectator)而为道德提供普遍性基础。而道德发展即是人们将这一旁观者视角内化,而逐渐获得两种德性:一为自制克己的德性(缓和自然反应),一为亲和的德性(体恤并敏于他人感受)。
道德发展的这一过程,“将自己的社会化概念与每个个体的绝对重要性,以及每个个体独自抉择的能力融合在了一起”。这包含必不可少的教育,即长久的文学的与想象的训练培养,置身训练情感的具体语境,在此,行为者收到某些情感反馈,见证并努力模仿道德楷模,而绝非接受明白无误的指令或牢记某些哲学原则、教条。
三、情感力量解救理性的软弱
卡尔维诺这样定义“经典”:“经典就是每次重读的时候,都像是初读带来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一本重温的书。”斯密思想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哲学解读视角下,我们渐渐发现,亚当·斯密并非那个冷酷的利益追求者,也非高高在上的道德立法者,而是一位敏锐而温情的、充满现实关怀的道德科学家。斯密思想启发着当下的我们,去审视现代社会技术化与形式化的理性思维,去关注个体自由与社会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
相比斯密重视(经验的)想象胜过(先验的)理解。两个世纪后的边沁与康德建构起的抽象道德原则和结论,似乎更显得有悖于情理或反直觉。这些道德和政治哲学更关心正确原则的形成,而非这些原则如何合理地应用于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世界。“情感制造了思想的峰峦,形塑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景观”(Martha Nuss⁃buam)。在斯密的语境中,道德情感(尤其是同情及其容受性(recep⁃tivity))作为人性的一种现实可能的能力要素,激励并强化人类行为的动机,从而支撑往往显得有限和软弱的实践理性,这种提醒愈发重要。
斯密在其道德哲学中赋予了文学以极为突出的地位,调动人们结合自身经历发挥想象将自己投射到经济交往的各个参与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国富论》中遍布的过目不忘符合直觉的小故事,便旨在于某些方面拓宽我们的道德想象能力。
另外,斯密召唤我们从哲学体系返回到常识,为普通大众的判断辩护。“个人利益的最好裁决者是个人自身”(individual better judge of its own interest than any statement or lawgiver.),警惕哲学家和决策者企图用知识分子“发明”的所谓更好的“体系”代替这种判断,克服常见的对普罗大众与底层劳动者的偏见和傲慢。
不专注于个人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要么虚幻,要么虚伪。当代伦理学教授 Michael Slote 指出,“道德情感是一种公共的社会性情感,人类天生的移情能力(empathy)是道德宇宙的粘合剂”。除了具备普遍性的“理性”之立法,我们仍有望借助于情感的仁爱、共感与同情,以跨越自我与他者(不同个体,甚至多元文化)的壁垒,更多地将目光转向普通大众,转向共同生活的人类同胞。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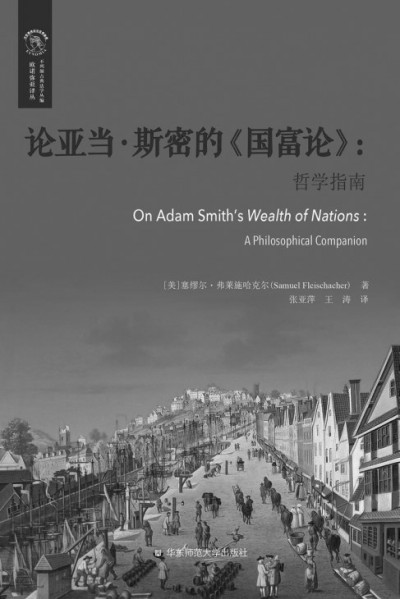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