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诗经典,除了被列入各种必读书目、常常是“提及多于读过”的大家专集外,还要算上那些篇帙不大但内容精省、世代相沿袭而广泛流传的蒙学作品。比起前者,这些作品往往面目平易,立论温和,虽少见谠言高论,也难说引领了什么风气,却能经受住时间的洗礼,于彼时有益初学,到今天则承续传统,体现古人日用而不察、习见而相忘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书今天来读,不仅门槛低、易进入,也更能保存古人趣味。把清人蘅塘退士孙洙编的《唐诗三百首》称为经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不过要理解它的“经典性”,至少需回答两个疑问:为什么是它而非别的选本能风靡二百多年,经久不衰? 少刷一条视频、多读其中的一首诗,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何意义? 想必这也是在消遣手段层出不穷的当下,还敢以“经典”自居的作品需直面的核心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周兴陆教授的新著《〈唐诗三百首〉通识》,就从该书的编选旨趣、所呈现的唐代精神风貌、作品的格律体制、艺术特征和海外传播等几方面提要钩玄,于娓娓道来的轻快笔调中,做出了系统而切当的回答,进而赋予唐诗以强烈的生活实感。
在卡尔维诺看来,经典背后拖着历史的尾巴。《唐诗三百首》也不例外。自有唐诗以降,历代选本迭出,编选者或出于文献保存的目的笼括一代之作,或为了张扬一己趣味随性裁汰,自作揄扬。到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颁布功令改革科举,于乡会试中加试五言八韵律诗一首。此令一出,学习作诗一时成为“刚需”,坊间遂出现大量唐诗蒙学读本。七年后,曾主持乡试的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出版,也是时风使然。不过此书虽服务初学,却并未像《唐人试帖》《唐人试律说》《全唐试律类笺》《试帖最豁解》一类应试指导书那样专选排律,而是秉持“备众体而通一体”的诗学传统,在广泛借鉴前代选本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温柔敦厚”的主流旨趣确定选篇,因而入选的作品趣味醇正,且各体大致均衡,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唐诗的面貌,最终超越其他选本,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对此周老师有一个精妙的比喻:“这三百余首作品是从近五万首唐诗中经历了一轮一轮选拔而最终胜出的。就像选拔运动员一样,经过县、市、省级层层淘汰,孙洙挑选出这三百多首建立了国家队。”所以说,它“体现了唐诗的特征,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乃至“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学相媲美都毫不逊色”(第221页)。并非过誉,因为如果给一个想了解唐诗,乃至中国古典诗歌的“小白”推荐一部入门作品,最合适的可能还是《唐诗三百首》。
但好归好,对生活方式与古人大相径庭、处境早已发生根本变化的今人来说,《唐诗三百首》有非读不可的理由吗? 在书中,周老师以切己的心得告诉我们,熟悉了古人语境后,这些作品也可让今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联想自己的遭际,融合当下生活,以丰富情感体验。像白居易的绝句《问刘十九》,写雪天以“红泥小火炉”招友人饮酒,本是常人常事,但“一经诗人点化,便亲切温馨,诗味盎然,意趣无穷,真是 日 常 生 活的审 美化”(第15页)。三言两语,从平淡庸常中提炼诗意,已开宋人先声。又如岑参的《寄左省杜拾遗》头四句“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薇。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读来典重,实则就是说“每天随例上朝‘打卡’,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第20页),说得直观而熨帖。再如宋之问《渡汉江》“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一句,因是被贬后逃归,“越临近家乡,心里越是羞怯”,不仅担心“如何面对家人”,更是害怕“家里情况怎么样? 会不会有不好的消息啊? 越是焦急越是不敢问。就像在外读书的学生,一听到家里打来的电话铃声就紧张,总是担心家里发生什么不好的事”(第67页),便将宦游置换成今天的常见遭遇,字里行间饱含在外游子的辛酸。除了情感体验,古人心中还萦绕着一些永恒的烦恼,如孟浩然“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写的是“一个拷问灵魂的人生问题:人如何能超越死亡的有限而走向永恒呢?”对今人而言,思来想去,也许“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第50页)依然是最能撑起这个问题的答案。
从情感体验和思想叩问层面为唐诗注入生活实感,正是《〈唐诗三百首〉通识》用心之所在。其实对清人而言,唐诗同样是“古诗”,但就像金圣叹说的,“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无外乎传达一己心思。类似说法书中多见引用。周老师之所以特别拈出,想必就是要强调“唐诗抒情的妙处是,既能说出其心中之所诚然者,又能说出人心中之所同然者;出于个人诚实的怀抱,又能道出天下人普遍的心声”(第44页),而心声历代累积,便融汇在前人对一首首诗的阅读与理解过程中。所以对后人来说,唐诗不仅能缘情,更能体道,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认识图景,“唐诗修正了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语言,中国文人感悟世界、认识人生、联络情感、表达自我,都受到唐诗的影响”(第219页)。如果套用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说法,则唐诗无疑是语言中最精美的庇护所。书中第三部分《〈唐诗三百首〉的艺术世界》从“抒怀序志”“亲情友谊”“田园山水”“烽火闺情”“佳偶姝丽”“物候节令”“咏史怀古”“丝管丹青”等几方面疏源导流,既揭示唐诗在古典诗学情感类型表达中的独特意义,也很好地回答了当下为什么仍要读: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传统的延续,之所以仍能不经意间被《唐诗三百首》中的精言美语击中,是汉语的维系,让我们和古人的认识方式始终保持着内在一致性。
这些精义的抉发,离不开周老师长期治古典诗学的深厚学殖与独特感会。这一方面体现在对不同诗体的语言特征与创作规则的熟稔把握。对此,书中除了有《唐诗的体裁与近体诗的格律》一章作专门介绍,于具体的作品鉴赏中亦时有体现。如孟浩然《留别王维》首句是“寂寂竟何待”,尾联又说“只应守寂寞”,按后来的作诗规则看,“寂寂”与“寂寞”句意与字面皆重复,是犯了“侵复”的毛病。对此周老师将语言与诗意融为一贯,指出“失望,落寞,真是一副悻悻而归的可怜相,连‘寂寂’‘寂寞’有重字都顾不上了”(第49页),既说出了唐诗对规则的讲求“大体则有,定体则无”(第215页),尺度相对活泛,不像后人总结的那样严苛,又点破此诗故意露拙,但恰好与主旨相契合,达到了“反常合道”的特殊效果。又如岑参《逢入京使》:“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书中如此解读:“应该是先在马上逢入京使,然后东望故园,再流泪。现在倒过来写,这叫逆挽法。这样显得突兀不凡,不至于平直。”(第67页)其中“逆挽法”是清人总结出来的章法规则:“所谓逆挽者,倒扑本题,先入正位,叙现在事,写当下景,而后转溯从前,追述以往,以反衬相形,因不用平笔顺拖,而用逆笔倒挽,故名。”(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说的是清楚,但有点复杂,而周老师以之解诗,既彰显岑参构思的妙处,又简洁明了地说明何为“逆挽”,可谓两相得宜。
另一方面,周老师在整体把握传统诗学演进规律的基础上,于不经意间做出了颇具卓识的“大判断”。如古人注重亲情友谊,但在诗歌中“抒写兄弟间亲情和朋友间慰勉的诗歌相对较多;抒写父母与子女间情感的诗歌,特别是对父亲写的诗歌,相对要少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有重家庭伦理的传统,“对严父慈母的敬畏抑制了才思,诗人是不敢在父母面前逞才的”,而说到这里又话锋一转,“或者说这种血脉亲情超越一切语言”(第65页)。仔细想想,两种分析不仅都于理可通,而且深入思想的内里,并能从“中国人比较含蓄,不善于表达父子、母子的亲情。在诗歌里,这样的亲情往往被泛化为一种怀乡之思”(第66页)找到印证,可谓发人深省的得间之论。
由此看来,有关诗歌经典化的重要话题,以及读诗对当下的意义,书中基本都涉及了,并且点化生新,颇多“大判断”与“小结果”。相信读者阅后,能在纷扰嘈杂的当下离传统更近一点。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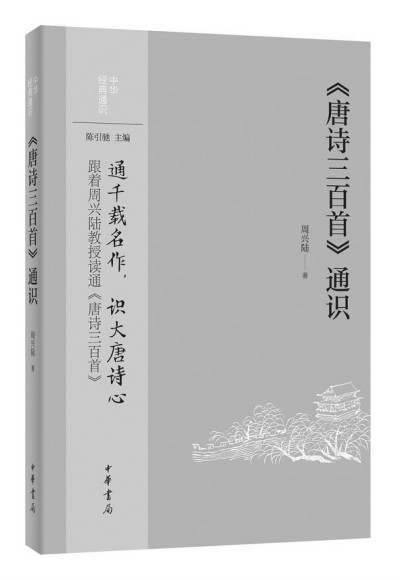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