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却走上清史研究的道路,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读书过程?
卜键:我在上世纪80年代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先后在中国戏曲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中国文化报》等处工作,2010年被调到国家清史办。起初我很不情愿,但随着大量的阅读补课,对清代的了解逐步加深,渐渐沉浸其中并找到乐趣。个人的看法是:工作单位的转换大多身不由己,会影响到阅读,而阅读也会让你安于乃至爱上新的岗位。
由于要参与清史项目管理和审稿,兼任《边政志》主持人,必须要看相关的档案文献,逼着你往纵深走。这种阅读不无被动与功利,却十分有效。我也发现以研究和写作引领阅读,是一种有目标也有压力的读书法,与宽泛松散的阅读不太一样,对于学者应该是常态吧。
您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又有宽泛的阅读基础,对于清史的阅读和研究是不是比较自如?
卜键:不自如。经常读得头晕脑涨,但是不厌倦,常会有所发现。记得入中戏读研未久,祝肇年先生就提醒我搞个小本子,阅读时随笔记录一些好词和妙语,并要保持对于语词的敏感性。那时的我算是用功的学生,整天在图书馆泡着,中戏位于棉花胡同,距离首都图书馆(国子监)、北图古籍部(柏林寺)、中科院图书馆(灯市东口)、北图善本部(北海)都很近,骑车皆在15分钟左右,且闭馆日错开。中戏的图书馆则开到晚十点。负责借阅的老师大多喜欢刻苦的读者,我永远记得北图的郑培珍大姐,见中午我就拿个馒头干啃,悄悄替我买了内部食堂饭票,也允许我待在阅览室内看书。就是在善本室,我检读万历刻本《北宫词纪》,发现卷首龙洞山农序钤有两枚印章,“弱侯”“大史氏”,顿时眼睛一亮。因为对《西厢记》版本的研究很热门,其中“龙洞山农序本”很重要,却不知为何人。经过考证,可知其就是万历间状元、大理学家焦竑(字弱侯,做过翰林院修撰)。我把这个发现写成一文投给《文学遗产》,很快获得刊载,解决了当年《西厢记》版本研究中的一个小缺环。
阅读中凡有大小触动,我会立即记下来,择时再深入挖掘。古人犹如今人,多数并不呆板,情感充沛,充满智慧,要善于捕捉。
您先后出版过《李开先传略》《明世宗传》《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清风之华:王杰与乾嘉两朝政治》《嘉靖皇帝传》等传记,写作的动因是什么?
卜键:各有各的动因吧。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李开先的。他做到了吏部文选司郎中(负责高官任用的司长),突然被免职,回家后写了著名的《宝剑记》。前辈学者如社科院吴晓铃先生、杭州大学徐朔方先生,也包括我,都认为他是最有可能的《金瓶梅》作者。为了搞清背景,我曾一页页从头到尾地翻阅《明世宗实录》,下了大功夫,对这个历来评价不好的皇帝产生较深的了解,同情之理解,写了《嘉靖皇帝传》,后应人民出版社之约修订扩充为《明世宗传》。纳博科夫说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重写也有近似之义。经过重新修订,今年又出版了《嘉靖:一个帝王为何会厌惧皇宫》(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又下了将近半年的修订功夫。
写作《国之大臣》比较晚。2014年,好友惠西平(时任陕西人民出版社社长)托我约两位清史专家,写写陕西清代历史人物王杰和王鼎,一个生活在乾嘉年间,一个在嘉道年间,皆位至内阁大学士,清正立朝。我找传记组组长潘振平询问,居然没人了解。我有些好奇,就去翻阅相关资料,首先被王鼎的气节所打动,深深感动。王鼎是一个被长期遮蔽的爱国英雄,为保护因抗英革职流放的林则徐,他在往河南督办河工时,向皇上建议让林则徐协助,得到批准,而在黄河决口合龙后,道光帝仍将林则徐流放新疆。他在给林则徐送行之际老泪纵横,回京后激切上言,不为采纳,便在军机处以死谏诤,是谓尸谏。记述王鼎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是对儒家思想精义的再领悟,我写得很投入。写《国之大臣》的两年,也是我学习清史、研修清朝政治文化的愉悦时光。而为枢阁大臣作传,必然要涉及朝政大端,不吃透很难落笔。
另一部《清风之华:王杰与乾嘉两朝政治》,今年始得写完出版,着重点则有些不同。王杰与王鼎都以忠清正直立世,品节英挺,吏事练达,也都有几分老陕的执拗,但没有这样激烈。王杰性格沉静内敛,但坦诚真纯,心地洁净,极为清廉,长期担任礼部尚书、乡会试主考官,四个儿子中连一个举人都没有,不许他们挤占科举名额。其次子学问甚好,气不过父亲的阻拦去西安参试,王杰写信给陕西巡抚,声称如果取中我先弹劾你。乾隆喜欢他的清素品性,虽有和珅多次进谗,而信赖不变;嘉庆对王杰更是敬为师长,王杰离京时,嘉庆赠诗“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
这两部作品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如高阳、二月河等,您对他们的历史小说也有研究吧? 创作中您对清史细节的把握有什么原则? 学者的写作和作家相比,是否更严谨一些?
卜键:我读过他们的作品,比较起来更喜欢高阳一些。学者和作家的历史写作,一个非虚构一个虚构,比较甚难,严谨的标准也不同。个人检讨治史之弊,当在于空疏,缺少细节,缺少场景,缺少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挖掘。其实历史曾是活色生香的日常,很多史实一经掘发,生动细节就会自然显现。如禅让期间的嘉庆帝颙琰,很多书写他在上皇跟前的小心谨畏,写和珅挑拨其父子关系,而读和珅与福长安在子皇后大丧期间的两份奏折,全是在说颙琰如何敬爱父皇,如何恪守礼数,如何克制悲伤关注国事,这才是真实的和中堂。
我发现您的作品都非常生动有趣,充满想象力,甚至富有悬念,文学性很强。
卜键:写学术文章和著作一定要枯燥无味吗? 早些年我写过很多学术文章,像《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屡予刊载。现在自认为境界又有些提升,但编辑的回复是,文章很生动,但与本刊风格不吻合,也有的称是外审说的。难道要把所有文章都定成一种风格吗? 难道学院派就是模式化套路化和艰涩呆滞吗? 不以为病,反以自傲,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当过高校老师、从事过出版、在艺术研究院供过职,经历过的这些职业对您有什么影响?
卜键: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我并未停止过阅读和写作。很敬佩那些长期在一个领域深耕的学者,但自己不是,多年来兴趣一直在游移,阅读和写作都跟着兴趣走,跟着感觉走,像学术圈里的游击队。但是跟着兴趣走,经常会充满新鲜感,充满读和写的激情,应也大致不差吧。
《库页岛往事》也是跟着感觉走的收获吗?
卜键:《库页岛往事》是一个意外,当然也算跟着感觉走的收获。那是在2015年夏天,我开始为退休做准备,将一部分书运往远郊的房子,多年垫底的旧书被翻出来,其中就有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萨哈林即库页岛),见妻子读得入神,我也拿过来翻翻,一下子就沉浸其中。契诃夫往库页岛时刚30岁,已经声名大起,却选择逃避浮华,跨越两万里艰难路程来到这个恶名远扬的苦役岛。他在岛上待了三个月,由北而南,走访监牢和强制移民,写成这样一本苦难之书。库页岛曾长期归属中国,可不管明朝还是清朝,极少有官员登临,文人墨客更没有一个人去过,不能不为之深感羞愧。我是带着这份愧疚写的,基调不是谴责,主要是反省。历史的路是一步步过来的,也是由众多个体行为汇成的,应该在梳理时有代入感。有人说历史书写要求客观,当然没错,但不够全面。钱穆先生曾说,一个人要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充满温情。
您如何理解钱穆所说的“温情”?
卜键:钱穆提出的温情说,发自内心,震耳欲聋。如果你细读过儒家经典,就会带着感情来看待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史。清朝不是汉族政权,可从康熙、雍正到乾隆,都热爱读书,熟悉儒家文化,精擅书法,不仅题写诗文,还酌加小序和评点。他们在宫中园中遍设书屋,享受阅读的愉悦,也与臣下探讨学问,这不就是温情吗?
乾隆登基的时候,见督抚常指责某官书生气太重,为此专发长篇谕旨,说我从五岁读书,也是一个书生,如果大臣都是书生,按照儒家经典的要求善待百姓,廉洁奉公,国家不就好了吗? 他也批驳那些嘲笑书气之议,曰:“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他的话中也是满含温情。
您有一读再读的书吗? 经常重温的是哪些书?
卜键:特别喜欢鲁迅,喜欢他的文字,那种精深和犀利,读时痛快淋漓,自己的写作风格也受到影响。过去流行鲁迅的单行本,薄薄一册,颇便携带,看得眉飞色舞。后来条件好了,两处房子里都有他的全集。鲁迅是小说家兼学者,今天的王蒙也是,个人认为他俩都属于天才,小说写得好,搞研究也是好手。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略同,少年时所受教育不完整,知识不系统,是以一直希望能抽空重读经典。就像《史记》,我曾翻阅过,也反复读过一些章节,但没能通读和精读;《资治通鉴》也没通读过,还有《淮南子》《水经注》等,都很想细读,期待将手头的写作告一段落,静下心来补课。
如果有机会见到作家或学者,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卜键:就说已故的吧。我非常怀念冯其庸先生。他是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也是恩师。读硕时,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业师祝肇年先生让我去送硕士论文,未在,就请院办转交。有一天我正在院图书馆看书,管理员说有位老先生要见你,居然是冯先生。先生时已过六十,先一层层找到我在四楼的宿舍,又跑到图书馆来找。中戏的院子很小,我们就在球场边谈了一个多小时,先生给予我很多鼓励。论文答辩结束时,先生问论文在哪里发表,说这篇论文很完整,不要拆开发表。后来他把近四万字的论文荐给一家刊物发表,并让《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感念刻骨。先生退休后住通县张家湾,我过一段就会去看他,说说近期的阅读和写作,他听完会帮着分析,话语直截,有鼓励也有批评。现在没有这样的待遇了。
我还很怀念一位台湾学者,戏曲研究的大家、“中研院”曾永义院士。曾先生学问渊博,坚守华夏道统,有风骨才情,也极为用功,可谓著述等身。他热衷于架设两岸人文交流的桥梁,在世时每年都要举办戏曲研究和创作的活动,也频频到大陆讲学和参会,古道热肠,特别愿意帮助年轻人,将我视为忘年交。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卜键:《红楼梦》吧,我在红楼梦所待的时间较长,读了很多遍;到清史中心后,便会从大清史的角度,再作凝视。近年来虽集中读史,但也每年给《红楼梦学刊》写一篇文章。去年写《冷笑的资格》,今年又写了《黛玉的冷笑》。黛玉本是书中最喜欢冷笑的,而在三十六回后,却再不冷笑了,即使别人怼她也不回敬了,有意思吧?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有三册,我想就带这三本吧,会永远读下去。如果能再选一本的话,自然要带一本野外生存的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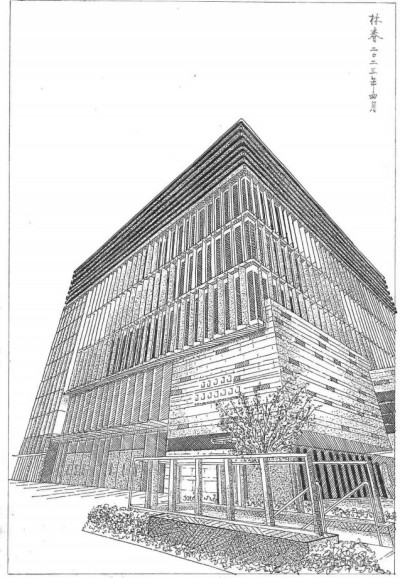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