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
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与社会板荡交相呼应的是思想巨变,曾被誉为“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的《论语》,在步入20世纪后备受争议、数度沉浮:“20世纪的革命运动和现代化变革,给孔子和儒学的命运带来了根本的变化。”
1905年废除科举后,《论语》开始跌落“神坛”;新文化运动中,最为冲决罗网的声音当属“打倒孔家店”;20世纪中叶以后的数十年间,孔子一度被视为负面典型;改革开放以来,对《论语》的评价和认识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回首百年,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而“这一时期的《论语》诠释最值得人们注意,研究这一时期的《论语》学有着特别的意义”。刘伟教授所著的《20世纪〈论语〉诠释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即是一部聚焦变革世纪、董理诠释脉络的最新力作。
一
《研究》主脑明晰,述作相彰。与单纯重视文本编定、审音释字、注疏流衍的考据性工作不同,《研究》明确将现代“《论语》学”的核心概括为“义理阐发”。当然,后者也不能罔顾前者,须是在理解文义的基础上,分析其间所存的思想意趣与哲学洞见。要之,惟求训诂,难窥全豹;只取义理,无征不信:故合则两美,分则俱伤。
有鉴于此,《研究》所论既有“六经注我”式的典籍,如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树达《论语疏证》等;也有“我注六经”式的专著,像赵纪彬《论语新探》等。而当具体到专书辨析时,尤其是面对偏重“汉学”的著作时,《研究》往往有意选取“融会汉宋”“阐发己见”“开创新制”等角度予以评述,继而凸显“义理阐发”的主脑地位。
如,《论语集注补正述疏》虽承乾嘉余绪,《研究》却言其有志沟通汉宋,广征博引往往是发挥义理的手段与方式。再如,《论语疏证》因“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而蜚声于世,《研究》不落窠臼,独辟蹊径,以“理性判断,阐发己意”褒举此书;并结合《子罕》首章,揭橥“经史互动”的方法如何为《论语》学创辟“新途径”。
当然,现代《论语》学的重点虽在“义理诠释”,却不可因此设限,故步自封;就其外延来看,还包括《论语》的编者考订、成书断代、版本勾陈、注译传播等问题,涉及“哲学史、经学史、经济史、伦理史、教育史、文化史、历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校雠学等多门学科”。故《研究》于评述前贤成果外,特设“《论语》文本编撰讨论”“孔门‘四科’意蕴探析”“《论语》中的祭祀与身份认同”三章。
三章之间交相阐发,层层展开。《研究》在文本编撰一章中详细讨论了《尧曰》的篇旨与结构,以期运用“宋学”的思理解决“汉学”的困境,既富创新性,也有说服力。从“学以成人”(《学而》)到“学以成圣”(《尧曰》)的孔门宗旨,经《研究》点出后,为进一步探析“四科”意蕴与理解祭祀活动奠定了方向。质言之,上述三章在总结百年间训释、解说、发挥《论语》之作的基础上,深挖精研文本诠释与义理建构之间的连动关系,探绎儒学(乃至中国文化)实践理性的精神所系。
二
《研究》思接百载,贯通点线。《研究》以《论语》学为总纲,将20世纪分为“清末至民国时期”“新中国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期”三大阶段;并于每个阶段内,先就其时代背景、基本情况、总体特色进行概述,再选取重要典籍,分别予以个案分析。系统呈现出20世纪《论语》诠释的整体风貌与衍化谱系。
就“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期”而言,经由拨乱反正,传统文化有所复兴;但此间又有微妙不同,可以1990年“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为界:此前一段,虽已逐步走出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阴影,但《论语》研究依然处于边缘地带,“对儒家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的处理,仍很流行”;而后一时期,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否具有普遍性等一系列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论语今读》一书应运而生。
《论语今读》曾将整部《论语》乃至儒学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半宗教、半哲学”,并不无遗憾地指出,“我认为是真正的关键和研究的起点所在,但在今日中国学术界却很少被注意或强调”。《研究》为补此缺,多所着墨,一方面把“半哲学”与“如何做”(how to)、“一种生活方式”做通贯性理解,明确实用理性的哲学品格既非柏拉图式的理念追求,也非黑格尔式的逻辑建构;另一方面,又将“半宗教”进一步凝练为“生之所依”与“死之所归”,继而从“塑造群体心理”“规范群体行为”“给人终极关怀”三个维度回应了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可见,《论语》并非“于当世之利害,钱谷兵刑之实物,默然置之度外”,讲明义理的根本目的是修己安人。
三
《研究》平情理解,守正创新。人文著作往往受到学术环境、政治立场、写作目的等相关因素影响,不免留下时代的烙印;《研究》于此类作品并未采取抽象否定的态度,而是深入肌理、详辨瑕玉。如,《论语新探》常因其政治挂帅,被视为“迎合某种反革命政治需要而歪曲和践踏阶级分析方法的铁证”;《研究》却未人云亦云,实事求是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扎实文献工夫有机结合”是《论语新探》的一大亮点。
与此同时,《研究》对港台地区的《论语》学研究,亦不因其立场有别而掠人之美;相反还从“研究过程的一贯性”“研究主体的多样性”“学术研究的主导性”等方面,进一步肯定其所具优势。从《论语文解》(1918年)到《论语要略》(1925年)再到《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从《依〈论语〉论孔学》(1956年)到《论语新解》(1963年)再到《孔子与论语》(1974年),钱穆先生关于《论语》的一系列相关著作,正是前述优势的具体表征。
其中,《论语新解》一书,以“突出义理,兼顾考据和辞章”与“摒弃门户,融会汉学和宋学”的特质,堪称港台地区《论语》学的典范之作。此书虽对儒家文化饱含温情与敬意,却把“性”“天”“理”等一切先验维度与形上探求,置于视域之外。《研究》将其归因为“受到清代朴学以及近代西学等当时学术背景的影响”。
四
百年回眸,非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旨在“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与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方法论上或许可变“接着讲”为“重新讲”。“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具体到现代《论语》学的研究上,须在“兼采汉宋”的基础上“会通中西”。“我们期待把孔子和儒家的问题放进古老文明现代发展的纵深视野,置诸全球化的现实处境,以理论思考与实践关怀相结合的态度,把这一问题的思考推进到一个更深入的水平”,从而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当然,所谓的“自主”与“创新”,不是目空一切、自我欣赏;恰恰相反,需要注重历史与理论的回环互动:“哲学的发展既关乎观念层面的流变,需要反思中西哲学历史的变迁过程,也应站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之中,正视时代所提出的政治、科学等不同领域的问题,并对此作出深层的回应。”要之,以历史筑牢底气,用思想挺立骨气,是拜读《研究》后最为深刻的印象。
(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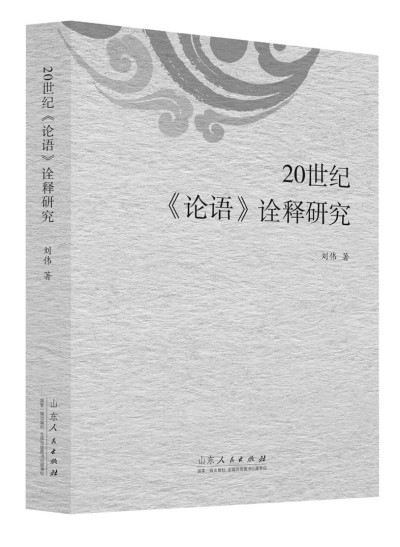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