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在其代表作《菊与刀》中写道:“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弄清楚,日本政府对日本人民能指望些什么? 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吕万和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页)对于西方尚且如此,对于和日本仅咫尺相隔的我们,考察研究东瀛情况更是极为必要的了。日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应如何进行观察与研究? 它能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哪些经验与教训? 可以说,这正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反复探索的重要命题。
近日问世的《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一书,覆盖1898—2022年的时段,详细记录了百余年来以南开学人为代表的我国知识分子如何观察日本、研究日本的历史足迹,为读者展现了我国日本研究发展的真实历程。该书包含八大部分(卷一至卷七及附录)。其中卷一至卷六,利用多方渠道广泛收集而来的资料、史料,按时间顺序对南开的日本研究历程做了全面的呈现;卷七是有关南开日本研究的各类统计数据;附录则是刘岳兵教授往年所做相关论说和报告的合集,不仅总结了南开日本研究长期以来各项工作的宝贵经验,亦提出了值得深思的真知灼见。
一
据《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所录资料载,1898年5月,年仅22岁的张伯苓作为北洋水师的一员,随同政府官员前往山东,参与回收甲午战争期间被日本军队占据的威海卫基地。转天不久,该基地却又依据《中英议租威海卫专约》移交到了英军手中。亲眼目睹了祖国土地短时间内的三次易帜,张伯苓心里很不好受,倍感屈辱,感慨“海军救不了中国”,遂立下了以教育挽救国运,“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3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153页)的雄心壮志。这可以说是其日后创办南开大学的初心之所在。
同年秋,张伯苓便受聘于当时积极倡导新式教育的严修家馆,负责英文、数学、理化等西学科目,并在此后的清末新政与留日热潮下,和严修等人多次前往日本考察,积极吸取东瀛经验以策划新式学校的创建。这虽然还谈不上是“研究日本”,但却是南开与日本发生联系的历史开端(《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第714页)。
据称在访日期间,他们曾前往各所学校参观,亦曾与井上哲次郎、穗积八束等日方知名文人相会交流。尤其在拜访日本维新功勋大隈重信时留下过如下一番记录。
余(严修)问:“人言,智日进则德日退,然乎?”(日人作此论者甚多。)伯(大隈)曰:“是大不然。是固兼进无退之理。”与余私意极合。一美国新闻记者在坐,与伯问 答,一日本人译之。余问唐君(唐秀丰),所言伊何? 唐君言,但闻记者问:“日本之文明但取诸欧美乎,抑兼用本国乎?”伯曰:“取人之文明则己之文明自进。”其言简括、得体。
此段记录显然说明,张、严等人并不赞同当时国内流行的“智进德退”“见利忘义”之论,而是坚定地认为惟有取外国之长才可能真正实现振兴教育、挽救国运的目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理念,1904年10月在严馆的基础之上,私立中学堂得以创建。翌年,私立中学堂改称私立敬业中学堂,进而在两年后迁入天津南开洼新址,又复更名为南开中学堂(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10卷附编,第14页)。是为南开大学前身。
尽管在筹建之初对日本经验借鉴较多,但此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的步伐日益加快,张、严等人开始在对日认识上逐渐迎来较为显著的转变。譬如,1908年严修致信钱少云时曾谓:“日人在关东,全力趋于实利主义,其下流社会,吮膏吸髓,如蝇如蚁无论矣,即公所谓上等社会能顾大体者,其处心积虑,亦何尝有异于是。”(严修:《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第209—210页)而此后经过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4年日军侵占胶东半岛、1915年“对华二十一条”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认识变得更为坚定起来:“坚韧不拔,百折不回,悠悠苍天,终必偿汝,国威以振,国耻以雪,诸生勉之,予日望之。”(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1卷,第22—23页)由此看来,南开大学在正式创立之前,其忧国忧民、奋发图强、教育救国的特质业已充分呈现了出来。这亦如刘岳兵教授所指出的,他们当时的“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有着鲜明的目的性,这个目的,大而言之就是为了爱国和救国”(《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第720页)。
二
1919年2月10日,在张伯苓、严修的主持之下,“私立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14日的学期始业式上,张伯苓发表演讲:“办学校须有宗旨,亦犹盖房者,心中须先有草图,用何器具,得何成效。先时尊君尊孔等,后来全个仿日本,均非其道。……知乎此,然后再定教育宗旨,是以教育宗旨不可仿造,当本其国情而定。”(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1卷,第109—110页)即在当时的时局背景下,基于对日本更为冷静清醒的认识,决意依据中国自身的国情走出一条全新的教育之路来,以实现为国为民乃至“为万世开太平”之根本目的。
而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或者更准确地说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了其频繁使用的“反面教材”。因为南开大学“就是在五四运动的声浪中酝酿诞生的”,她“创建于国难之中,其目的在于‘育才救国’”(《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第746页)。关于此点,《编年》中收录了大量实例。例如在建校伊始的《南开日刊》中曾有多文载曰:“(日本)得陇望蜀,识见狭小,愈起邻人之怨。外交手段,实为可耻。以高丽之小,防备之周,而独立之声忽起。况堂堂中华,果同心共济,起而与之抵抗,奚难哉! 奚难哉! 东邻人曷速猛省。”显然,南开师生从一开始便对自身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有着清楚的认识,其爱国之情空前高涨。然而此后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仅没有任何收敛,反而由于中方的积极抵抗与华盛顿体制的持续打压而不断增多增强。
“七七事变”爆发之初,张伯苓便代表南开学人做过明确的表态:“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3卷,第26页)正是基于这一态度,南开大学和女子师范学院、北洋工学院、华北工业学院等各校学生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了六十余个抗日团体以御敌卫国。于是,7月28日前后在华北发动全面总攻的日军便将南开视为抗日基地,对其校园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与炮击,尤其派出第六飞行队以“九二式五十千瓦弹”实施了轮番轰炸。当时的惨状,正如书中所记:“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第173页)
而为了保留抗战余力,南开大学先迁至长沙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于1938年移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抗战栋梁之才。
三
经过长达八年血雨腥风的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在1945年8月迎来了抗战的全面胜利。翌年,重回旧址得以复校的南开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张伯苓出任校长。据载,在10月17日举行的复员后第一次开学典礼上,秘书长黄钰生向全体师生做了表态:“南开大学被敌人毁得最早、毁得最惨。敌人投降了,南开大学复校,我们并不以复仇教学生。消极的,我们要使中国不必再有抗战;积极的,我们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以学术促进世界的和平。”(黄钰生:《黄钰生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86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南开大学于1952年遵照中央指示完成了院系的大规模调整重构。那一时期,南开的历史学研究、日本史研究方面涌现出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质量很高的科研成果。譬如,时任科研委员会副主席兼科研处副处长的吴廷璆先生,就曾于1955年《南开大学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第211页),代表着当时我国日本史学界研究的最高水准。吴先生在文中熟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方法,深入剖析论证了日本飞鸟时代(593—710年)、奈良时代(710—794年)、平安时代(794—1192年)社会性质的变迁问题,即:“大化改新以前日 本社会既非单纯的氏族社会,也不是奴隶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大化改新本身是一种政治变革。……平安时代庄园经济发达,国家为保证税收,便用法令将农民紧紧缚在土地上,逃到庄园里的农民也失去了自由。自由农民变为农奴,正是斯大林用以和‘封建前期’区别的封建制度的标志。……由此可知,农奴制度下的奈良平安时代是不能认为奴隶社会的。”
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卓越的成绩,同时得益于上级领导部门的经费支持和人员充实,南开大学于1964年3月召开校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扩大会议时讨论通过了成立五个研究外国机构的决议。其中之一便是由吴廷璆先生担任主任,俞辛焞、米庆余、王敦书三位先生为核心成员的日本史研究室(《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第211页)。该室不仅在此后的数十年间继续研究、发表了数量浩繁的学术成果,而且还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进一步加速并扩大了与日本学界的交流合作,从而夯实了南开大学作为我国日本史研究重镇的地位。
四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界研究又有了更为迅猛且空前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南开大学一方面扮演了领军式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亦发挥人才蓄水池的作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才俊。此时,“主任”的接力棒已从吴廷璆先生交到了俞辛焞先生手中。
俞先生是我导师熊沛彪先生的导师,故论起来是我“师爷”。俞先生当时除了处理日常行政工作并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兄弟院校、日本各高校的交流合作之外,亦撰写出版过大量极具影响力的重要学术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99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专著”(《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第275页)。
以吴廷璆、俞辛焞等先生为首的南开日本研究学人曾与来访的早稻田大学学术访问团展开积极交流,共同研讨并谴责了当时日 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史实的错误。他们站在学界的立场表态指出:“自从一八七四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台湾以来,无所不用其极,直到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日 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和残暴,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事实。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不但使中国人民、亚洲人民遭到了极大的牺牲,而且日本人民也遭受了许多灾难。这绝不是日本文部省少数人可以抹杀的。”(《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第242页)
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日本研究的规模,1988年4、5月间,南开大学又以日本史研究室为基础,联合校内其他系所相关教师组建了日本研究中心,由俞先生担任主任、吴先生担任顾问。该中心在1996年由杨栋梁先生担当“主任”后,又于2003年扩大成为日本研究院,先后经历了杨栋梁、李卓、宋志勇、刘岳兵四任院长,如今正由刘岳兵院长主持各项工作。可以说,在历届主任、院长的引领之下,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工作在最近几十年里迎来了欣欣向荣、不断攀高的盛况。
五
最后,谨以《南开日本研究史料纪事编年》一书中的各类记录为基础,对南开大学百余年来研究日本的历史足迹做一简要总结。
南开的日本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几大历史时期。第一期为1898—1918年:该时期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以后不断走向深渊,面对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因而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张伯苓、严修等老一辈教育家怀抱着救亡图存的伟大志向,开始广泛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为日后南开大学的创建开展了一系列积极的活动。第二期为1919—1948年:正是在张、严等教育家的主导之下,南开大学于1919年2月 10日正式创建。然而在随后的近三十年间,中华民族却依然面临着更大、更严峻的挑战,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所以南开学人自然会将日本作为“反面教材”,把批判战争、反对侵略、御敌卫国作为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的核心内容。第三期为1949—1977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南开大学秉持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从教育救国迈向了教育强国的新征途。尤其是与日本相关的研究,开始熟练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理论方法,对日本史的各个历史时期展开了客观严谨的实证性考察与理论性分析,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第四期为1978—2022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学术环境有了极大改善,新角度、新主题以及运用新掘史料展开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而在这一宏观动向之中,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在国内始终占据着代表性的地位,发挥了领军性的作用。
正如本文开篇所言,观察并研究近邻日本对于我国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课题,而如何反思过去、面对现在、展望未来则是研究的重中之重。无论从何种角度切入日 本研究,无论开展何种主题的日本研究,承继并发展以往救国、强国的基本思想与学术传统,时刻保持与时俱进的姿态,都应为我们时刻所铭记。而这,正是南开日本研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今年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成立2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我作为中国日本研究学术共同体之一员的一份祝贺之情。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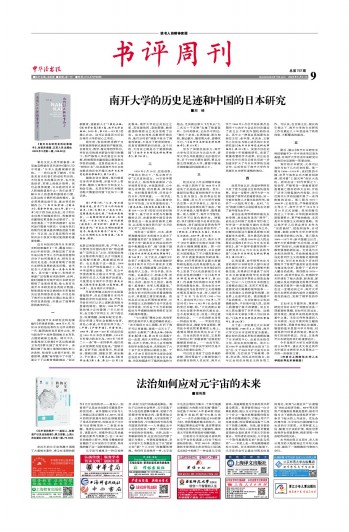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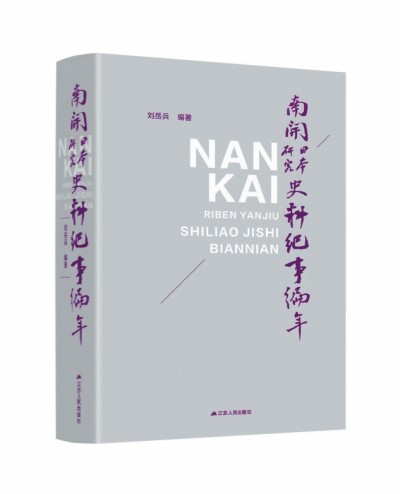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