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飞
区域国别学是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文等进行全面研究,通过融合文学、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形成关于区域、国家和全球问题的系统认知和知识指引,最早可追溯到西方殖民主义时代。二战后,随着世界格局的重新建立,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了对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形成了现在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是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为满足对外交往中的现实需求,对域外知识的一种常识性探究和知识体系的构建。
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纪60年代。出于新中国外交的需要,早期在大学和政府部门成立了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主要从事翻译等相关工作。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了专门的区域国别研究所,将研究范畴扩展至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外交等多个学科领域。而后,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联系的不断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1年,教育部启动区域国别研究专项,截至目前已在全国180多所高校设立了400多个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基本实现了对世界各地区和国家的覆盖。
纵观国内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区域国别学的产生和发展及时反映了时代的战略需求,推动了国家的战略发展,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与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也亟需区域国别学为我国深入了解世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保障。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公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区域国别学增列为新的一级交叉学科,标志着新学科发展阶段的开始,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开始由传统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特色研究生项目、特色研究平台等向科学、系统的大学学科专业,构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发展转型。
什么是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可以从以下几个背景和角度思考和解读这个问题。
一是全球性和平衡性。长期以来,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在学科发展上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局面。近年来,新兴国家作为研究的“客体”转变成为研究的“主体”。中国就是新兴国家的典型代表,同时经历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强国的民族复兴与大国崛起之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区域国别研究力量的兴起,将会给区域国别研究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更丰富的学科内涵,让学科发展具有更强的全球性和平衡性。
二是交叉性和融合性。长期以来,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都注重交叉与融入。事实上,这只是在一个主要学科问题上融入了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然而,因为不同学科中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学术范式不同,所以很难实现顺畅的学术对话,并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国家把区域国别学设为一级学科,就是要实现更高层面的大交叉、大融合和大升华。
三是创新性和包容性。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必然要推动学科创新。区域国别学要在一级学科的高度上进一步发展,关键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出发,从全球高度来看待区域国别问题,从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广泛联系、平等交往和深度融合来建立学科知识体系,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研究范式,注重底层方法上的融通与创新。
当前,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应当是对国家、区域的系统了解与全球视野的有机结合。在解决地区、国家问题的同时,要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地球村”中,所有的发展问题和治理问题,都需要区域国别知识,而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全球性的视野和工具。没有深入、全面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全球治理研究,就不可能获得更多的理性认知,也就不能实现全球性的有效合作。为此,我们需要解决学术的“孤岛化”问题,提升服务国家和世界的能力。当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区域国别研究都受到学科和地域的限制,需要克服“学科孤岛”“地域孤岛”“认知孤岛”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发展,难以实现真正的交叉融合、协同创新,难以及时有效地回应国家、世界和时代的重大需求,难以解决重大需求与零散、破碎的知识供给之间的矛盾,导致区域国别研究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推动了学科深度交叉,实现区域国别研究在理论、方法、数据、议题等方面的融合,形成共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需要重视全球参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从学科发展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由被研究的对象转变为研究者和贡献者。因此,区域国别研究应当以“多视角、全覆盖、共参与”为己任,充分体现世界各国学者的观点,尤其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供支持,促进学界的平等交流。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需要在具体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体现全球视野,需要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协作;同样,中国自身的区域国别学在理论、实践等层面,要兼顾世界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经验,并体现其世界意义。
在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诞生一周年之际,《区域国别学:全球视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杨丹主编)应运而生。这是一本从全球、中国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的视角,审视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文集。过去几十年,北外开设了101种外语、4个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37个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3个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中心、23所海外孔子学院,区域国别研究的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当前,北外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不再采用“拼盘式”的学科拼接,厘清相关学科与区域国别学间的内在逻辑,打通学科底层逻辑,实现了独特的“熔炉式”学科融合和交叉创新发展。
2022年4月,北外成立的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CCAS)以学者、学科、学术为核心,汇聚了来自181个国家、使用100多种语言、涉及多个领域的优秀学者,促进全球学者共同协作,推动全球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学术创新,回应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促进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的发展。《区域国别学:全球视野》这一文集正是北外学者与国内外学术界在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CCAS)建设过程中,携手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而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
如果说,殖民时期西方世界的“东方学”是当代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前身,那么,当下中国学者们想要构建的“区域国别学”绝不是21世纪东方的“西方学”。“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地道出了文明发展的逻辑链。“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兼收并蓄的态度,才能带来共同进步。建立交叉融合学科体系,尊重文明多样性,跨越文化交往的藩篱,增进不同国家与区域间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积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国际合作搭建新平台,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本文集中传达出来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目标宗旨以及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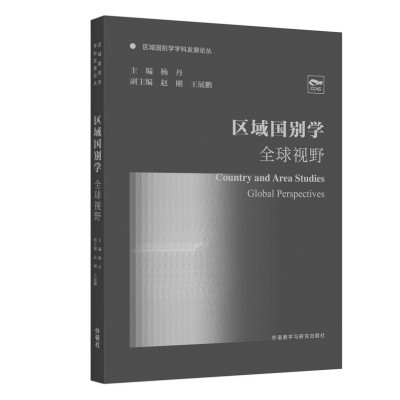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