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深怀一颗悲悯心、寻根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间成长环境做回溯,对川北乡村的时代命运、川北少年的生命抗争做了如实的呈现。
张国龙新作《瓦屋山桑》,首发于2022年6月的《人民文学》儿童文学专号。儿童小说首登《人民文学》的数量,还是屈指可数的。这部小说延续了张国龙“铁桥李花”系列的人物与故事,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川北乡村少年米铁桥、米李花和他的小伙伴们的生存境遇、求学经历,致力于描绘直面苦难的真实成长、时代变迁中的乡村新貌,也讴歌了默默陪伴在少年们身边的一人一物、一花一木、山峦河流、乡村新貌,讴歌了乡间少年身上所体现的坚韧成长与生命力量。
《瓦屋山桑》仍然是发生在麻柳溪边、一个为生活所困的家庭的故事。山乡少年米铁桥家正在面临的冲突,源自米铁桥的妹妹米李花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初中,铁桥想说服爷爷供李花读初中。作品开篇的时代背景,有着属于那个年代的典型性,偏远、贫困乡村的凋敝,艰辛的田间劳作,衰老的劳动力,外出的务工潮,留守儿童,失学问题,也有着属于米铁桥家的现实问题——外出打工的父母失联三年,家里盖新房欠了外债;哥哥米铁桥和妹妹米李花与年长的爷爷相依为命,读高中的铁桥选择辍学,回家劳作。但这个故事较之前作,又有明显的差异。随着时代的推移,这部作品的背景已然来到新世纪以来十余年间。巨大的生活矛盾与压力的化解,已经不单单是乡亲邻里间的温暖互助,更有了来自外环境的、时代变迁的巨大“怀抱”。
张国龙是一位深耕少年成长小说创作多年的作家,如他的“梧桐街·暖涩系列”少年小说,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凸显了消弭“代沟”的语言风格,是生动的“青春期”心态描摹与深刻的成人反思。创作《瓦屋山桑》,或者说在写作“铁桥李花”系列时,作家的文笔风格,显见地呈现了与之前作品不同的创作基调与语言风格。
作家深怀一颗悲悯心、寻根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乡间成长环境做回溯,对川北乡村的时代命运、川北少年的生命抗争做了如实的呈现。因而,作品选择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作家的叙事基本遵循生活流,呈现了浓郁的写实风格和返璞归真的创作意愿。
这部作品的成长书写,也着意呈现了一种挣扎状态的“成长”。十五六岁的少年,所承受的生活压力,所面临的艰难抉择,远远超出许多成人。即便身陷困境,但作品中并没有人为制造的矛盾,没有刻意陷入绝境的煽情,也没有绝处逢生的戏剧性,而是完全遵从了生活与时代的推动。
作品取多线叙事,不但描绘了米铁桥一家,还同时勾勒了乡间人物群像,描绘了他们的困境与选择。铁桥的几位同学如康正康,一样因为上不起学,休学一年,最先走出乡村,去深圳打工挣学费;一向老实听话的陈和平,先跟着舅舅学理发,但学艺无成,最终也选择离家,外出打工;张云蛟,家庭相对较好,爸爸转正当上公办教师,他也参加高考,考上了大专;李花的同学付晓珍,也是爸爸妈妈外出打工的家庭,但条件相对较好,父母能时不时给家里寄钱,但完全无法尽到陪伴引导孩子成长的义务。迷惘地撞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在老师的帮助下平安度过。
作家的叙事,虽然可以归为一种“苦难叙事”,却于苦难中孕育着饱满的阳光与希望。作品对爷爷与少年的乡间劳作,有多段写实性的描绘,包括妹妹李花,也在为这个家庭拼尽全力。苦难实实在在潜藏在文字间,作家还原了其间的艰辛,但又以小小收获的欢乐心情冲淡它。
一众少年都在追梦,都在不断学习克服困难,并不断克服困难,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打拼。对铁桥的未来,作家用了这样一句话,“打起十二分精神,迎接扑朔迷离的未来”。而在这个未来,时代张开了明朗的怀抱,给了铁桥“继续往前走的勇气”。作品里简笔描绘了乡村的时代新变,成为作品中苦难生活中的光亮。乡村的生活,在铁桥眼里,是满满的希望,是村里通上电了,能看电视了,是家里打了机井,用水不愁了,是火车轨道铺进了村,公路也逐渐通了。这个生活段落的尾声处,村里通电,有了广播员的需要,村里修路,有了劳动力需要,村里还缺基层干部……罗村长的到访,让一切现出了可见的美好未来。
当然,作品最温暖的,或者说最打动人的,在于亲朋之间相互的牵挂、关爱与体谅,在于身处困境仍然心怀善意并尽己所能地释放善意。劳累一天的疲惫少年,瞥见爷爷编了一半的箩筐,立即“弹起身”,“跑到院前的机井旁,拎起水桶从头到脚冲了个透心凉”,用一桶井水让自己恢复“战斗力”,少年超越年龄的懂事,坚韧,耐劳,令人慨叹。李花因为体谅赶场回来的爷爷又渴又饿,顶着日头给爷爷摘黄瓜。作品中,时时洋溢着动人的亲情,一方面是两兄妹为攒学费,精打细算,另一方面,给爷爷买化痰的冰糖,又是二话不说,高度共识。包括邻里间的互送物品,默默施与帮扶,与尽己所能回报。这种诚挚的情感羁绊,读来令人动容。
作家虽然采取平实的叙事,但故事的反转到来时,仍能击中人心。作品以时间为序,写到了一个丰收季,展望生活的转机,也写到了下一个大旱的艰难年关。这个家庭两次面临难解的困局,一次是妹妹面临上初中,家里却实在拿不出钱来;另一次是大旱的年景让铁桥无计可施。而两次破局的,都是爷爷。铁桥背着爷爷准备“造反”,坚持送妹妹去读书,但爷爷其实早已深知两人的心意,早就为李花准备好了生活费。铁桥在外出打工与留在家里照顾爷爷间犹豫不决,爷爷一锤定音,督促他出去打一年工,供出妹妹,再回来。每次家庭困局的化解,其内里,是家人间相互的、无私的“成全”。爷爷虽然早已力不从心,仍咬牙坚持;虽然心怀儿子媳妇外出打工杳无音信的心灵伤痛,仍同意铁桥外出。哥哥为妹妹前程考虑,全力支持妹妹读初中;妹妹为哥哥考虑,虽然成绩优异,仍然选择了报考中专。他们所做的,都不是理论上的正确的选择,他们封闭了自己上升的通道,放弃了个人的梦想,或断了自己最后的退路,在成全家人的思路中做出义无反顾的选择。
张国龙的语言,显出了较之于前作更加精炼的特色,遣词运句,简洁而有力。少年米铁桥赶场归来的那顿饭,用了四个字形容,“山呼海啸”,速度、声量迎面而来。暴雨突袭的场面,也是声势全出。一些颇为醒目的景物描写,可谓“寓情于景”的写作典范。开篇一段乡间景色,“狠毒的太阳不情不愿偏西了,它的怒气似乎消散了些许”,将山乡农民在农忙夏日对毒日头既爱且恨的复杂心情描绘了出来。一家人聚在屋中听雨的片段,“瓦屋上,雨声嘹亮。院子里,灯光迷离。”嘹亮的,显然不仅仅是雨声,更是一家三口共渡难关的信心;迷离的,也不仅仅是灯光,更是萦绕在屋子里的暖暖亲情。
结尾处的描写,也是颇有意境。夜送村长回来,铁桥带着黑儿,“晃晃悠悠往回走”,周围,“月光把山湾上下照耀得轮廓分明”,铁桥的内心,则“像是穿行在某一个古代的夜晚”,“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肃穆和永恒”。应该说,那正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与无数个不断书写的未来,只要不断向前,而不是自我放弃,那个未来便终究会来。
而作家将这许多我读出的意蕴做了“留白”的处理,并不拎出来渲染,而是让一切重归生活,铁桥听见了不放心他走夜路、寻找而来的爷爷的喊声和火光。铁桥一家的故事也因此,并未落幕。他们的生活的故事仍在那个平行空间中演绎下去。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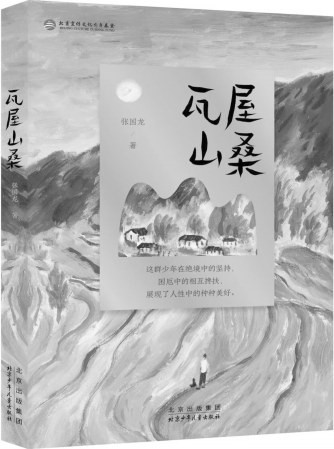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