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凌峰
上海古籍出版社素来重视书目题跋著作的整理出版,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汇编出版“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因其品种齐全、质量精审,而具备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出版特色,成为上古社继“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以后的又一套代表性古籍整理丛书。近年来,上古社以精装形式系统重版该丛书,兼对部分品种作了适当订补,如《澹生堂读书记 澹生堂藏书目》据天一阁藏鸣野山房抄本增补资料,《群碧楼善本书录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据新刊《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辑录(附版本考)》补辑邓邦述题跋,《善本书所见录》新辑补“善本书所见录续补”二十八篇等,皆可窥见整理者与编辑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精神。
除再版旧品种外,“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也注重新品种的开发。近年来随着古籍资源日益开放,古籍深度整理自然成为时代命题。“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推出的新品种,即不乏探索追求书目题跋著作整理新高度的深度整理本,其中以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允为书目题跋著作整理的新典范。笔者认为此书有三大善,特撰小文略陈管见。
首先,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将顾廷龙过录胡文楷增订并自加批注的内容加以吸收整理,使读者得睹顾廷龙批注本《涵芬楼烬馀书录》的庐山面目。此外,将批校内容收入整理本时,是视同夹注随文嵌入,或缀于每篇之后,或附于全书之末,常令整理者颇费思量。以笔者所见,目前持后两种办法较多,但此法每多为整理者省工,而不便读者翻检;随文嵌入则吃力不讨好,既为揣摩批注与正文对应关系而劳心费力,又不免遭割裂正文之讥,但若整理工作到位,此种办法最便读者使用。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所载顾廷龙批注,系据高桥智《顾廷龙批注〈涵芬楼烬馀书录〉》整理,高桥氏的整理办法是摘引对应原文,将批注内容分为“增”“订”两部分。若径以高桥文收入附录,则整理者与编辑俱颇便利,惟读者苦无标注、烦于翻检而已。然整理者与编辑虑及读者需求,投注了大量心血,将这些批注一一复位,嵌入正文,始有今日读来何处为“增”、何处为“订”皆一目了然之效。斯为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第一善。
其次,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将著录书尽可能核对国家图书馆著录信息,逐一标注索书号,并将版本著录信息有异者亦尽数标明。书目题跋著作所以受到读者的重视,其中原因之一便是载录具体书籍的版本、题跋、藏印等直观信息,为读者了解具体书籍内容提供帮助,包括在未能获睹原书时,可据此了解大概。但在线上阅书、线下访书更便利的条件下,书目题跋著作的功用与定位也会有所改变,读者据以“按图索骥”、辅助查访原书的情形必然有所增多。涵芬楼烬馀书对于研究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如《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具备重要价值,对于研究商务印书馆同人学术著作,如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等也有参考作用,是故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逐条核对了国家图书馆的索书号和版本著录信息,颇便学界“按图索骥”,深入考究张元济主政商务印书馆时期的出版史与学术史,对读者考察鉴定具体书籍的版本、图书馆参证修订著录信息等皆能提供重要参考。
当然,整理者与编辑能够完成这样的工作,也有涵芬楼烬馀书毕竟时代较近,递藏源流清晰,且整体捐赠国家图书馆的便利条件。但更重要的是整理者与编辑皆认识到读者有查核原书的需求,并先行做了这道工序。如今古籍整理似多默认读者未必覆核原书,或对古籍同一版本不同复本的特殊性未加考虑,故标注索书号似仍是一种较为新鲜但并不时尚的做法。相信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的出版能为业界树一标杆,推广重视索书号等信息的整理办法,斯为第二善。
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的第三善则在于详实的附录与索引。其中附录所收研究文章有陈先行《影印〈涵芬楼烬馀书录〉稿本前言》一篇,对《涵芬楼烬馀书录》稿本的内容与价值作了全面阐释。另有沈津《张元济与〈涵芬楼烬馀书录〉》一篇,对涵芬楼藏书的遭际与此书结撰的缘起以及修改成书的过程作了细致发覆,可作为这部整理本的导读。外加张人凤先生对涵芬楼烬馀书籍数目及版本情况所作统计表,以及高桥智先生《顾廷龙批注〈涵芬楼烬馀书录〉》一文的解题部分,此书附录可称观止。
另外由于《涵芬楼烬馀书录》著录信息较为完备,新版也配备了综合索引,举凡书名、著者姓名字号、序跋题记者姓名字号、藏书家姓名及印鉴等,皆包罗无遗,这样详尽的索引编法,不仅合于张元济先生的“善本”观,也能便于读者从书籍版本、传承递藏、阅读互动等多方面利用这部书目题跋著作。传统上对于书目题跋著作所作的索引多限于书名和著者,这自然与具体著作的著录详备程度有关,但也关乎整理者与编辑的重视认真程度。“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近年出版/再版的一些品种皆于“综合索引”留意颇多,相信能为将来此类著作整理本的索引编制建立范本。
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的三大善已略陈如上,笔者在翻阅过程中仍然感觉此书有些缺憾。例如此本所载顾廷龙批注皆据高桥智《顾廷龙批注〈涵芬楼烬馀书录〉》移录,而高桥文盖因刊物排版技术限制,于藏印只能著录其文字而不能反映其形制,致使批注信息有所损失。高桥文整理似亦有遗漏,笔者按卷首书影图十三“宋宝章阁直学士忠惠铁庵方公文集”,有顾廷龙移录胡文楷增订并自加批注的内容,然覆查整理本第四二五页及高桥文,皆未见相关批注。又卷首所附顾廷龙批注《涵芬楼烬馀书录》书影并未注明系私人或公家所藏,大概整理者与出版方虽知晓批注本现藏何处,但囿于客观原因难以直接利用,且出版周期亦不容许再等待转机,因此留下遗憾。此外,本书标点亦偶有可商,如第一九页“《周礼》六卷”条陈奂跋“校《周礼·汉读考》一遍”,当是陈奂取此本校读乃师段玉裁著作《周礼汉读考》,“周礼汉读考”中间不应有分隔符。
以上所述不过白璧微瑕,而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允为书目题跋著作整理新典范的地位,私以为必能获得读书界的承认。笔者窃惟整理者、出版方及其他涉事诸公能对此给予足够重视,俾于重印之际可以取得原书,再加详校,使新版《涵芬楼烬馀书录》臻于完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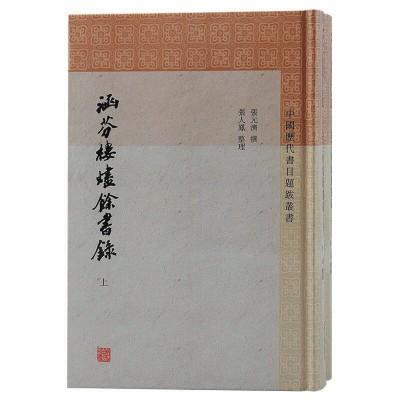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