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微
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宋代学者对前朝的文化遗产极为重视,宋室南渡之后出现的“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盛况即为明证。孝宗淳熙八年(1181),郭知达主持编纂并刊行《杜工部诗集注》三十六卷,然此书在宋末已罕见流传。今世所见传本均为理宗宝庆元年(1225)曾噩官于广东南海漕台时所主持修订的覆刊本。曾噩重刻时将郭编本杜集更名作《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清代以后,此书再次易名为《九家集注杜诗》。此书在现存的数种宋代杜诗集注本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如此重要的宋本杜集却一直未有完善的点校本面世。近日欣闻聂巧平教授点校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校本从初稿到成书前后历时凡十载,参校七种海内所能见之版本,苦心孤诣,考据严谨,堪称十年一剑之学术佳作。
郭知达编刊本《杜工部诗集注》,诸种书录称为“蜀本”。这一初刻“蜀本”在宋末已不易见。理宗宝庆元年(1225),曾噩得到这一善本杜集后,有感于其“字恶纸缺”,遂组织人力物力对其进行了全面校订,翻刻于广东五羊漕司,重新命名为《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此本又被后世称为五羊漕司本或广东漕台本。南宋以后流传之郭知达编纂本杜集,均出自曾噩的这一覆刻本。
聂巧平将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作为点校的工作底本。不过,这个底本的确定还曾经历过一段波折。此前学界大都以为现存《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最早之本为中华书局1981年的影宋本,而中华书局之影宋本的底本原为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藏本,瞿氏藏本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散出,当时张元济先生因无力购买这一珍稀宋本,遂设法借来制成铅皮版准备付印,后因抗战事起而未能如愿。1981年中华书局便用张元济先生当年的铅皮版打样制版影印,然其原刻本却一直不知所踪。实际上中华书局影印本的底本,即瞿氏藏本当年为山阴沈仲涛先生购得,秘藏于研易楼,不轻易示人。此本后随沈仲涛先生乘坐轮渡跨越海峡,辗转漂泊至台湾。1980年,沈仲涛先生将珍藏四十余年的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此本收入《善本丛书》中影印发行。
由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本难以获见,故大多数大陆学者仍只能利用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殊不知中华书局铅皮版影印本的原本仍存天壤间,且已在海峡对岸影印出版。明晓以上原委之后,便可知道聂巧平将铁琴铜剑楼藏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作为点校工作的底本是非常适当的。然其2013年最初开始整理时却仍是以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作为底本,至2017年整理本脱稿之时方在友人的帮助下访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影宋本。从版本优劣的角度来看,此本乃中华书局影印铅皮版之原本,无疑可视为优质善本,亦是作为底本的最佳选择,因此聂巧平毅然决定更换底本。她在《后记》中说:“看到影印精美、字大遒劲的宋版图书,恍如隔梦,百感交集。二话没说,立即决定更换底本,推倒重来。几年的辛苦劳动化为泡影,很心痛。但我没有怨言,只有感恩。能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的铁琴铜剑楼藏宋本作为底本,多么幸运!面对眼前校勘精细、刻印精良的宋人宋注善本,对学术的庄严感与敬畏感油然而生。”将自己辛苦付出数年心血的成果推倒重来需要多么大的魄力和勇气!从中可见聂教授对学术的严谨态度,赤诚精神与百折不挠的毅力,令人感佩。
除了对底本的追寻颇费周折之外,聂巧平还花费了很大精力搜寻《新刊校定集注杜诗》的众多参校本。共参校以下七种版本:辽宁省图书馆藏清内府刻本《九家集注杜诗》,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中华书局1981年影宋本,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九家集注杜诗》,以及燕京大学哈佛引得所据清嘉庆刻本排印《杜诗引得》。这些参校本有些虽容易得到,有些却颇为珍贵,极难寻获。聂巧平教授多年来奔走海内外,孜孜以求,收集到海内外七种校本,其艰辛恐非外人所了解。而这些参校本的最终获得,无疑对《新刊校定集注杜诗》的校勘意义非凡。
聂巧平点校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堪称对郭编本杜集的一次全方位的深度整理,其对此书底本的校勘不仅体现在杜诗正文上,而且也体现在注释内容上。
在充分掌握了主校本、参校本的前提下,聂巧平辨析比较诸校本之异同,去伪存真,取舍态度谨严,终成皇皇四册之集注点校整理本,实为近年来嘉惠学林之盛举。整理者花费巨大精力对郭知达、曾噩原本中的注释内容逐条进行文献验核,辨析异同,考订字句,匡正讹误,故整理后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面貌焕然一新,注释文献的精准度在清刻本问世之后再一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提升,功莫大焉!整理本所订正了的底本中的讹误诸多,书中有很多精彩的校例。如《桃竹杖引》“风尘澒洞兮豺虎咬人”,注曰:“张载诗曰:贼盗如豺虎。”校语曰:
“张载”,原作“王粲”,检王粲诗无“贼盗如豺虎”句,考《初学记》
卷十四《礼部下》、《晋诗》卷七张载《七哀诗》有此句,当是误置,据改。
又如《春日戏题恼郝使君》,底本注引江淹《送友人别诗》,整理本将“江淹”改为“沈约”,校语曰:
“沈约”,原作“江淹”,检“遥裔发海鸿”四句,江淹诗无,考《艺文类聚》二十九《人部》十三、《梁诗》卷六沈约《送别友人诗》有此四句,据改。
又如《双枫浦》,底本注释中将王褒《与周弘让书》的作者误署为刘孝标,整理者将作者改回王褒,校语曰:
检“顷年事遒迈”二句,刘孝标诗文无此句,考《全后周文》卷七王褒《与周弘让书》有此句,当是误置,据改。
陈尚君先生在《点校整理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序》中已经指出,聂巧平对此本的校勘,酌情参校了其他宋本杜集以及清代以来各家注杜解杜之论著,还参校了唐宋各大类书与历代诗文总集,也吸收利用了已有的出土文献以及当代学者的杜诗学成果,因此这一点校整理本可视为继清刻本之后具有“集成性”校定成果的郭编、曾刊本杜集。
整理本卷前有聂巧平撰写的长达四万多字的《前言》,对涉及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的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首先,《前言》指出,在伪注泛滥的南宋中后期,郭知达《新刊杜诗》“独削伪注”,与现存《十家注》《百家注》《千家注》《分门集注》绝不同类,开辟了宋代杜诗学正确的发展方向,在杜诗学史上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对清初钱谦益等人刊削伪注亦起了先导作用。同时还指出,《新刊杜诗》的“坡云”非伪苏注,均为“师云”“赵云”所转引或编纂者摘自诗话笔记中的东坡论杜之语,如此便澄清了此前学界认为《九家集注杜诗》尚存少量未删除汰尽“伪苏注”的错误认识。《前言》还指出,郭知达《新刊杜诗》在宋代集注本中具有“独削伪注”“详引赵注”这两大优势。特别是郭知达本还保存了赵次公对杜诗异文的汇集和辨析,然《十家注》《百家注》《分门集注》《草堂诗笺》等注本均刊落赵次公的异文辨析部分,因此《新刊杜诗》的文献校勘价值与上述那些宋本杜集不可同日而语。此外,《前言》还论析了《新刊杜诗》的文献价值与版本价值。指出《新刊杜诗》保存了不少散佚文献的佚文,由于宋人注杜多引杜甫之前的典籍,而这些文献目前大多数已经亡佚,故《新刊杜诗》恰好成为文献辑佚的重要来源。像东汉杨孚《异物志》、西晋郭义恭《广志》、南朝宋沈怀远《南越志》、西晋魏完《南中八志》、后晋平居诲《于阗国行程记》俱赖此书的征引,保存了弥足珍贵的片段,这也反映出《新刊杜诗》之文献价值。值得指出的是,《前言》中所有观点都是通过细致的校勘从一条条材料中抽取出来的,故其所得结论大都确实可信,体现了无徵不信的严谨学风。
总之,由于底本别择审慎,校本搜罗丰富,点校细致认真,聂巧平点校的《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是目前郭知达编本杜集最堪依据之整理本,为宋本杜集的整理提供了良好范例。相信此书的整理问世必将为推动杜诗学的繁荣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当代杜诗学研究也必将由此取得新的成绩。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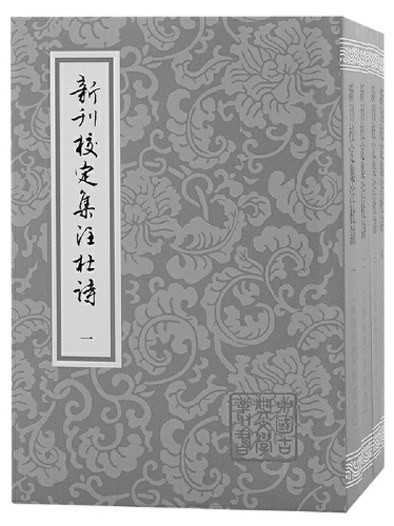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