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
有清到了他爹坟上。他爹埋在孤山铺圆墚凸的小土台上,阴阳江湾先生说,这里山向好、水向好,土厚实,葬在这里能荫佑子孙。有清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他开始用杀猪刀挖坟前的土,很费力,时不时就得停下来缓口气。约莫挖了二尺深,他把所有刀具并盒子一件件放了进去。看着这些他爹传给他,传了许多代的刀具,他在坟前默了良久,心里起了誓言。
——《杀猪匠》
喝完一盅,老爷道:“美得很,满花子!”那人用酒壶并酒盅,凤凰三点头拉长一兑,果然,酒盅上满满盖着一层酒花。老爷和那人四目相对,相视而笑。那人心里欢喜,再酌一盅给老爷,老爷却微笑着直摆手:“放心,有我喝的。”那人也一笑,一仰脖。
——《巷道老爷》
卧房只有如斗纸窗可以透光,而彼时屋外如浑暮,而屋内如夜,窗外电闪阵阵,几乎要裂墙窗而入。媛媛不禁掩耳向外婆怀中瑟缩,就连在这山水中长大的焕焕,自以为对这山水天地已经过分熟稔了,这一刻也害怕起来了,也不觉向奶奶身上靠去,奶奶便一手从背后揽住媛媛捂着耳朵的小臂,又一手去拉焕焕。
——《南山有台》
讲故事的这个人叫刘栓(他说他从山里来,学书法喜欢张旭、米芾,所以自己起了个笔名叫颠山),一个青年作者,目下供职于一家大学出版社。我的一本正在热销的书,他是责任编辑。那书中大部分的篇章是我写的。但同时,大约有三分之一,我累了,老眼昏花,于是凭口说出,而他,用录音笔记录下,整理成文字。
他的文字功力叫我惊讶。那天我给一个来访者题字,他说,我将上大学以来,工作以来,琢磨出的最好两句话贡献出来,这两句话叫“承先贤衣钵,开自家面目”。话语一出,赢得满场惊讶。尤其是“开自家面目”一句,隐约间透出一股霸气来。
他的老家在陕南秦岭最深的山中,最高的山中,那地方叫山阳。我说,你是普通人家的孩子,祖祖辈辈都是山民,能从这一山放过一山拦的地方,家族中走出你这么一个人物,是家族一代一代积攒地气的结果,获得性具有遗传性,积攒到了你这一代,家族中终于出现了个人物,考上名牌大学,居住在了城里。
作者原先把这本书的书名叫《龙须草》。龙须草是一种长在山地的草木。农户人家、行脚士兵、云游僧人脚下穿的那草鞋,大约就是用这种草编织的。还有,那“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蓑衣,据说也是用它编织的。
我能理解作者用“龙须草”作为书名的寓意。那是草根百姓的植物,吾家吾国,吾土吾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作者借龙须草,表达了自己对故乡,对如蝼蚁、如草芥的那一方百姓的喟叹,对他们顽强的生存斗争精神的礼赞。
这是秦岭最深最高的山里。在我们匆匆的路经者的眼里,山峦高耸,云遮雾罩,一场风就带来一场猛烈的暴雨。我们无法更深入地走进去。那狭窄的山里劳作的人们,那灰瓦白墙的房屋建筑,那一直通向山顶的羊肠小道,对我们来说,那就是谜。他们的日常生活起居,他们的行事方式,他们那乱糟糟的头发所罩着的脑袋,整天在想些什么,这些都是谜。
阅读其中那些杀猪匠的故事,那些篾匠、瓦匠、泥水匠、铜匠、木匠、石匠,那些普通人家的婚丧嫁娶、民间习俗、行事方式,等等,叫我想起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孙犁的白洋淀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这些系列轻轻揭起这偏僻地域一角的面纱,把那些地方的人类生存图景展现给世界看。
当然,他们的文笔老辣,简约而又精准,且给庸常的生活人为地涂上了一层玫瑰色,这是需要本书作者学习的。
而本书作者的长处则在于,他是以一支缜密的笔,如数家珍般的描写,展现了那块山地上的人们,生活的全部俗常性。这也是一代与一代人,艺术追求不同,对生活的理解不同的原因吧。
我建议作者把书名改成《南山有台》。这样会沉甸甸一些,居高临下的概括力强一些。这话来自《诗经》。
《诗经》中有“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一句。专家为我们注释说,所谓“台”,所谓“莱”,都是地里长的一种草,台可制蓑衣,莱嫩叶可食。那我们在这里且把“台”当作作者所说的龙须草吧!从《诗经》的年代,这草就长在南山里了,而从《诗经》的年代,百姓就生活在这片山地了。一茬一茬的草,一代一代的人,直到今天。如是想来,我们不由得向这块山地致敬,向这些卑微的如蝼蚁如草芥的生命致敬。
作者是如此的年轻,人生的大幕,文学的大幕,对他来说才刚刚拉开。这本书的叙事,还显得啰嗦或繁琐,故事也叙述得不够饱满,虽然作者凭借丰厚的生活底子,给予了一些弥补,但是还是不够的。也许在下一本书中,我们能看到他的改变和提高。
前天我画了一张画,画的是秦岭高耸的一角。画名叫《直上秦岭第一峰》。旁边题字说:“秦岭第一峰曰太白山,第二峰曰牛背梁,第三峰曰西岳华山。”
驴友们告诉我,从秦岭第二峰柞水的牛背梁上山,顺山顶绕,可以绕到黄峪寺,那是唐代皇家行宫翠微宫原址,再往东绕,还可以绕到云遮雾障的那些山阳的大山中去。
谨以此语,寄语刘栓以及所有的青年才俊们。你们有年轻作为本钱,可以而且有理由比我走得更远一些。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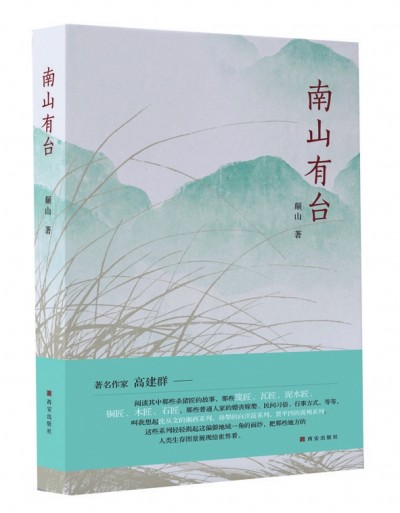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