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刘兵
江: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正确,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这三条往往表现为下意识,或者只是内心深处的信念,通常不方便直白说出。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当然不会每个人都是科学主义者,尽管科学主义者在他们中的密度可能比一般公众中的密度要大一些。
这次我们打算谈的这本书,取名《第三次沉思》(Third Thoughts),从字面上看完全不反映任何主题信息(本书的一篇序中说温伯格自己同意是“第三本文集”之意)。护封后勒口上的译者秦麦简介,居然写着:天文学硕士、教师、占星师、自由译者、天文爱好者。“沉思”+占星师,很可能让不了解内情的人误以为是一本讲伪科学的书。
本书作者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因为有点热衷于“跨文本写作”(写学术论文之余也进行大众文本写作),所以在公众中也算薄有浮名。本书就是他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集结,属于大众文本。
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个你非常熟悉的问题开始讨论。温伯格作为物理学家,也玩票写过一本科学史著作《给世界的答案》——据说这本书没有像他的其他著作那样广受好评,而是招致了不少批评,因为他在书中宣称:辉格史学应该在科学史中有一席之地。而在《第三次沉思》所收的25篇文章中,有两篇是温伯格对上述批评的回应——他当然坚决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极力论证辉格史学在科学史中具有独特的合理性。我知道和辉格史学有关的话题曾经是你非常熟悉的,因此很想听你先谈谈对温伯格上述观点的看法。
刘:我也正想重点谈谈这个问题。关于辉格史学,是一般历史学中,尤其是科学史中非常核心的问题之一。如今,这个概念在国内科学史界也是基本常识了,不过可以有点自得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在国内最先介绍引进与辉格史问题有关理论的人呢。
简要地说,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在其《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在许多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倾向:他们……强调在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并写出即使不是颂扬今日也是对今日之认可的历史。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今日的方式,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从而存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可以进行选择和剔除,可以强调其论点。”
在科学史发轫之初,科学史写作大多是职业科学家的业余爱好,那时的科学史基本上也都是“辉格式”的。大约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随着科学史研究的职业化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新一代的科学史家从一开始,就更多地接受了人文科学的训练,相应地,新的研究传统和新的价值标准得以巩固。不那么极端的反辉格史的倾向已经成为专业历史学家的某种标配。
但或许是因为作为诺奖获得者这样的权威身份,让温伯格很有自信地宣称他对辉格式科学史的肯定和坚持。这里也许还有很多原因可以讨论,例如这与温伯格对科学的“正确”和科学之进步的强调等是密切相关的。但至少,在“专业性”的问题上,温伯格的自信是可以被质疑的。设想,如果一位历史学家要对物理学领域的专业问题发表意见,那物理学家们又会如何反应呢?
江:我们不妨先“就书论书”,在《第三次沉思》的“关注当下——科学的辉格史”一文中,温伯格为科学史中的辉格史学辩护的主要理由是:科学是在不断积累和进步的,不像人文学术,可以几百几千年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原地踏步纠缠不休,“但是我们可以完全自信地讲,时间的流逝已经证明,关于太阳系,哥白尼是对的,而托勒密的信徒们错了,牛顿是正确的,而笛卡尔的追随者们错了”。温伯格还找科学界支持他观点的人来壮声势:“我想这是因为科学家们需要这样的科学史——关注当下科学知识的科学史。”
是的,温伯格的玩票科学史,可能是科学家需要的科学史,但他显然忘记了,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却不是历史学家或科学史家需要的科学史。根本的问题在于,温伯格完全误解了科学史的目的和功能——这正是一个票友进入陌生领域时很容易出现的情况。而更致命的是,许多科学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如果想进入科学史领域玩玩票,那肯定只消略出余绪就可以轻松成为一代名票。
问题的根源是,温伯格和许多科学家一样想当然地将科学史视为科学的附庸——讲讲科学家的故事,讲讲科学成功的故事,唤起听众对科学的热爱和崇敬,最终目的是成为寻求新科学知识的科学共同体的啦啦队。在这样的目的之下,关注当下自然是必须的,因而辉格史学看起来也就是合理的了。
可是,科学史的目的,显然不是寻求新的科学知识。
所以,温伯格为科学辉格史辩解的主要理由是无效的。更何况,在细节上,这位票友的论证也有漏洞,例如,关于太阳系,我们早就知道哥白尼也是错的……
刘:所以我说这与温伯格对科学的“正确”和科学之进步的强调等是密切相关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前面的多篇推荐序中,许多序作者也同样在赞同着温伯格关于辉格式科学史的主张。当然,温伯格在书中也以表面上很“谦虚”的方式提到:“像我这样的科学家必须承认,我们不能达到专业历史学家对于史料的掌握程度。”但究竟应该由谁来写科学的历史呢?他的答案是:“都可以写。”在这表面谦虚的背后,其实透着对科学史研究的深层轻视,仿佛科学史家的优势只是掌握了更充分的史料,而并不需要其他的训练准备。就此类比,如果一位科学史家说,我们虽不能达到科学家对实验数据的掌握程度,但我们也可以做科学研究,那人们又会作何感想?
半个多世纪前,现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萨顿,曾就在科学教学中的情况评论说:“请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来讲天文学史,或者请一位化学教授来搞化学史,他们会感到这是完全自然的事(难道他未曾获得诺贝尔奖金吗?而这不就是充分的资格吗?)……一份漂亮的教学计划印出来,那所大学的公众(教授、学生和随从)会大吃一惊,发现他们当中竟有如此众多的科学史家。谢天谢地!几乎系里每位老师都是了!当然,这样一张课程表是一种虚张声势,而且主讲人越著名(如果他们事实上不是科学史家的话),这种骗局也就越大。”我注意到,温伯格在此书中也屡屡提到自己在大学中讲授科学史课。
这也表明,除了科学史学科与科学相比的相对弱小之外,对科学史的误解,在科学家或科普工作者中,也是大有人在的,这也提示着,在当下这样一个事事追求以专业化作为传播工作之基础的时代,对于专业化的科学史的传播和理解,专业科学史工作者们仍然还有大量艰巨的传播普及工作需要去做!
接下来,我还希望能适度地谈谈温伯格的大众文本写作。我不知道你觉得他在此书中这些普及化的、也即应该是面向非专业人士的文本写作是否成功呢?这恐怕就又涉及有关科学家和科学作家(science writer)的专业化问题了。
江:你引用的那段萨顿的话,仿佛是萨顿在半个世纪前就为温伯格这样的玩票科学史特地准备的,“虚张声势”“骗局”……这些措辞真是太犀利了。
至于温伯格的大众文本写作,我们不妨以书中“我们仍不了解的宇宙”一文为例来考察一番。此文是温伯格对霍金《大设计》一书的评论,虽然这种缺乏热情的书评并不罕见,但说实话这篇书评确实乏善可陈。
我们知道国外有许多物理学家不喜欢霍金,只是考虑到霍金名头实在太大,一般也不好意思直接说霍金的坏话,通常要表达对霍金的不满就说些皮里阳秋的话嘲讽两句。温伯格是否喜欢霍金,我没考察过,从这篇书评看,似乎也不像喜欢的样子。
温伯格一方面说,许多评论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大设计》的宇宙观有没有上帝这件事情上“在我看来很愚蠢”,一方面却自己也在书评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谈论宗教和上帝(幸好他是结合着人择原理来谈的)。温伯格同意《大设计》的“主题之一确实对宗教具有影响”,但对于书中的另一个主题(外星人,以及我们要不要主动寻找外星人),温伯格这篇书评中却没有一语提及。
当然,温伯格的理解能力还是足够的,对于《大设计》的第三个主题——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温伯格正确地指出:霍金“表达了一种对现实彻底怀疑的看法”,他也意识到霍金其实已经站到哲学上的反实在论(《第三次沉思》中译本将这个词译为“反现实论”,意思不算错,只是表达不够专业)阵营。
不过,温伯格最后说,他感觉必须指出《大设计》中的“一些历史性错误”,我又不大赞成了。他一共指出了三条,第一条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后两条基本上属于吹毛求疵。这估计也是刻意遵循在末尾说两句“白璧微瑕”的书评套路吧。
刘:你举例分析的是温伯格的一篇书评文章,你对这篇他评论霍金《大设计》的书评的见解,我也都同意。其实在这本文集中所收录的文章,有不少是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的。但这些文章读下来,与我以往对《纽约书评》的印象却有点不太一样,也不知是我过去的印象出了问题,还是温柏格的文章在《纽约书评》上也属另类。
本书收录的一些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以及曾发表在其他报刊上的文章,除了书评之外,还有不少很像我们这里的“科普文章”,只不过是一位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写。在我读下来的感觉中,其实这些“科普文章”并不是很好懂,除了一些并无特殊新意的科学史介绍文章之外,哪怕是在讲他本人最熟悉的理论粒子物理方面的话题(例如“标准模型”),阅读的趣味性和通俗性似乎也都有些问题,至少,面向非专业人士,要想真正读懂,恐怕也还是很困难的。我想这样的普及传播,效果也还是有限的吧。
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温柏格对于载人航天的坚决反对,以及他对SSC(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下马的遗憾。当然这又与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关心自己领域经费分配的利益立场有直接关系,在这里他又确实表现出一个热爱自己的研究领域的朴素形象。或许,如果一定要为此书的特殊价值找到一个支撑点,我认为可以是:它提供了一个有名望的科学家的业余科学史和科普的代表性样本。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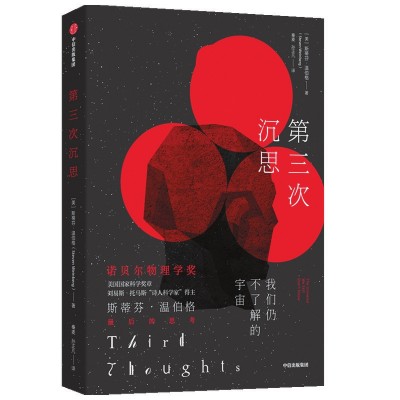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