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河源
司马少先生那几篇文章断定《喜》是不值得卒章的“烂书”后,想持平而论《喜》,就得有相当勇气,遑论为之辩护了。但读完《喜》后,我觉得并未浪费时间,自觉还收获不小,因为,《喜》激发了我的思考。
“百代皆行秦政制。”大秦全面推开的郡县制(道县/路县/省县),成为吾国牢不可破的政构,千年不易。自秦以后,曾风光无限特别让人追怀的周制封建,流水落花春去也,沈园无复旧亭台了。虽然汉初和西晋,也有短期的王侯封建,但七国之乱差点让襁褓中的大汉夭亡,八王之乱更直接葬送了西晋,锦绣中原尸山血海,南渡衣冠堕泪新亭,无限凄凉。
两千多年过去,秦帝国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就有譬如依然在使用的地名,岭南的如南海、桂林、龙川、封开等。更可称伟大的无坝引流工程,如川西的都江堰,桂东的灵渠,是真正经过时间检验的永续伟业。一个帝国能给后代留下一个如此工程,足够不朽了,秦居然能有二,就这点,不妨颂颂秦的。
自谓“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的始皇帝,奋百年积威,十年之间,横扫六国,并吞八荒。千古一帝也好,残虐暴君也好,都成过眼烟云,大秦帝国留给人的印象,只能是一个边界模糊的影子。好在,封存在湖湘大地古墓古井中的秦简,最近几十年,不断出土,给古不考三代以下的历史学者们无上的惊喜。其中,古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的出土文物,尤其十一号墓地主人喜的陪葬秦简,更是管窥秦帝国包举宇内机制的一块切片。
虽然喜“个人的历史,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他短短四十六年的生命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又是如此平凡,几乎没有叙述的价值。”历史学者鲁西奇先生当然“无意于给喜立传,或者写一部喜的个人史,或生命史。”但何以他对这位“和秦始皇是同代人”的喜,又异常关注呢? 因为他想借喜来呈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卑微个体生命的若干面相”,给“在这个世界存在过”却“不曾在历史上留存”的无数人,“找寻在历史长河中的存在感和‘意义’”。
《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一书正文,由三个部分组成:“斯人”“黔首”与“为吏”。加上一份非常详实的分章注释。喜个人的身高、样貌、穿着、所居、所业、婚娶、老病、名字、邻里、秦人、吏卒、黔首、徒隶、长吏、列曹、诸官、诸史等等,经由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岳麓书院藏简、北大藏秦简相关内容的爬梳排比抽绎分证,鲁先生很好呈现了秦帝国县乡以下的基层结构,核心家庭的一般面貌。至于那个时代寻常而现下不易共情的观念行为,《喜》在不少层面有相当精彩的揭示。比如“暴”谥之秦,居然崇孝,出人意表。“原则上,不孝是可以处死的。《史记·李斯列传》说秦始皇死后,赵高等诈伪作始皇帝书赐长子扶苏,说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正因为此,《法律答问》中所举的免老甲和‘告子’爰书中的士伍甲才会以‘不孝’为由,要求将其不孝子处死。”
对于中国古代帝制两千多年的基层治理,我们的一般看法是“皇权不下县。”这在绝大多数时期,应该是实情的描述。但用在秦帝国,就显然并不适用——大秦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甚至可以达到现代交通通讯允许的程度,一竿子就到了乡,“秦时的乡吏,一般包括乡守(乡啬夫)、佐和史三人。”户籍、民爵、征发、赋役、出产、土工,莫不在乡吏的掌控当中。在出土秦简所记录的兵卒、黔首个人信息,名字而外,年龄、乡贯、身份、身高、脸色、须发、穿着等等,均详细记载,令人匪夷所思。
武装到牙齿,管控至微细,科层化程度之高,跟现代社会差相仿佛,即使皇权专制顶峰的明清,控制基层中国的力度与密度,恐怕也远不能与大秦相颉颃。睥睨四海,天下无敌之时,认为金瓯永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就再合理不过了。始皇帝怎么可能相信,自己沙丘暴亡,尸骨未寒(其实寒不了,“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就被赵高、胡亥和李斯联手矫诏,逼死公子扶苏,胡亥上位。数年之后,“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徒之徒”的陈涉吴广,“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杰并起而亡秦族矣”。15年而社屋为墟,子孙族灭,《喜》这份大秦帝国的组织切片,或者就提供了部分答案。
我没有追踪鲁教授对司马少先生批评的反应,对我而言,司马少先生的细读功夫,对我的粗略是极大的矫正和提醒,对于我所期望的“有学术趣味的非专业阅读”而言,司马少那样的读者,多多益善,当然,最好“带着最大的同情”。如吴尔夫所言:“如果在媒体没有准头的射击之外,作家能感到还有另一种批评,来自于爱读书而读书的人,他们在慢慢地、非专业地,带着最大的同情,但又以最严格的态度阅读。这难道不有利于提高作家的写作质量吗?”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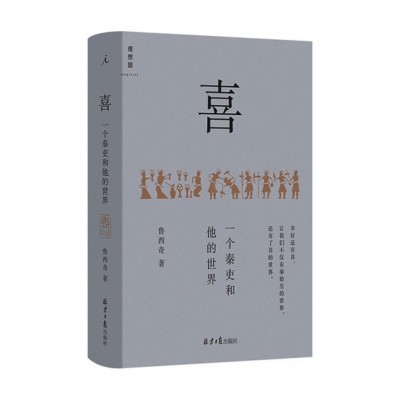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