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伟
在鲍磊以往的作品中,不管是《夜照亮了夜》还是《青春是远方流动的河》,都能读出他身上是有着浓郁的书生气的,这是一种青春叙事,也是一种如一袭白衣,翩翩而至的公子的古典气质。在新书《飞走的鼓楼》中,风格延续的同时也在酝酿着突破,奇幻故事的新编则带来了天马行空的阅读体验,还有借助多重人格讲述来进行的文学实验,又让人眼前一亮,不同的题材显示出写作者也在努力进行着自我突破。就如在阅读中,我发现一些人物、情节常以熟悉的气息在不同文本中穿插出现,带来了一种统一情绪的延续。还有很多故事似完未完,落笔处总留下了大片空白,这或可说是作者刻意营构的情调,但将之视为城市之中故事多义性的隐喻也未尝不可。
或者就像他自己自述的那样,这一本书是要“向我居住多年并热爱的北京致敬”。那“北京”是什么呢? 在《一棵桑葚树》中,北京是一种“失去”;在《飞走的鼓楼》里,北京又是一种“寻找”;到了《可是我还是学不会》中,北京又代表了一种逃离之后的“结局”;当然,北京也可以是“互相取暖”(《铮铮和唐唐的两扇门》)和人生颠簸中的安定和淡然(《阿南旅馆》)。十九篇小说,十九个故事,也就是十九种北京的风景。作家对城市的书写,描绘出了城市的诸多面貌,而凝聚在其中的还有作家本身的个体情感体验和写作姿态。于是,这些不一样的北京风景已然在透露着与惯常所见的北京书写不太一样的气息。
通读之下,这本集子中有两个文本格外地让我驻足回味,一篇是《飞走的鼓楼》,另一篇则是《凡墙都是门》。因为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篇小说构成了一种呼应。前者写的是一个纯洁少年陈默在沧桑中年刘森生活中蜻蜓点水般掠过后留下的一圈涟漪,后者写的则是“我”藉由一场梦而得以畅游自己喜爱已久的女作家笔下倾力书写的小镇“月光古城”。哑巴少年陈默的出现,唤醒了整日里昏昏噩噩的刘森尘封已久的苍老的心;“我”在梦中穿越时间,邂逅了一场另外时空中的古城玄幻。这样两个故事,一个现实,一个奇幻,看似并没有交集,但实际上在叙事的内里却暗含着对应。在《飞走的鼓楼》中,陈默悄然离去后,刘森虽然遍寻不得,但还是再次捡起来自己内心深处早已遗落许久的初心;而《凡墙都是门》里,“我”从梦中醒来,纵然惆怅于梦境中的美好不可得,但面前的墙却是真实可触碰的,这样的“实”又给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身披岁月沧桑的鼓楼飞走了,这在现实中当然不可能发生,而月光古城中的奇幻故事,却又未必真的是神话传说。鲍磊围绕着“鼓楼”,用现实世界的人事写出的是人们久藏于心底的那种炽热和躁动,并让它得以在纸面上成形;而在虚幻的月光古城中,他则是从迷离中幻化出了对于现实的某种期许,让那些形而上的渴求在生活的白墙之上获得了真实的碰撞。毫无疑问,鲍磊在一正一反、一虚一实的反衬中,写下的都是关于在某个空间中的一次“寻找”,正是在这个关键词之下,两个文本获得了呼应,也让我们读到了小说集中潜藏的文心。
初识鲍磊,是在鲁迅文学院的作家班之上,他在生活中的简单、率真也让人好奇其笔下的文字究竟是何模样,正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鲍磊文字中所弥漫的青春、纯粹甚或是稚嫩都是他生活的完整投射。他的很多执拗让笔下的文字或者说整个人都显得那么的“边缘”,可这样的边缘带来的不是隔绝,在这个城市边缘游走,恰恰为鲍磊带来了更多的观察视角和写作活力。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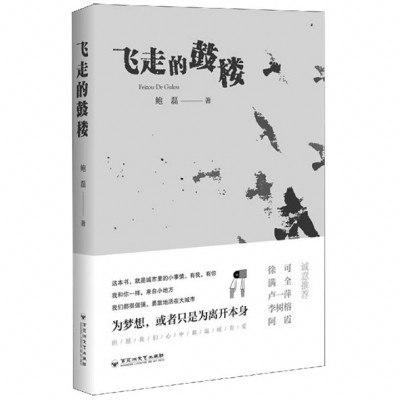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