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
古代文学传播研究,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以来,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宋代文学传播研究,成果也相当丰硕,其中北京大学王岚教授的《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2003年)、南京大学巩本栋教授的《宋集传播考论》(2009年),尤其引人注目。近年来,又有多元多向的开拓,潘明福君的《两宋时期的文集编纂与传播研究》(以下简称“潘著”),就从三个维度上有力推进了宋代文学的传播研究。
第一,从广度上拓展了宋代文学传播研究的领域。之前的两宋文集传播研究,更多的是个案研究,集中探讨一家一集的编辑、刊刻和流传过程,而潘著着眼于宏观,由点及面,全面系统地探讨宋代文集编纂与传播的历史背景以及文集编纂的类型与主体、理念与原则、模式与方法等等。潘著还进一步将宋代文学传播研究的视野由两宋境内传播延伸向两宋境外传播,深入考察了两宋境外传播的民间私下传播、使节公开传播、商人售卖传播等途径及其效应,增进了读者对宋人文集在两宋境外传播面相的认识。潘著不仅仅关注宋人编印的本朝文集,还关注宋人编印的前代文集。这就完整地还原再现了两宋时期文集传播的盛况,因为宋人既传播和接受本朝人的文集,也同样传播和接受前代人的文集。因为本朝人的文集、文学典范,是在前代人文集和文学典范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了解前代人特别是唐人文集的传播,就无法真正了解宋人文集传播的根基和前提。所以,潘著不仅从共时性方向拓展了宋代文学传播研究领域的幅度,也从历时性方向拓宽了宋代文学传播研究的长度,这颇具范式意义。研究一个时代、时期的文学传播,不仅要注意同一时代、时期的文学传播,还要注意前代文学在当下的传播,这样才能理清一个时代或时期文学传播的理念、途径、方式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使研究更具有历史纵深感。
第二,在深度上开掘了宋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层面。宋代文集的抄本传播,虽世所共知,但宋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更多注意刻本传播,于抄本少有深究。而潘著则深一层地探讨了宋人文集抄写的多种动机和类型,或因进献、或求干谒、或藉赏读、或为求序、或为传承、或求扬名,让我们对宋人为何抄写、如何抄写文集有了深入的认知和理解。两宋时期的“行卷”,以前学界不大关注,近年随着对宋代科举文化研究的推进,对“行卷”的历史现象已有越来越多的了解。而潘著则深入一步,从传播的角度分析了“行卷”式传播的模式及其影响,从众多案例中概括出“行卷”传播的三大特点:传播目的的功利性与路径的单一性、传播内容的精品化和文本的临时性、传播对象的明确性和时间的固定性,凝炼出“‘射线群’传播”和“代表作领衔传播”两种模式,皆发前人所未发。他还发现,“行卷”传播既有动力,也有阻力。动力来自于前代举子“行卷”的启示和当代行卷成功者的鼓舞,阻力则来自于朝廷的公开打压和“謄录”“糊名”等考试制度的制约。这些新发现,都是沉潜于浩瀚的文献史料,经过艰苦的爬罗剔抉而得,故结论坚实可信。作为与“科举”并存的“荐举”制度,对文集传播的影响,时贤几乎未曾留意。而潘著深入考察了“荐举”制度对文集传播的影响,指出荐举制度形成了特定的传播渠道,开启了二次传播和广辐射面的传播途径,结论新人耳目。从政治制度层面考察宋人文集传播的动力因素,大大深化了宋代文学的传播研究。
第三,从精度上提升了宋代文学传播研究的水准。个案研究,难以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现象上升到规律性认识。而宏观的整体研究,易于把握全局、总结规律、提炼特色。潘著无论是上编对于文集类型、编撰理念及原则的提炼,还是下编关于“行卷”传播模式、荐举制度对传播影响的概括,都不满足于案例、现象的陈述,而是尽可能地上升到理论高度,总结出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往往一语破的。如果说宋人“以类相从”的编纂原则,让我们既熟悉又陌生,那么,“奏议不入文集”的编纂原则,则让我们倍感新奇,而书中对“奏议不入文集”两大原因的揭示,又足以使我们心服首肯。书中章节的标题“模式与方法:宋人对唐集的编纂”“理念与原则:两宋编集的独特旨归”“‘行卷式’传播的模式”“两宋时期文人文集的商业模式传播”,都可以看出著者对传播现象进行理论概括的努力。
总之,此书新见迭出,论证周密,思路清晰,是近年来对两宋时期文集编纂与传播研究的一部力作。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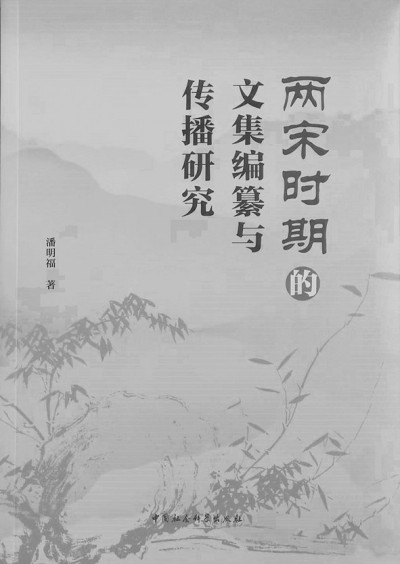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