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香
随着近些年丝绸之路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领域,相关研究不断丰富。他们或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进行通史性论述,或从不同专题角度进行研究,但是陆海兼顾,中西互通,多学科交叉并且图文并茂地解读丝绸之路的通识性专著并不多见,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新作《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以下简称《丝路十八讲》)无疑是近年来丝路研究的一部代表作。
如同作者2001年所出版的影响深远的《敦煌学十八讲》(后又再版)一样,《丝路十八讲》也是一部“极具个性”的作品,即如作者所言,在照顾每个时段东西交往的主要内容之外,更多地把作者自己若干年来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一些收获融入其中(P7),因而该书显然是通过新材料、新问题等带来的新认知,希望讲述一些其他的丝绸之路通史类著作中所没有的内容,这无疑更令人期待。
《丝路十八讲》从月氏、斯基泰与丝绸之路前史讲起,涉及到张骞“凿空”与汉代丝绸之路、佛法的传入与流行、纸对佛典在丝路上传播的贡献、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粟特商业活动与贸易网络、祆神东来与祆祠祭祀、中古波斯与中国、条条大路通长安、唐代长安的多元文化、《兰亭序》的西传与唐代西域的汉文明、从波斯胡寺到大秦景教、摩尼教入华及影响、唐代的“郑和”杨良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归义军与东西回鹘的贡献、葱岭东西的各政权、从蒙古西征到马可·波罗来华等十八个专题,时间上跨越先秦至元,涉及到陆海及草原、西南丝路等,兼顾到了东来西往双向交流,材料丰富而多元,问题意识突出而强烈。全书470多页,45万字,构思宏伟、体大思精,无论是作为一部通识性质的教材,还是作为一部研究论著,都具有一定典范性和前沿性。
一、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新材料与新认知
《丝路十八讲》虽然以讲义的形式呈现,但如作者所言,重点根植于自己研究的主要时段,同时也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些内容直接来自于已经发表的文章(P8)。因而该书最大特色就是新见与新知,这其中一方面是新材料的利用,另一方面就是新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并由此开拓出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例如讨论汉代丝绸之路时,大量利用了悬泉汉简等材料,指出敦煌悬泉不仅仅是兵站,更是客栈,悬泉所接济的人,不仅有东归的将士,还有东往西来的外交使节,从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各国的材料来看,汉朝与西域各国的物质文化交往,是两汉时期丝路往来的主要内容(P39,P43)。而悬泉小浮屠里简的发现,说明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经传入敦煌,也由此说明佛法是经敦煌传入内地,这样就在贵霜与东汉之间的佛教传播链上增加了一个关键的点,意义重大(P69)。
出土文书和石刻材料也是作者关注的重点。作者自2000年来陆续出版《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著作,均利用了新出石刻、文书等材料。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也体现在本书中。例如作者通过梳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和粟特文文书及中原各地出土的汉文墓志等材料,勾勒出中古时期控制陆上丝绸之路的商业民族粟特商队的构成、由粟特商队建立的胡人聚落的功用、粟特人的商业活动与贸易网络等,以及由商业活动带来的东西文化交流情形,包括祆神沿丝路东来与沿线各地的祆祠祭祀等,这些研究都具有前沿性,可以与欧美、日本等学界进行国际性学术对话。
在探讨萨珊波斯与中国的关系时,作者敏锐地注意到1980年西安东郊发现的波斯人李素及其夫人卑失氏墓志,展示出一个波斯景教家族入仕唐朝的完整画面。尤其是李素及其子曾执掌唐朝天文历算机构司天台,担任最高长官司天监,显然与其景教徒身份及其在天文历算方面的特殊才能有关。这项研究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大大推进了萨珊波斯与中古中国关系史的研究。此外作者对1984年陕西泾阳发现的《杨良瑶神道碑》进行了重新解读,发现唐朝贞元年间曾派遣中使杨良瑶从广州出发,经海路前往巴格达,出使黑衣大食。这一事件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意义重大,它开启了唐朝官方经海路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和贸易(P349)。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如同“唐代版的郑和下西洋”,作者通过揭示出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丰富了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关系史的篇章。
二、将丝绸之路纳入中外关系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如作者所言,在中国,丝绸之路研究是放在“中外关系史”学科当中的,这门学问早年又叫作“中西交通史”。从张星烺、冯承钧、向达、方豪“中西交通史”几大家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一大批学者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丝绸之路研究也重新焕发了活力。而丝绸之路研究的热潮,对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是一个强大的促进,在各个方面推进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进展。因而作者在《丝路十八讲》一书中不仅仅将视野放在传统中国与域外的关系上,更是放眼到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流与文化互动中进行考察,使得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
在全书第一讲中,作者讨论了在张骞西行之前,在丝绸之路上活跃的各民族和政权,如匈奴、月氏、斯基泰、波斯以及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留下来的希腊化王朝治下的各个民族,他们历史及分布等。与张骞相比较,他们都是丝绸之路的先行者,因为他们的存在和活动,早期不同文明之间有了频繁的交流。尤其是月氏、斯基泰等活动范围广泛的民族,承担起“前丝绸之路”时代的东西方物质文明往来的中间人角色(P28)。
作者在最后一讲涉及蒙元时代,从蒙古西征谈到传教士等来华,尤其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父子从地中海来到中国,停留很长时间,又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回到家乡。马可·波罗留下了关于13世纪后半叶丝绸之路上各国的种种见闻,成为这一时期有关丝路的最重要的文献。本讲融汇了作者及其主持的马可·波罗读书班的研究成果,补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例如关于马可·波罗《寰宇记》的各抄本情况、其选择陆路来华原因、在华十七年的“斡脱商人”身份及前往大印度、扬州、杭州等地的活动,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的住地及经商、被捕等情况,这在同类元代中外关系史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作者通过分析这些史实指出:蒙元时期中西交往的加强,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蒙古各国与欧洲直接接壤,使中欧交往进入直接接触的阶段,欧洲通过使臣、商人直接了解了中国,中国也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因为中国和建都波斯地区的伊利汗国关系密切,所以阿拉伯文化,特别是医学与天文历法,大量传入元朝(P448)。
三、东西视角的观察与解读
文明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治中西交通史专家方豪先生就曾指出:“东西民族,既有接触,文化亦发生交流,有来者,亦必有往者。”然而囿于材料的限制,我们对于外来文明传入中国的研究较多,对于中国文明或中原文明的西传则更多关注丝绸、漆器、铁器以及瓷器等的传播与影响,这种观点和内容一直层层因袭。《丝路十八讲》一书也用很多笔墨书写中国所受外来文明的影响,尤其是以长安等为中心,讨论外来文化的影响力,如“条条大路通长安”“唐代长安的多元文化”两讲专门对此进行聚焦。但除此之外作者也另辟蹊径,从纸、书法作品、典籍等新的视角来解读中国文化的西传,在纸对佛典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贡献一讲中,从物质载体的角度,来看中国发明的纸张对于佛教典籍作为一种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传播的重要意义。另外,中国发明的纸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书写材料之后,因为轻便易于携带,成为旅行者必要的装备,大量的纸质文书方便了丝路旅人的相互联系,也为旅行者提供法律保证。写本让丝绸之路的运营更加迅捷和畅通,可以说,丝绸之路离不开写本,换句话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P125)。这个认识大大突破了学界对丝绸之路内涵的理解。
唐朝势力自唐太宗时代开始深入西域地区,持续统治西域一百多年,在此期间,唐朝的制度文化逐渐进入西域地区,为当地绿洲王国所吸纳。在《兰亭序》的西传与唐代西域的汉文明一讲中,作者通过19世纪末以来库车、和田等地出土的汉语和胡语文书,考察构成中原文化核心内涵的书籍在西域地区的流传。书法作品《兰亭序》不但在敦煌有较多摹本流传,进入西域地区也在和田等地有写本残片出现,这些零星的抄本,虽然只是摹抄或者是习字类的文本,谈不上什么书法艺术的高度,但它们出现在和田这样遥远的沙漠绿洲中,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兰亭序》是以书法为载体的中国文化最根本的范本,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化史都不能不提的杰作,它在塔里木盆地西南隅的于阗地区传抄流行,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渐到西域地区的最好印证(P268)。
四、多学科的交叉与多语种材料的利用
丝绸之路研究和中外关系史一样,涉及内容较广,属于多学科领域,因而即便是通识性质的教材或著作,也需要跨学科视野。《丝路十八讲》的十八个专题,涉及到历史、民族、考古、文学、书法、版本、宗教、地理、美术、语言等多个学科,反映出作者跨学科的研究素养及深厚的学术积累与功力。例如对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积累与运用,对于各类写本、刻本、抄本及书法艺术的收集与整理,对于考古新发现、图像学的追踪与解读,对于民族史、语言学、地理交通等的重视与研究,对于欧美、日本等学界成果的充分吸收等,都是该书学术价值高的一种体现。
多语种材料的利用也是该书的特色。除汉文材料外,也大量使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等材料,除此之外还有敦煌、新疆及中亚等地出土的胡语文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丝路文化交流原貌。例如过去由于材料缺乏,一些学者把粟特的“萨保”(粟特文称s’rtp’w)和印度的“萨薄”(即梵文Sārthavāha)等同起来,其实在印度文献里,“萨薄”意思就是商人首领,即“商主”,而通过对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和西安出土的北周史君墓双语铭文中萨保一词的对音研究,粟特文s’rtp’w则从一个单纯的“商队首领”之义发展为“聚落首领”“一方之长”之义,在古代文献中,“萨保”和“萨薄”是严格区分的,从未混淆过(P138-140)。在论述摩尼教、景教入华及其影响等问题时,利用吐鲁番等地大量发现的中古波斯语、帕提语等的摩尼教文献以及20世纪20年代黄文弼先生获得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1980年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三封粟特文书信等,了解到高昌地区在回鹘西迁之前就有摩尼教徒的存在,回鹘西迁之后,形成了高昌的摩尼教团,由此证明高昌回鹘是9-12世纪世界摩尼教的实际中心(P327)。而通过吐鲁番发现的景教寺院遗址以及大量发现的叙利亚文、粟特文、回鹘文景教文献等,了解到高昌回鹘地区的景教徒主要是粟特人和回鹘人。这些研究丰富了学界对三夷教向东方传播的认知。
此外对于学界有些人提出所谓丝绸之路“通少断多”的问题,作者利用敦煌出土的于阗语行记、德藏吐鲁番出土Ch/U6879粟特语文书、回鹘语文书Ch/U3917等材料,结合出土的汉文文献,发现公元10世纪前后西州回鹘与周围政权如归义军、甘州回鹘、于阗以及葱岭以西地区伊斯兰世界基本保持友好交往,研究指出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大国支撑的官方与民间贸易,但丝路上的每个国家,都不会放弃丝路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因此以各个小国或地方政权为单位,仍然努力推进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以中转贸易的方式,使丝绸之路没有断绝(P400),这也很好回应了一些学者站在中原王朝立场上所持的丝路“通少断多”的判断。作者进一步认为,在丝绸之路上所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一般不会因为政权的对立或割据而中断,总是会有其他途径的沟通,而这恰恰是官方史料很少记录的内容。
除以上几点外,《丝路十八讲》一书考虑到其通识性质,采用了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呈现。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彩色图片,一些来自于各种图册、论著等,更有一部分来自作者亲自走访考察的照片,如景教碑、乾陵蕃王像、汉长城、玉门关、高昌佛寺、广州南海神庙、扬州清真寺,中亚阿弗拉西阿卜遗址、片吉肯特遗址、沙赫里夏勃兹的卡费尔-卡拉古城、伊朗亚兹德琐罗亚斯德寂静塔、意大利教堂的鄂多立克画像、威尼斯马可·波罗故宅“百万之家”等等,而且每一张照片在图版目录中都标注有拍摄日期,使得该书内容更加真实、生动且丰富,这在同类著作中极为少见。
当然丝绸之路的涵盖范围较广,对于大航海时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内容,本书并没有涉及,就如作者所言,这些篇章今后应当单独阐述。另外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思考,例如对“丝绸之路学”的建设问题、整体的“丝绸之路”认识以及对于由丝绸之路而引出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考等也还没有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这也大概是作者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总之,作为以传播通识为主要目标的学术成果,《丝路十八讲》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足以成为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前沿与典范之作,可谓谱写了丝路研究的新华章。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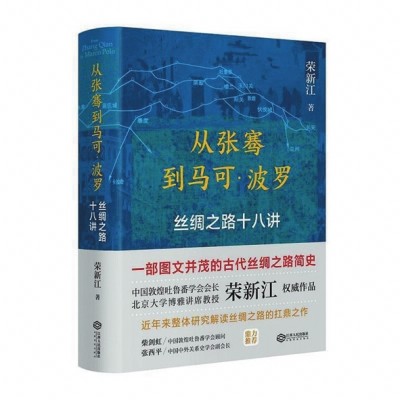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