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村里,就只是去沉浸式地倾听、记录、整理和选择,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如此写来,时代这个词原本很宏阔的词,竟然让我慢慢地觉得很是具体可亲。
■本报记者 舒晋瑜
《宝水》是70后作家乔叶的长篇突围之作。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出来。这个既虚且实的小小村落,是久违了的文学里的中国乡村,它的神经末梢链接着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链接着当下中国的典型乡村样态,也链接着无数人心里的城乡结合部。村子里那些平朴的人们,发散和衍生出诸多清新鲜活的故事,大量丰饶微妙的隐秘在其中暗潮涌动,如同涓涓细流终成江河。
“文学是人学,这是金科玉律,是真理。不论是写什么题材,也不论作品以什么为背景,我聚焦的永远是人情人性和人心,这永远能让我沉醉。”乔叶说,在深入了解乡村的过程中,最能打动她的是人们对老家故土的爱。这爱是很复杂的爱。是欲远离又不舍的爱。回去的人,离开的人,去复来的人,来又走的人,映射着田园和土地对于人们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写《宝水》,你大概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是否对乡村建设也有一个整体的梳理?
乔叶:准备很多,难以备述。简单地说就是素材准备,但细分下来其实有多个层面。这个小说写的是村庄的一年,是个横切面。怎么截取这个横切面,怎么去下这个刀子——庖丁解牛的刀子——我考虑了很久,翻来覆去地想。这个横切面,只要下了刀子,就必然什么都有。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等等,乡村的复杂性必然携带着这些。因为是切近于当下,所以也要特别关注近些年的相关信息,比如近些年乡建思路的变化,乡村妇女生活状况的变化,等等。尽力去实地看,不过更便捷的途径还是收集资料。比如农村问题田野调查报告,民宿经营笔记,地方志,村庄志,老家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关于方言的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太行修路的报道,都有所收集。趁着采风的机会,全国各地的村子我跑了不少,一二十个肯定是有的,没细数过。但尽管如此,也不能说对乡建有整体梳理,只能说对近十年的乡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中华读书报:在掌握大量的素材之后,如何取舍,如何定位,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乔叶:乡村正在发生巨变,我能掌握的尺度和原则就是去捕捉细节。正如再高的山也需要一步一步攀行,我觉得对巨变的书写也必得附丽在具体细节中。密切贴合着人物的情感和命运的细节,都是让我动心的素材。比如小说第二章第二节“以姓氏笔画排序”,当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时,就知道它非常适合写到小说里。这个事讲的是村里的农家乐和民宿都有自己的名号,这些名号都要上到村里立的指示牌上,哪家排上,哪家排下,对于游客而言不过是一眼掠过,但对当事的村民而言非常重要。所以这事虽然极小,却也一定要有个章程,乡建专家孟胡子给的章程就是“以姓氏笔画排序”,孟胡子说农村的事就是这样,该粗就得粗,该细就得细,细起来就得有根儿比羊毛还细的线儿给绷着。你说羊毛轻吧? 那也怕搁到称上称,一称就有斤两。
中华读书报:作品塑造了九奶、老原等一批有血有肉、生动多样的人物形象,讲述的故事都非常鲜活、真实、接地气,这些细节是怎么来的?
乔叶:我获取细节的经验就一条:不预设,比如去村里,就只是去沉浸式地倾听、记录、整理和选择,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确实缺一不可。我个人的体悟还加上了一点听力——像特工一样潜伏在村庄里,窃听人们藏在深处的微妙心事,才有可能和他们同频共振,一起悲喜。如此写来,时代这个词原本很宏阔的词,竟然让我慢慢地觉得很是具体可亲。
中华读书报:创作过程中难度最大的什么?
乔叶:创作难度的类型有多种,写作前的资料准备和驻村体察,写作时的感性沉浸和理性自审,初稿完成后的大局调整和细部精修,还有在前辈的乡村叙事传统中如何确立自己的点,这都是难度。各有各的难度。可以说,纵也是难,横也是难,朝里是难,朝外也是难。还真是不好比出一个最大的。或者说,每一个都是最大的。因为克服不了这一个,可能就没办法往下进行。比如说,对这个题材的总体认识就很难。为什么说写当下难? 因为这个当下的点正在跃动弹跳,难以捕捉,也因为很少有现成的创作经验可做参考。对这些难度,除了耐心去面对,我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是一个笨人,所谓的经验都是笨的经验。
《宝水》有新风尚和新特质,而这新也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我在江南看到特别富裕的乡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富裕的乡村的宗祠都修的一家比一家好,宗祠的存在就是典型的旧,却能和新完美融合,而新旧的彼此映衬也让我觉得格外意味深长。小说里的人物也有新旧之说。评论家李林荣说《宝水》在塑造人物和环境方面最显著的成就不是塑造新人,而是写活了一些熟人和旧人在新的境遇中发生巨大变化的细节和过程。比如地青萍就是个旧人,她带病上场,整宿整宿失眠,饱受无处诉说的自我诅咒恶念的纠缠,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抑郁状态。住到宝水后,情况才逐步好转,但这不是因为她本身有了什么质的变化,而是因为她在宝水村这个新的生活场景中,通过结识和理解身边的各色人等而重建了自己和外界的关系,为自己营造了全新的生存小气候。我觉得写乡村一定会写到旧的部分,那才是乡村之所以为乡村的根本所在。新时代的乡村固然有新,但旧也在,且新和旧是相依相偎,相辅相成的。新有新的可喜,也有焦虑和浮躁,旧有旧有的陈腐,也有绵长和厚重。
中华读书报:离开乡村二十多年再写《宝水》,你觉得这种距离感对创作是有益的吗?
乔叶:来北京已经两年有余,尽管之前也常来北京出差和学习,但客居和定居的体验感受还是有本质的不同,地理视野的多维度似乎让我原本的乡土性更鲜明了些。我的写作状态也发生了改变,这两年来也在不断调整中,尽力使得写《宝水》时气息充盈和饱满。我写作长篇时的习惯是:既要沉浸其中,也要不断抽离。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要感谢北京。“故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忘记了这句话从何听起,却一直刻在了记忆中。自从工作调动到了北京,在地理意义上距离故乡越来越远之后,就更深地理解了这句话。人的心上如果长有眼睛的话,心上的眼睛如果也会老花的话,也许确实需要偶尔把故乡放到适当远的距离,才能够更清晰地聚焦它,更真切地看到它——在河南写《宝水》时一直在迷雾中,尽管基本的东西都有,却不够清晰,在北京这两年里写着写着却突感清晰起来。如果没来北京,这个小说可能不是这个面貌。现在回头去想,北京和故乡有接近性,同时又有差异感,这个尺度还挺美妙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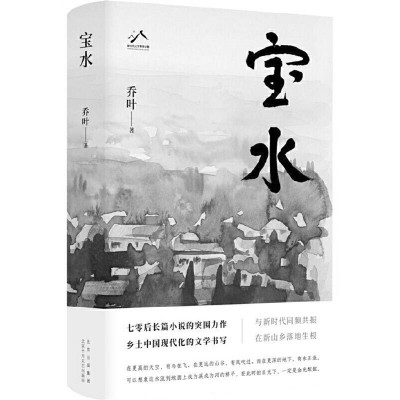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