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
《缪泾人》是何庆华写给故乡缪泾的一束“情书”。各篇以人物命运的展开为主线,通过写他们的日常生活,交织进缪泾一带的社会环境、乡风民俗,书中涉及到的缪泾地方的风景、风俗,人物对白,以及民众的生活方式,都带有浓郁的江南乡土气息。但《缪泾人》不同于一般乡土小说的地方在于,它并不着力于凸显城乡对立,或以“乡”作为批判现代文明的武器。而只是用一支饱蘸深情的笔,描写了时代转型期江南农村社会几个命运浮沉不定的个体,以人带事,以人物命运折射时代沧桑变迁,于其间自然流露她的价值理想。
书中人物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穷闾陋巷中人,如《马桶西施》《虎姐》《半夜猪叫》中的主人公,他们都是无法在历史上留痕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还有一类则带有一定的文化符号色彩。如《蓝月亮》中的缪根生象征大爱,《“天鹅”与“呆鹅”》中的“天鹅”之代表美,《老克拉》中的老克拉象征对文明世界的向往,《小焉》中的小焉俨然苏州评弹的化身,这些人物或有现实中的原型,带有相当的写实成分,但作者显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理想,而在事实上形成价值抒写,她敏于捕捉那些身处幽暗角落的小人物的悲喜,也对探讨他们的命运感到非同一般的兴味。这里面不仅仅有“共情”,因为共情仅仅是代入情绪、感同身受,何庆华对人物命运的理解、熨帖,又带有几分过来人的审视与悲悯。
《马桶西施》一篇有点儿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的味道,但不同于赵树理以理想置换真实的写法,何庆华一方面并未回避造成琴子悲剧命运的外在原因,另一方面以奇兀之笔写了这对夫妇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生命中的苦难。从小说结尾处不乏赞美的笔调,我们可以读到何庆华“唯情”的价值取向。我们常说“泥淖中的温暖”,值得赞美的是“温暖”而非“泥淖”,但《马桶西施》提示我们,对某一类小人物来说,有时“温暖”恰恰与“泥淖”共生,彼此几乎无法分割;《半夜猪叫》写乡下的女屠夫麻姑。麻姑活着不易,出生在苦难重重的家庭,杀猪是她的生存之“技”,也是她的生存之“道”。“拿着屠刀,立地成佛”,何庆华竟将麻姑的杀猪写出了庄严的味道。汪曾祺在《受戒》里写荸荠庵和尚们杀猪念经,使我们感到烟火俗世的幽默情味;麻姑杀猪也念经,但流露出的却是乡村小人物的生存之涩味。然而生存本身何其庄严,沈从文就曾描写过一个老水手数钱的执着神态,以“忠实庄严”二字形容湘西河滩上的那些拉船人。麻姑杀猪的庄严是与之仿佛的;《虎姐》是整部小说集里非常出色的一篇。“虎姐”这个人物的命运轨迹是一个圆,她从乡村走出,在城里转了一圈,又回到缪泾。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以来,“离乡-返乡”是不断被书写的乡土小说母题,如鲁迅一般的启蒙者的返乡故事的结局是一个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如沈从文一般的返乡抒写,则是以建构精神故乡的方式返乡。“虎姐”的返乡无疑属于后一种返乡,这毋宁是作者立场的一种表达:那能够治愈个体心灵创伤的力量,能够疗救文明弊病的药方,都始终需要回到生命的源头、生活的本相中去寻找。
以上的几篇小人物志都是关于“泥淖”的故事,写了这几个人物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以一种民间的自洽逻辑去面对“泥淖”,守护本心。另外几篇中亦有对困境的表现,但更多表达了作者对于理想的追问。《“天鹅”与“呆鹅”》叙事方面略单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含了何庆华对于美、自由、尊严与爱的理解。美丽的“天鹅”因爱而折翼,而放下自尊,又因对美、自由的执着而重获勇气,冲出藩篱。《最后的老克拉》这篇小说让我想到金宇澄的小说《繁花》里的“姝华”一类人物。老克拉的“晒被絮”是非常成功的一处细节描写。不同于其它几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老克拉”本质上不属于“缪泾”,但他的故事构成了“缪泾”沧桑历史的一部分。“老克拉”身在缪泾而怀念向往一个更广阔的文明世界,何庆华充满诗意的乡愁抒写并没有掩盖这一点,这是她比较深刻的地方,这也使得“缪泾”以更为完整立体的面貌呈现于文本。
《小焉》是《缪泾人》中的压轴之作。诚如范培松教授在序言里写的,《小焉》和《虎姐》是何庆华“文化理想的两根重要精神支柱”。“虎姐”和“小焉”身份不同,一为进城务工的乡下姑娘,一为小镇评弹演员,但她们都可以说是逐梦者。虎姐梦想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过上富足的城市生活,小焉热爱评弹艺术,希望不仅能靠评弹立足,也能将这一艺术形式真正传承下去。而她们的梦想志向遭遇到了幻灭失落。《小焉》的叙事是典型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小焉、唐伯君这一支写的是评弹行业的衰落,萧师傅那一支写的是旗袍手工艺的没落。这两支在小说结尾处得以汇合,本是一个算得上圆满的结局,但小焉却倒了嗓子,永远地告别了评弹,这就使这个故事染上了几分悲情色彩。
《缪泾人》无论写哪类人物,都植根于江南乡村与江南社会,因而显现出鲜明的地方性,这也是这部小说集的诗性之所寄。缪泾是典型的江南乡村,作者的一支笔旖旎摇曳,写出了这个地方风物的柔美宜人。像《虎姐》中有大段的乡土风景画描写,春夏秋冬,各有各景,虽然时间流逝,人事浮躁、动荡、变迁,而江南风物则仿佛永恒如斯。她写乡下的春天:“风吹一口气,湖面就皱了,闪着无数的珠贝。鸭子、呆鹅从竹园里摇摇摆摆走出来,一不小心脚底踩到了春笋的芽尖。它们一律用喙蘸蘸水,像书法家甩掉毛笔上的水,它们扑腾进碧水里,然后开始泼墨画,吸水吐水,荡出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或把头探到水底,亮出嫩黄的脚蹼,在跳水上芭蕾。”文字具有灵动的诗意。她笔下的缪泾乡民养殖、播种、莳秧、斫稻……体现了吴地典型的稻作文化特点;有些乡民甚至保留着旧日的礼俗,如元宵节通过厕所神“坑三姑娘”占卜年景、收成、婚配、吉凶……也都很具江南民俗文化意味。
或也是得益于对记录真实的偏好,何庆华对乡风民俗有一种“留影”般的意识。在数码复制、电子复制的时代,“留影”变成一种很容易也很便捷的事情。但正像本雅明在《摄影小史》里启示我们的,复制时代的“摄影”实际上已很难再现过去时光的“灵韵”,那是一种交织着神性的、完满的体验。何庆华则试图还原缪泾水乡过去的“灵韵”。她在这当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两种方法:一是穿插了不少民歌、弹词及富有年代感的流行歌词。粗略统计了一下,集中七篇小说,相关引用多达二十多处。这部分引用与各篇叙事主体水乳交融,在塑造人物、烘托意境方面都大有助益,而更重要的是将一种鲜活的地方性深植在了文本当中。《小焉》不必说了,《秋思》《莺莺操琴》《牡丹亭·游园惊梦》《紫鹃夜叹》等弹词的引入本就是一种间离,因为这些弹词对于今天的一般读者非常陌生,带有过去岁月的神秘感,同时也是无所不在的文化符号,提示我们《小焉》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故事。而像《马桶西施》一开篇就引用了双凤山歌,《虎姐》里也有一段山歌。双凤山歌是吴歌的一脉,民歌的一种,是人们在田野劳动或抒发情感时即兴演唱的歌曲。山歌中的意象是典型的江南风物,民歌中的情感也契合小说的价值诉求。这些地方性民歌的引入,或使我们想起上个世纪废名、沈从文等乡土小说家在创作中对民间资源的化用,何庆华的写作无疑接续了20世纪的乡土小说传统,但又多了一些时代特色。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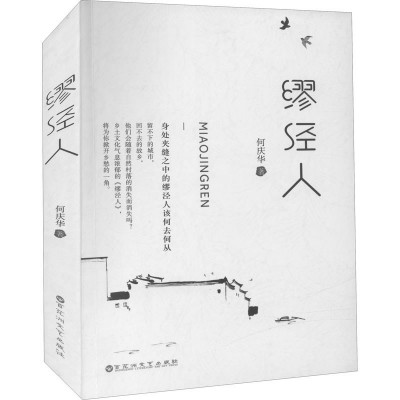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