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 张可煜
1937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研究了巴西中部的南比库拉印第安人,想“寻找一个最接近简单形式的社会”,但最终只发现了人类。而我的工作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经验方向相反,我是去研究那些因身体残障而丧失某些能力的人,像南比库拉人那样为生存而挣扎的一类人,我发现的却是社会。像列维-斯特劳斯描述的印第安人一样,残疾人是“边缘”人,研究他们在社会边缘的脆弱地位可以让我们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全貌。
罗伯特 ·F.墨菲:《静默之身——残障人士的不平凡世界》,页5
读这段引文,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罗伯特·F.墨菲(Robert F. Mur⁃phy,1924-1990)的自况或自信,将自己与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人类学 家 列 维 - 斯 特 劳 斯 (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 相 提 并论;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也点出了人类学研究进路上的一个重要差别:从社会发现人,或是从人发现社会。他认为,在列维-斯特劳斯试图寻找一种最基本/原初的社会的亚马逊之旅中,所延续的是涂尔干模式的理想,希望寻找一种人类生存的替代形式。不过,列维-斯特劳斯最终看到的是在不同形式之下的共同心智结构,是人之为人的思维方式。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经验相反,墨菲认为自己的思考路径是从人身上发现社会。
我们当然应当还记得卢梭在《爱弥儿》里的警示:“应该通过人来研究社会,也经由社会来研究人;想把政治与道德割裂开来的人,对二者都将永远一无所知。”不过,需要承认的是,在实际思考和写作中,人类学者事实上难以避免地会强调某一个方面或路径。
与墨菲的情况类似,凯博文(Arthur Kleinman,1941-)书写《照护》(The Soul of Care)的过程也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的研究性写作。或者说,他以照护者和研究者的共同身份写了这本书。凯博文早期主要做精神疾病研究,但在晚年的时候,由于自身经验,特别是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太太十年之久,从而更多关注日常照护问题。在太太去世以后,凯博文完成了The Soul ofCare这本书,出版后的次年,中文版面世。
需要强调的是,很多时候都有一个陷阱,就是由人出发看社会的过程中,容易忽略掉政治社会结构,落入个体主义。的确有这样的陷阱,但是它不一定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因为我们所说的“具体的人”不等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个体(individual),而是具有内在社会性的关系性或人格性的人(per⁃son);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鸡零狗碎的碎片化的研究,而完全有可能进入一种人以及人类意义上的宏大结论。在我们看来,墨菲和凯博文的研究都呈现了这种可能性。
此外,“由具体的人看社会”也意味着对自己的关注,对自身的关注、对身体的关注、对附近的关注、对真实生活的关注,这就意味着这样的研究是天然自反性的研究,也就是在研究过程当中一直把自己视作被研究者。现代社会科学一个非常重大的自我限制,就是常常把自己当成是置身事外的人,意味着是我们是作为研究者去研究一个事情,而不在被研究群体当中。就这点而言,我们在阅读墨菲的作品时,能够看到他的文字所产生的力量。不仅仅是智识上的恍然大悟,也包含情感上的唤起、共鸣和投入。
回到墨菲其人。坦白说,在中文世界,即使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人对他的熟悉程度也不太高,之前他唯一译成中文的作品是其入门性的教材《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1/2009)。其实,他曾经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在不到50岁的时候确诊脊髓癌,逐渐瘫痪,后近20年基本上在轮椅上度过。1990年去世,年仅66岁。
1974年,在确诊脊髓癌后,墨菲与他的太太 尤 兰达(Yolanda Murphy) 合 著 的 Women of the Forest出版。1979年,他撰写的人类学教材《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Cultural and Social Anthropolo⁃gy)出版,也就是前面提到商务印书馆译介的那本书。1987年,《静默之身》(The Body Silent)出版,仅仅三年之后他就与世长辞。《静默之身》基本上是以个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研究,墨菲同时作为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探讨残障者的生活世界。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定义了我们所知道的墨菲:一位在轮椅上完成自传式民族志的人类学家。在这个意义上,他早年在亚马逊所做的蒙杜鲁库人研究尽管也可以使其位列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英雄式的人类学家”,但他晚年基于个人苦痛而完成的这本民族志才真正让他成为不仅仅只是一位人类学家,更是一位敢于面对和理解苦难的“英雄”。
人借由感官和躯体感知自我和世界,健全者基于自己健康的身体想象社会,把它当作前置在命运中的假设。直到身体生病,它不再是理所当然的物什。残障意味着什么? 成为残障者意味着什么? 死亡是否比残障更可取? 墨菲将自己的生活碎片、感受和情绪连缀起来,钩出情境中的意义之网,言说《静默之身》。
1972年,墨菲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刚卸任系主任一职。48岁的他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前景明朗,认为自己正处于美国中产阶级男性的中年黄金期。然而随后,他注意到自己的肌肉出现局部痉挛。身体的存在从无形到有影,从无意识的主体变为有意识的客体。在全书的第一部分中,墨菲从三条线索来描述自己“渐进式残疾”的过程:身体、心理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他描述了身体症状伊始、病情发展、确诊脊髓肿瘤与康复训练的经历。疾病所带来的不仅是病痛,更是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难以言喻的偶然性。这种精神负担影响他对世界的理解、建构,以及自我认知。在住院之际,他反思患者作为社会人的义务与责任。患者失去了做选择的自由,被剥夺作为“患者”之外的所有社会角色,陷入社会关系断裂的困境。疾病意味着失序,失序让人感到不安。
病痛细密地缠绕他的生活,他分析自己的个人生活史,从而理解自己面对苦痛的反应。童年时期遭遇的大萧条和原生家庭的破裂带给他不安全感,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天主教家庭成长的经历带给他自我克制的能力。他在战时海军服役时期养成了饮酒习惯,退役后他成为学者,酗酒问题几乎让他的生活崩裂,于是他选择戒酒。他将自己后来的残疾与这段经历类比,理解其中共同包含的逃避、遗忘、分离和求死意欲。
在全书的第二部分,他阐述了残障者身体、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他指出:“残障人士的心灵发生了转变,由社会的冗余变更成了一种准人类的东西……他们受到身体疾病的折磨,这种疾病转而成为心性上的癌症,由此社会关系也会出现病态。他们在世界上生存的基本条件发生了转变,他们在本地做了异乡人,甚至成了流亡者。”自尊的根本丧失,受损感的自我习得,导向的是被动或者主动的社交隔离。退缩带来孤独,自我价值感的降低和羞愧情绪的向内蔓延。与此同时,墨菲反思了自己作为主流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何以支配他的自我意识,在他患病后,一切关乎“我是谁”的回答被残障者身份支配,带来弥散的愤怒。由此,墨菲指出,残障者身心的隔离与社会文化、环境和体系的排斥密不可分。换言之,身体的残障,不仅是个人处境,更是社会问题,因为残障之身指向的乃是社会之人。
由此,墨菲援引社会运动和历史法案,描述现实世界何以在他们的身体和社会中筑起了歧视高墙。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版,当时的美国政府在进行一场残酷的运动:在没有事先告知或者经由医疗审查的情况下,临时解雇残障者,以此来减少享受社会保障的残障者数量。与此同时,当时的美国社会残障者还面临着社会保障上的困境,如果要获得医保,必须接受相关保险或者补充保障收入,但是如果要获得医疗补助资格,则必须是贫困的。残障者在就业上困境重重。种种问题,都旨在说明残障问题既不是单纯的身体问题,甚至也不是个人或家庭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制度性或结构性的问题。
在全书的最后一部分,墨菲描述了自己陷入完全瘫痪的过程,他直接其称之为一种社会状态。墨菲说,“残障者是人类状况的隐喻,因为这不仅是身体功能的丧失,而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存在状态。”
“一个(残障或瘫痪的)人如果死了,会更好吗?”他以自己对死亡的犹疑与生的坚定,以最后的生命否定了这个问题。墨菲认为,残障者抵抗孤立、依赖、失序……进入内在自我和最终否定,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生命的愤怒表达。他鼓励残障者以及所有人,通过对自我和环境的重新发现,突破文化层面的藩篱,超越生命本身的价值。
在评估自己在这项基于自身残障体验的研究和写作中的角色时,墨菲说,“瘫痪是生命和无序状态的一种不平衡,我在探索这个关系的过程中扮演了萨满的角色,试图通过将其放在神话和信仰的背景中,把病人和疾病进行调和……我的任务与萨满所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寻求治疗,而是强调理解。”也就是说,他所希望做的,不仅是“治愈”,而是“理解”,理解残障对于人类处境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菲所做的,或许还不完全只是从人发现社会,而是进一步由社会中的人看到了人类的普遍性问题。
换言之,虽然他是在具体的地方写的一个具体的人,可是这是真正的人、活生生的人,而且是可以触及到社会性的存在和人类的话题。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可以落入在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具体的人上面的一种温情的知识。不仅由具体的人进到社会,进一步说,还可以到具体的人及人类。即对人的研究、对人类的研究,而这真正不断地回到了人类学学科自诩的目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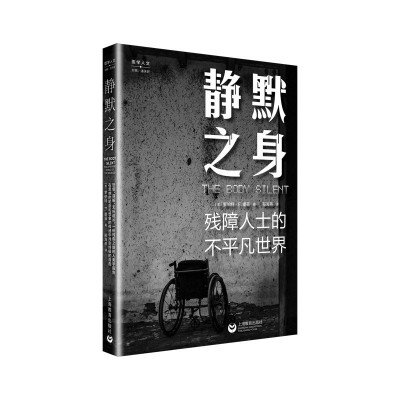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