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社会学的一场奇妙相遇,造就了一个关于门卫的独特故事。
当我们提到门卫时,脑海里往往不自觉地浮现出“保安制服”“门卫岗亭”等印象。或许对于生活在2022年的我们来说,更加习以为常的是包含了门卫服务的居民小区物业,“物业-业主”而不是“门卫-住户”乃我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符号。
如果将时间拨回二十多年前20世纪末的纽约,公寓带有门卫(doorman)并不是常态化的社会现象,而是高收入群体高档住所的某种标志。空间距离亲密接近而社会距离遥远区隔的门卫-住户关系出现了。门卫成为了住户日常生活里每天出现却又常被忽视的寻常存在,然而在吸收运用人类学方法的社会学家彼得·比尔曼的现代城市民族志叙事里,一切变得不寻常起来。
门卫这一“职业性工人阶级”是一枚折射美国社会阶级问题复杂性的棱镜。比尔曼既是这枚棱镜的观察者,又用他独特的“语言概念之网”捕捉并塑造了它。
这一成果来自于一门课程教学。在比尔曼的带领下,学生们接触到了社会学田野研究的所有阶段和过程,总计完成了应答率达到63%的共计上千小时的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访谈资料。之后要做的便是用这些宝贵的食材烹饪出一道学术美食。这恰是一项社会科学研究的乐趣与难处所在。作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深刻也生动地揭示出了一个隐蔽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世界。
为什么门卫这份工作既容易获得又难以获得? 门卫在讲述自己为何当上门卫时,几乎都归因于朋友或亲属告知的偶然机会。这种“弱/非正式关系的优势”,让获得门卫这份工作变得轻松。然而,比尔曼却发现这样的“机会叙事方式”恰是“社会结构”对个体经验的塑造方式。也就是说,沿着“种族、族群断层线”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社会结构,主导了工作信息的传递轨道,使得某些人/族群易于获得工作机会,但同时也导致了其他人/族群失去了公平地获得这些工作的机会。比尔曼用他手术刀般无情的理论,剖析出了社会结构运作的现实结果。这也从法律之外的视角,更加真切地告诉我们反就业歧视与促进机会平等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何等重要。
除此之外,同样令人疑惑的问题还有:美国门卫的收入可以轻松超过70%的美国人,但为什么这份职业连门卫群体自身都不认可呢? 另一个更加直观的数据是,门卫职业的直系亲属传承率连30%都不到,这意味着大多数门卫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他们难道不想自己的后代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吗?
一位受访门卫说出了整本书里最令人惊心的话:“门口这里就像是动物园。而我们则是被展示的动物。”对于住户而言,门卫是每天都要接触的活生生的人,却又是“社会意义上的死者”。比尔曼指出:“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的社会学张力”往往是通过否定他者的社会身份而被简单粗暴地解决的,比如奴隶制。这种方式由来已久,且有着诸多“现代变种”。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也指出了这里的关键:仆人/奴隶(我们现今所言的社会底层人群),他们消耗自身生命的劳动产出是“非生产性的”,即“消费他们的劳动所换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主人的自由”。
不仅如此,身着干净制服的门卫,每日接受“仪式性污染(ritual pollution)”、承受混乱无序,成为街道脏污混乱与公寓整洁有序之间的阻挡者,从而维持了住户们的社会地位。这也印证了人类学研究所表明的“职业声望与仪式性纯洁”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你是门卫,你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门卫,还是更期待他们成为自己所服务的住户呢? 书中并没有谈论到和社会阶级地位、工作职业无必然关联的快乐和幸福。仅根据书本,我们无法判断比尔曼和学生们是否询问过门 卫们“你感 到幸福吗”。提到积极情感,我们还可以从比尔曼回答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时,看到社会学解释的某种局限性。“为什么有门卫的公寓更少出现安全问题呢?”他的结论是:越是注重安全的住户,越倾向于选择有门卫的公寓,这不过是住户“自证预言”。但这显然忽视了门卫提供给住户的“安全感”。在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结构中,“安全需要”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正因如此,恰是门卫的存在本身,让住户接收到了“带门卫的公寓是更安全”的预先信号,“自证预言”才会启动。
比尔曼带给读者的启发还不限于此。如果说人类学或心理学更多是以进入门卫的心灵、所处境地的代入视角,来理解和阐释他们的感受与言行;那么社会学便是基于前者并做到跳出身临其境,进而给出更加全面、相对宏观的理论解释模型。这体现为比尔曼对门卫-住户关系与服务员-顾客关系的比较,比起后者,前者中存在着更为明显的“职业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门卫和一般服务员并不一样,他们面对的不是大多数只见一次的顾客,而是长期相处的住户。门卫按照职业主义要求而必须在常规工作中平等地服务任何住户,但为了让住户满意而又必须提供长期的个性化服务。比如,有些住户对是否需要门卫在每次有访客时都通知他时并没有特别需求,这时门卫就可以说“那我每次都通知您可以吗”,进而实现对住户行为习惯的塑造。
门卫对住户行为的塑造能力,还体现在“圣诞节奖金”数额、支付方式的确定上。如果你是一位受到门卫更多照顾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你会给更多的奖金吗? 那如果你是长期外出工作而较少居住在公寓、收入很高的金融工作者,你会给多少呢? 空间距离和个性化服务对情感会产生不同效果,这一旦和住户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道德感等情况碰撞,那么“如何给圣诞节奖金”就成了一场每年都上演的社交大秀。或是为了少给但不愿成为给最少的那一个,或是想多给但又不愿与其他住户关系恶化,住户们频繁打探其他人给多少来决定自己给多少。因而出现了一个奇妙的共同特点:“说出的金额”总是比“实际给的金额”更低。
当然,只是陈述这一场社交大秀里的复杂互动关系远远不够,社会学家的看家本领便是抽象出一个具备解释此复杂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模型。比尔曼解释道:门卫们与住户们之间通过协商彼此边界、维持相互关系、理解(或误解)特定阶级的符号和标识,建立起了一个互相塑造而非单向决定的立体社会网络空间/协商秩序(negotiate order),并且他们自己同样被编织进这一社会网络空间之中。如此而言,可以反向塑造住户的门卫,真的是“社会意义上的死者”吗? 若回到我们的当下,在飞速实现城镇化的中国,城市居民小区里物业保安人员随处可见。他们管理性是否强于服务性呢? 他们还是易于被忽视的日常工作者吗? 这些都值得深思。
改变老式民族志的比尔曼,就像是给社会学的宏大视野,添加了诸多显微镜,让我们发现未曾意识到的、却深刻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隐形社会结构。
或许,人类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可以不断创造“有意义的符号”,编织“概念之网”,“捕捉”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我们,都是社会舞台的搭建者、文明的创造者,也是被社会和文明所塑造的表演者,或好或坏地扮演着自己的各类身份角色,过着寻常亦不寻常的一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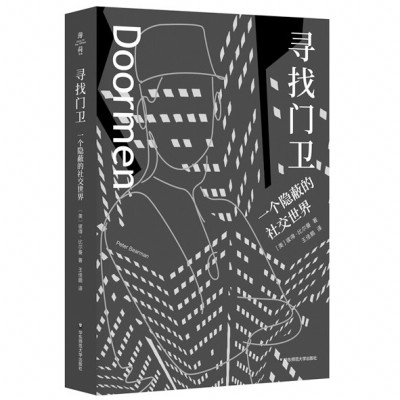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