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作者而言,手中的笔就像是火把,要有意识地去发掘那些幽微人性的内部。对于批评家而言,它则要去照亮书本里的幽暗处、书本里被忽略的山山水水。
在日前举行的《持微火者》修订版首发式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评价张莉的文字像“看着荷塘里活蹦乱跳的鱼在跳跃”。
张莉很喜欢这个比喻。不是因为夸奖,而是这个比喻很形象,因为写作这部书的过程对她来说,的确是全情投入的状态。今年8月,张莉的《小说风景》获得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这是鲁迅文学奖在时隔12年后,再次授予一位女性批评家。
中华读书报:《小说风景》源自在《小说评论》上开设的“重读现代中国故事”专栏,起意是什么?
张莉: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是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重读中国一百年来的经典小说,并在其中找到我们这个时代新的阅读经典的方法。我觉得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在当下的土壤中,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而经典就是要常读常新。为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作家、这部作品依然感兴趣,其中一定有某种密码需要我们去解开。所以,写作《小说风景》的过程,就是在寻找、破译时代密码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在这一系列文章中,重读经典文本的同时,你也在思考当下文学创作的经验和问题。阅读你的作品,能感受到你其实是把自己的生命经验跟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张莉:在理解作品时,不仅仅要找到我们时代的读法,还要去思考“它是如何写的”“为什么这部作品在当时会引起广泛注意”以及“为什么它成为经典”等问题。比如说,萧红何以在那个时候写出《呼兰河传》? 鲁迅何以在那个时候写出《祝福》? 思考这些问题,要投入自己对生命经验、情感经验和人的理解。可能我是一个动情动意的写作者,在面对一个触动我的写作对象时,会格外动情。因为动了情,所以我在写评论时,也特别希望把自己被打动的那一瞬传递给别人。但我现在觉得,这样的写作特别耗神,对写作者的消耗也很大。
在这里要提一下《持微火者》,它是我最动情的一部作品。“持微火者”这个名字其来有自,是受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启发。伍尔夫曾在她的作品里写到过那些女性创作者,她们在写作时犹如持着一束火把,而火把组成的微火,则照亮了那些在历史中被尘埃掩埋的面孔。这一意象使我十分着迷,对于写作者而言,手中的笔就像是火把,要有意识地去发掘那些幽微人性的内部。对于批评家而言,它则要去照亮书本里的幽暗处、书本里被忽略的山山水水。在内心深处,我渴望成为文学世界里的“持微火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中华读书报:你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第一代女作家,这是你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开端? 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张莉:这要从二十年前说起。当年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以女学生为例,讨论新教育、新媒体与现代爱情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那时候我就注意到,女学生命运的变化和整个社会的变革有很大关系,也认识到女性解放之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而且,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开始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女性解放,就没有我今天的生活。也就是说,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女性命运与我个人生命的连接。所以,后来的博士选题也是“自然的”选择,我想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去探索100年前的女作家们是如何成为女作家的,我希望从文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出发,讨论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女作家如何写作,她们的作品如何生成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如此说来,从事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的契机应该追溯到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它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女性生活、女性解放和女性写作的关系,也看到了“无数的她”。
中华读书报:强调女性文学和女性视角,对你的学术研究会有怎样的影响?
张莉:我觉得我不是在强调女性视角和女性文学,而是说以前我们的研究领域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女性视角,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基于女性读者的阅读能和基于男性读者的阅读站在共同的层面。我想说的是,女性视角不是在“被强调”,而是本就应该有一个女性视角存在,这对于研究者和创作者而言都非常重要。以往,在做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我没有特别强调过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但是,最近几年来,我深刻认识到我的女性身份对我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我开始认取我的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女性文学研究应该与我们的时代发生一种遥相呼应的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既然我看到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那么,我就尝试做吧。
中华读书报:能否结合你的《小说风景》谈谈具体的批评方法?
张莉:所谓女性视角,并非将女性简单地作为受害者去理解,也不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批判作品,在我看来,文本里每一个女性都不是完全的受害者,也并非天生就是束手就擒的人。她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扭转自己的不幸。比如《小说风景》提到,在《萧萧》里,萧萧是有反抗的,她最大的反抗就是不认同他人的讲述。“女学生”在老祖父的讲述里被扭曲、变形,作为听众的萧萧却没有被迷惑。小说中,她一直幻想自己有一天会像女学生一样生活。所以你看,即使懵懂无知,小说中的萧萧也试图从那个怪谈中挣脱出来,从那个百孔千疮的故事里获得启悟和滋养。尤其在被诱惑怀孕后,萧萧想到的是要逃跑,去做女学生,过另一种生活。没能离开是她的命运,而想离开却是她主体性的表达。在鲁迅的《祝福》里,祥林嫂其实也在努力,但因为外在力量太强大,她无路可去。在《小说风景》里,我想将那些喑哑的、看起来生命没有光泽的女性还原为有主体性的女性,她有她的力量,她做了她在那个时候能做的事情,她的悲剧在于那个社会没有给她更多的出路,是出路的狭窄影响了她对自己未来的想象。她不是蒙昧的“他者”。
中华读书报:你曾经谈到,“在我心目中,优秀批评家首先是‘普通读者’,他(她)有情怀,面对社会的人间情怀,面对作品的文学情怀。他(她)的批评文字不是冷冰冰的铁板一块,它有温度、有情感、有个性、有发现。优秀的批评家是文学的知音,是作品的知音,是作家的知音。”这一批评观是如何形成的?
张莉:这个批评观的形成与伍尔夫有关,我注意到她的关于普通读者的说法时,心有戚戚。当然还有我的学术导师们的影响。在我眼里,文学批评家其实就是摆渡人,是在文本和作家之间建立桥梁的写作者。我把自己的评论文章作为与读者的一种分享,我想和他们一起分享我的所学、所感。我觉得这种分享的意识对普通读者身份的体认很重要。
中华读书报:你的评论文章,不乏真知灼见的锐气,同时也有体贴和关怀。你觉得自己的评论风格的形成,和性格有关系吗?
张莉:批评风格的确与性格有关。我们家里是三姐妹,我和两位妹妹一起成长的经历深刻塑造了我。坦率说,我是喜欢理解他人、喜欢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这看起来是优点,但生活中也有不少困扰。比如常常顾左右而言他、不敢直接面对别人,不敢说不好听的话等等。如果说我的文章里还有一些锐气,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我在有意克服自己身上的这些缺点。也正因如此,我一直要求自己的文字要有锋芒、有态度,要向鲁迅先生学习,努力向“不合众嚣,独具我见”的境界靠得更近。二十年前,还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我的导师就跟我说过,文章一定要有所见识,不要让自己成为生产“学术垃圾”的人。那这是愿景,我可能永远达不到,但我希望自己向这个目标努力。
中华读书报:在你的批评生涯中,有无“看走眼”或把握不准的,遇到这种情况是回避还是迎难而上?
张莉:我写的都是我当时喜欢的作品,把握不住的作品或者作家我不会动笔。很多人会说“深悔少作”,我自己倒觉得一路走来所写下的那些文章,也算是生命历程的见证。人生脚印嘛,有深有浅很正常,要学着接纳自己所有的作品。孙犁先生说过一句话,“文艺虽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我对“天听民听”这句话感触很深,常常对自己说,写文学批评要对着自己的文学之心来写,要对得起读者对自己的审美信任。这个世界上,读者的审美信任太珍贵了,批评家要谨慎,不妄言。如果当初写评论是真情流露、不违我心,那么未来便可以内心平静对待自己当年的文字。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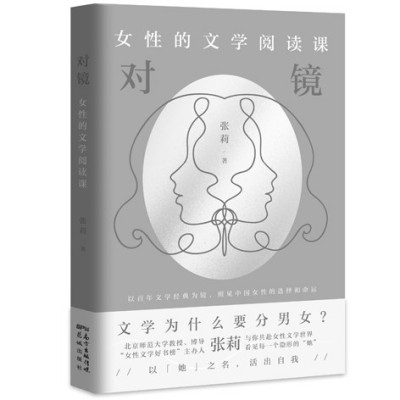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