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泰先生的庄子研究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可谓其一生学问的最重要方面。其庄子研究不仅是20世纪中国庄学研究的巅峰之作,也是两千年庄子学史上的典范之作,是可以与郭象、船山等人的庄学并峙的大文字。他之所以能够提供这样一个传世的作品,一方面与其出入世变的动荡经历、时代变化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其以学问修身应世的经历相关。
一、庄子之学的定位:孔颜之传
1932年、1934年、1935年,钟泰先生先后在《之江学报》发表了《读庄偶记(内篇)》《读庄偶记(外篇)》《读庄偶记(杂篇)》。1948年又在《读书通讯》发表了《读庄发例》。可以说,在1930—1940年代,钟泰已经达成了对庄子的一些基本认识。首先是庄子上继孔门,而有得于六经之传,因而读庄解庄都离不开六经;读经之法亦即读庄子之法;其次,六经中的易学与庄子关联尤其深密,读庄子尤需通《易》;再次,读庄子必先通老子。复此,读庄当以内篇为主,以外杂篇为辅,外篇杂篇可视为内七篇之注脚。在思想取向上,庄学以“游”为宗旨:《天下篇》自序其学“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 生与? 天地并与,神明往与! 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说之”,此三十六言者,可以约而言之,一“游”字而已。“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再次点明“游”字。“游”可谓庄子之道,能通达“游”之义,于庄子之学殆思过半矣。
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钟泰就提出庄子之学兼孔老两家之传,1930—1940年代,犹保留此见。但到了1963年的《庄子发微》,他提出,庄子之学渊源自孔子,而尤于孔子之门颜子之学为独契。庄子既为孔门颜子一派之传,则与孟子之传自曾子一派者,虽同时不相闻,而学则足以并峙。对于孔子之学的理解,则重在孔子晚年之易学与春秋学,此为孔子之两大学问,义理又相为表里。庄子于逍遥游阐《易》之缊,于《齐物论》则深明《春秋》之宏旨。如果说,孔子本乎先王之志,而为经世之书,为中华文明奠基,则庄子秉承孔子之易学与春秋学,而深有所得。
为中华文明奠基的《易》与《春秋》之学,也规整了钟泰本人学问的版图。1957年7月15日文史馆表格上,钟泰写自己的研究领域为文史组《易》《春秋》、宋明理学。而庄子之学竟然不在其列,看起来匪夷所思。钟泰的春秋学代表作是《春秋正言断辞三传参》(1966),这是其对整合平衡三传而理解《春秋》的著作。虽然易学为其一生的学问,但并没有此类作品问世。其实,庄子之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其易学之用,钟泰并非直接撰写易学作品,明易学之体,但将“寓言十九”的《庄子》视为易象,以《易》解《庄》,即从易之用而明易之体。就此而言,庄学的背景则是易学,此为钟泰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强调读庄必须通《易》的原因。兹举一例,《庄子·达生》有谓:“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历代解释纷纭,均难令人信服。而钟泰《庄子发微》独以易经巽卦解之,以为:“善养生若牧羊然,取譬于牧羊者,羊之性柔而狠,柔则易退,狠则易进,故于卦巽为羊,又为进退,意可知也。郭注:‘鞭其后者,去其不及也。’不知不及于此者,实由过于彼。如单豹不知防虎,其不及也,而根在离群独处,故‘不与民共利’,则其过也。张毅不知慎疾,其不及也,而根在媚世而卑损,故‘高门县薄’,过而不趋,则其过也。是以视其后者而鞭之,去其不及,这个所以救其过也。当合二义观之始全。”此解可以破千古之惑。方勇教授《庄子学史》(2017年增订版)也注意到这一例子。仅此一例,就可见钟泰庄学即为易学之用。
方勇教授在其《庄子学史》中说:钟泰晚年在学术上所造之境到了纵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能在庄子内部以及庄子与其他文献之间进行信手拈来的沟通互联,所立诸解,也都发人之所未发;钟泰庄子之学,历经前后三十多年跨度,见地更为落实,学术境界日臻深微广大,每为后人难以企及。然而,后期钟泰将庄子判为孔颜嫡传,与其早期以出入孔老定位庄子之学有所不同,且很难被现代学者们所接受。我本人能够理解现代学者们的疑虑。但我认为钟泰之意,仍然可以在隐喻的意义上成立。钟泰以庄子学承孔子,而孔子则为中华文明的人格化符号象征形式,但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个孔子形象,一是与六经不可分割,承接先王之道而又开立治出于二的新格局的孔子,一是作为儒家鼻祖的孔子。钟泰的孔子本为前者,而后者则为现代学术中主流的意识形态,在此观点架构下,庄子之学是不能得到恰当定位的。钟泰的说法,无异于强调,庄子之学与孟子一样,同为中华学术大中至正之路。研讨中华文明固然离不开孔子与六经两大符号,但庄子与孟子同样是重要的支脉,而不能以三教并峙之道家子学甚至等而下之的养生家、神仙家、方术等等视之。这也就是何以钟泰在解庄时,总是一再引用孟子解庄,因为庄子与孟子之会通处,在孔子之学,在《易》与《春秋》。对于钟泰这样的学者而言,一家一派之学无以定义孔子、孟子与庄子这些一流心智,相反,是一流哲人定义了学派,而不是某个学派定义了一流哲人。而从固化的学派性一般见解及其现成性架构中解放出来,是面向一流哲人的条件。那种将学派的教条化为某种框架,而后再去要求哲人的学术操作,很难企及一流哲人的思想高度。
二、钟泰庄学宗旨为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发微》明确指出:庄子之学,实为内圣外王之学。其所以著书,即为发明此内圣外王之道也。内圣外王之道,自梁启超以来,即被视为中国思想与文化之根本精神,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汤一介等等皆赞同这一主张。钟泰以为,《逍遥游》之辨小大,为内圣外王标其趣;《齐物论》之泯是非,为内圣外王会其通;《养生主》揭内圣外王之基;《人间世》为内圣外王之验;《德充符》,此学之成,充实而形著于外也。若是,斯内可以圣,而外可以王矣,故以《大宗师》阐内圣、以《应帝王》明外王,宗师即圣,帝为王之极至也。故而,内七篇只是一篇,内圣外王是庄子内篇之主线索,而外杂篇则从不同视角切入内圣外王。
连接内圣与外王的乃是“游”,“游”者则既可入于世,又可出于世,出入自在而无沾滞,即为游。出与入系于时。出则以身藏道,或以道存身,入则即游即应。庄子之“游”又是“乘道德而浮游”,钟泰以为浮即不沉溺,不沉溺即意味着超越。庄子对出和入皆不拘泥执着,而有“浮游万物之祖”的超越性意识。同样,在齐物论的理解上,反对和稀泥、无是非的简单化取向,而是主张:美者还其为美,恶者还其为恶;不以恶而掩美,亦不以美而讳恶,这才是美恶之齐;是者还其为是,非者还其为非;不以非而绌是,亦不以是而没非,这才是是非之齐。钟泰又以《至乐》“名止于实,义设于适”解《齐物论》,则以“止者不过当,适者不违其则”为齐物、齐论之要旨。这就将“乘道德而浮游”的道德之意呈现出来。游世而不避世,游有出入,出为游,入为应,即应即游,乘物游心而不避事。
庄子“游”的哲学具有积极的政治面向。这尤其表现在钟泰根据《大戴礼记·五帝德》以“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解释“黄帝三百年”,来解释《在宥》所谓的广成子千二百岁之说。这一解释引入了合往来古今而成一纯的历史视野。与此相应的是,《庄子》之进道德、退仁义、宾礼乐的秩序构建思路,在钟泰这里得以呈现。于是,我们看到的不再仅仅是那个被引向境界化生存风格的美学庄子,而是内圣外王的庄子形象。如果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那么《庄子》无疑以它自己的方式在呈现内圣外王之道的可能性。
钟泰的庄学研究与他本人的修身应世之路密不可分,从早年受益于王瀣,到后来与马一浮、熊十力等人的交友,他始终以自修其身的实践来展开其学术,又以其学术反哺其修身的工夫。其学问之所进即其工夫之所得。作为以传统学术应对世变的一代学者,晚年钟泰可谓游刃有余。于世变中见几而退藏,“闭门读书”“绝意于人事”“以自合盖”;《道德经》有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钟泰可谓真有所得者,终成全身全德的智者。就其一生而言,“幼受父兄之教,长好程朱之学,一生谨身饬行,不敢稍有偭越规矩之事,自以为虽算不了什么学者,总不失为一个束脩自好之士,依次做去当无大失”,如此律己,可谓甚严。在其交心书的微言中,仍然可以看出对道德文章的自信。
钟泰先生学术有着中国文化的全局视野,我本人在求学路上受惠颇多。随着这套《钟泰著作集》以及其即将出版的春秋学著作,我相信也期待着,钟泰先生学术思想仍被严重低估的状况,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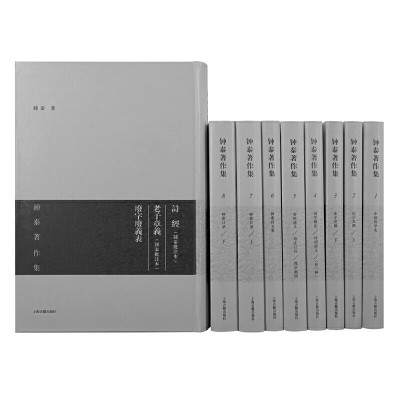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