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香室经说》(以下简称“经说”)十六卷,是俞樾晚年主讲杭州诂经精舍,二十年来“每有触发,随笔记录”而撰作的解经论著。虽然影响力比不上《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但也不乏创见。俞樾在晚年认为自己“著书不仅两《平议》”,且自注说:“两《平议》行世最早,然余所致力者,尤在两《杂纂》及《茶香室经说》等书。”(《春在堂诗编·八十自述》)可见,《经说》实属俞樾晚年的得意之作。
《经说》现存两个版本系统:一为《春在堂全书》本,包括光绪二十三年(1897)石印本与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二十五年(1899)、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及光绪间诸刻本,至光绪末年又有增订,越到后来内容越齐全。另一系统为单行本,现存三种,分别为光绪十四年(1888)初刻本、光绪十八年(1892)广东学院刻本与光绪十九年(1893)味腴书屋石印本。其中,《春在堂全书》本经过俞樾本人手定,“最能体现他本人的意愿”,是研究俞樾经学的首选。本次整理本即以凤凰出版社2010年影印南京博物院藏光绪末增订重刊《春在堂全书》本为底本,并参校《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二十五年《春在堂全书》本以及光绪十八年广东学院校刻本。精选底本,多方参校,遂成目前最为完善的《经说》整理本。
在校勘方面,整理者采取了尊重原作者的整理态度,尽量保留了底本原貌。比如书中常有异体字并存现象,如“无”与“無”,“法”与“灋”,“后”与“後”,“谥”与“諡”等。整理者并没有贸然进行统一,而是经过考察发现:书中所引《周易》之“无妄”,《周禮》之“灋”,《禮記》之“后”,《春秋繁露》之“諡”,都是俞樾引用经文时刻意保留的古字形。这种看似不统一,实则尊重了俞樾的原意,也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另外,书中引文与通行本文字有差异的地方,整理者也多出注而不轻易改字。如《郑风》“袒裼暴虎”之“袒”通行本作“襢”,《左传》杜注之“甑”通行本作“甄”,《周礼》正义“暜”通行本作“替”,《礼记》“甤”通行本作“绥”等,皆出注而不改字。仅在有足够把握确定是讹误字时,方才改字并出注,如《史记·鲁世家》“世”误作“史”,《礼记》“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中“上腾”之“上”误作“下”等等。凡此种种,可见整理者校字之谨严。
在标点方面,整理者也极谨慎,凡书中引文必核对原典,故而点断有当,信实可靠。如《经说》卷十五“辞于东门”条引用《左传·昭公十九年》杜注:“洧水出荧阳密县,东南至颍川长平入颍。”杜注“东南”二字,整理者将“东南”二字属下读,而今人多有将“东南”属上读。而查《中国历史地图集》,显见洧水由密县西北流向东南,到颖川一带与颖水交汇。再看《春秋左传正义·成公十七年》引《释例》云:“洧水出荧阳密县西北阳城山,东南至颍川长平县入颍。”可见《昭公十九年》杜注是节引,故“东南”二字当属下读,《经说》整理者无误。
整理本前附有《前言》,用了较大篇幅讨论此书的内容特色,有助于了解俞樾的治经特点。比如“述而有作”一节,整理者认为《经说》虽然在体例上模仿王引之《经义述闻》,但在提到《经义述闻》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进行辩正和补充。如卷一解“旧井无禽”,谓“近儒高邮王氏又破井为阱,并非经旨”,明斥《述闻》为非。解“驳马”,《述闻》读“驳”为“驳”,释为赤色马,《经说》则谓“驳”当作“”,释为牡马。虽未明言,实与《述闻》立异。其他如:“王氏《经义述闻》以‘期’为衍文,非是,故为辨正之。”“王氏引之谓‘至再拜’当作‘至壹拜’,究嫌‘至’字鹘突,似皆非也。”此类句子,书中很常见。可见,就《经说》来看,俞樾并非只是为了模仿,而是想要展现自己的见解。又如“举一反三”一节,整理者认为俞樾在解经时,有试图把一些训诂条例引为通例的倾向。如《经说》卷十一“纳甸”条谓“甸”字当读为“陈”,并引《周礼·稍人》注“甸,读‘维禹敶之’之敶”为例。事实上,俞樾认为“甸”与“陈”相通,早见于《群经平议》(卷七“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国作陈周”),又见于《诸子平议》(卷三十三“天甸其道”),又见于《达斋诗说》(“胡逝我陈”)。其他如“报”与“赴”通,“皇”与“往”通,“名”与“命”通,也常被用来举一反三,用来解说不同的经文。虽有时略显牵强,却能于其中看出其一贯的解经手法。当然,《前言》也指出了《经说》的其他特色,皆是整理者研究心得的总结,值得参看。
《经说》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值得当代经学研究关注。如《左传·定公十二年》传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史记集解》引服虔云:“人有入及公之台侧。”依服虔说法,“入及公侧”是说费人进攻到了国君身边。《经说》卷十五有“入及公侧”条,俞樾认为“入”字是“矢”字之误,这句是说费人在台下仰攻,射出的箭落到了国君身边。《经说》的这一观点,实历代注家所引征,影响很大。今可再补一证:新出睡虎地秦简“矢”字作“”,与包山楚简“内”字作“”同形。而“入”与“内”属于同源分化字,古文字中的“内”往往可读为“入”,且“内”字一形可“兼表入、内、纳三个词义”。颇怀疑《左传》中的“矢”先被误认为“内”,读为“入”,而后在传抄过程中径改成了“入”。如此,似可补俞樾“入”“矢”讹误一说。又如《尚书·金縢》记载武王克商之后病疾,二公告曰:“我其为王穆卜。”郑玄以为“穆卜”为“就文王庙卜”,伪孔《传》训“穆”为“敬”,孔颖达《正义》从之,后世亦多从其说。俞樾则发明“卜立后”之说,《经说》卷一“穆卜”条曰:“说此经者未解‘穆卜’二字,‘穆’乃昭穆之穆……二公欲为王穆卜者,盖以武王疾已不可为讳,欲卜立后也。”俞樾认为,“穆 卜”是指在二公以为武王的病已经好不了了,所以要卜下一代,周公阻止了他们,同时去祷告太王、王季、文王,请求自己替武王死,所以说“其勿穆卜”。如此一来,则文义畅然。唐兰也认为“穆 卜”就是要 卜武王的“穆”,学者冯时、朱凤瀚二位先生也同意此说。以上略举两例,可见《经说》至今有鲜活的生命力,值得学者研究重视。
《经说》初刻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近代以来声名远播,在今天却多为学者忽略,此书长期未经整理、翻检不利,恐是一大原因。此次整理本的问世,无疑大大提升了其普及性与易读性。《经说》本身自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俞樾的观点也经住了历史的考验,更展现出其历久弥新的价值,可谓“花落春仍在,《经说》久益香”。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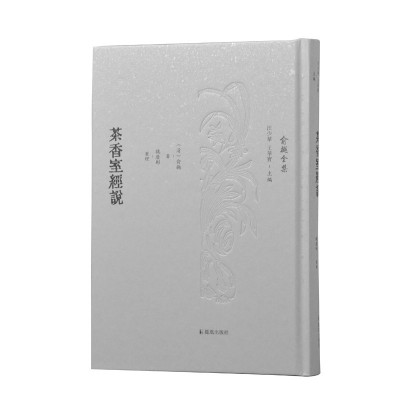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