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的小说常被认为很“通俗”,可能是因为他道出了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曾经历、思考过的那些问题:爱与激情、理想与现实、善与恶等。但仅以“通俗”显然也无法说明,如他的长篇《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人生的枷锁》等为何能赢得无论是研究界还是普通读者持久不衰的讨论。其实,相较于长篇,毛姆的短篇或许更精粹而隽永,是真正深谙如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且有种最好的随笔散文才具备的老道与世故。不过这种“世故”是不屑于圆滑而周到的,只是于世事人心见多识深罢了。
毛姆对人性的暗面有非同一般的洞察力。有些篇目使人读后脊背发凉,有种心理恐怖色彩。像《患难之交》里那位商人,外表“成熟稳重”“笑容和蔼可亲”。但当一位穷困潦倒的熟人找他荐工作时,他的安排和设计使人不寒而栗,可以说是不留任何痕迹地谋杀了对方。而这位商人面对“我”的追问直接坦率承认,态度从容和善,竟无一丝不安或罪恶感;这一类故事集中里不止一篇,像《赴宴之前》《信》,都是极好的心理恐怖小说。毛姆揭示出,当普通人内心的邪恶阴暗暴露出来,真仿佛平静水面下的一声炸雷。不过如果仅止于此,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我们的晚清黑幕小说写得比这还要彻底。毛姆的精彩还在于有时他仅仅是以人性恶为切入点,揭出“看客们”内心的种种因循、虚伪与丑陋。如《赴宴之前》里的斯金纳夫人、斯金纳先生、凯瑟琳,他们殷殷期待自己女儿、姐姐米莉森特能够主动分享丧夫的伤心事,以及她的亡夫“酗酒自杀”的“实情”,但当米莉森特真的如实道来,全家大惊失色,以至于做父亲的怪女儿不该如此“自私”。《信》也是如此,到故事终了,人们无法几乎是无法直视意味“教养良好”“举止高雅”的淑女内心那种“恶魔般的激情”。因此,说毛姆嗜写人性恶似乎有点儿简单化,他毋宁是在批评一种虚伪、老套的价值观念,在这样的前提下,毛姆细描人心中的“魔念”“罪孽”,几乎有种恶作剧的意味。
作者也喜欢拿着显微镜审视被人们称之为爱情的那种热情或激情。《插曲》认为天雷地火的爱情依赖于一种迟早会被消耗光的想象力;《雷德》几乎是“恶毒”地解构了那种童话般梦幻的爱情,认为这种爱情是多么脆弱地维系于“时间”本身。但要说毛姆“恶毒”吧,也不尽然,他当然喜欢嘲弄,他或也只是在自嘲,如果仔细辨析,能听到那些嘲讽的笑声背后的轻轻叹息。像在《雷德》中,曾如太阳神阿波罗般文雅娇柔的雷德已变成一个粗俗臃肿的男人,那曾如芙蓉般优美高雅而娇媚的萨丽,也已变成健壮黝黑的普通土著女人。当年老的萨丽与雷德再次重逢,她竟没有认出他,只是朝他“漠然地瞟了一眼”就走出了房间,这是多么惊人的一幕! 毛姆的笔法冷酷,但又充满悲悯。在《雷德》这样的小说里,依稀可以看到他在长篇《人生的枷锁》《面纱》一类小说中表达的主旨,即爱情的本质是非理性的,这或可以推及到人生所有方面的执着,在终点都是悲剧性的,只是人们甚少愿意直面这一点。
毛姆也怀疑任何的老生常谈。《生活的事实》告诉我们,长辈们的那类“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的经验之谈,不见得正确。面对命运的无穷尽的偶然,经验的锦囊并不总是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教堂堂守》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这位大字不识一个的教堂堂守,忠于职守了很多年,因被发现是文盲而失业了。之后,他略动了动脑筋就存下一大笔钱,成了一名殷实的商人,这篇讽刺的无疑是根植于知识的傲慢;《珍珠项链》是一则由对话构成的短篇,故事中的女家庭教师鲁宾逊小姐,阴差阳错得到一笔因错拿项链而带来的赔偿金,得意非凡,纵情挥霍之后走向了堕落。参考毛姆随笔中谈论莫泊桑的部分,这篇在构思方面大概受到了莫泊桑《项链》的启发,但此篇的主旨不在于表现人性,而是在探讨文学的本质。显然,毛姆并不认同莫泊桑的人性观,亦并不赞同他的文学观念。在毛姆看来,将人性区分为截然的善恶两端,将文学视为道德教化的工具,都是属于过于天真的想法。
对世事常常抱以冷眼和毒舌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刻薄”,不过我总觉得毛姆的“刻薄”底下还是有悲悯。《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所表现出的,主要都不是毛姆刻薄的那一面。尤其《刀锋》,故事架构很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主人公拉里固然并非梅什金一类的“圣愚”,但他面对苦难的同情与牺牲精神庶几近之。毛姆的短篇则仿佛是同一枚银币的另一面。《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和《吞食魔果的人》是集中使人印象深刻的两篇。爱德华·巴纳德跟《刀锋》中的拉里极为相似,他们都是那种执着于寻找生命意义之人。经历了父亲的破产,面对和恋人伊莎贝尔的婚约,爱德华决定接受一位世交的建议去塔希提岛工作。爱德华走后几年,望眼欲穿的伊莎贝尔发现爱德华来信越来越少。贝特曼·亨特,一直私心恋慕伊莎贝尔,是爱德华与伊莎贝尔共同的朋友,自愿替伊莎贝尔去塔希提岛探望爱德华。亨特见了爱德华之后发现他已成了和文明社会中的绅士截然不同的人——衣着“寒酸”然而态度“洒脱”,看起来乐在其中,并打算和一位土著姑娘结婚了。爱德华的选择是对于本阶层价值的叛离,是对于文明本身的弃绝;相比之下,《吞食魔果的人》中的主人公威尔逊的选择经过了更为审慎的筹划。作为银行经理的威尔逊至少为自己缴足了25年的年金保险,才下定决心在34岁时辞职。但对于这样一位有别于芸芸众生的“勇于掌握自己人生轨迹的人”,毛姆并没有笔下留情。故事最后,耗完了年金,威尔逊在一无所有的穷困中又活了6年,最后结局可想而知。这真是很有意思,以上这两个故事的传递出的观念似乎是相反的。但与其说毛姆是相对主义者,不如说他只是就事论事。因此,当毛姆在借着故事嘲讽这嘲讽那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前提,即他并不相信真空中的绝对,他更愿意将是非判断的起点还原到个体的独特处境上面去。
这集子里我最爱的一篇其实是《简》。女主人公简·福勒,一个年过半百的寡妇,在她崇尚浮华古典风格的嫂子看来,不过是个土里土气的过时人物。在叙事者“我”看来,简衣着独特,但笑容“颇为甜美”。简后来的两次婚姻都不乏戏剧性,但她显然太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第一次令众人大跌眼镜的婚姻之后,简仿佛被点铁成金了般,很快成为各种社交场合的焦点与明星,人人都觉得她很“幽默”,很有魅力。但实际上,她从头到尾都依然是同样一副“很简洁,很朴实,不造作”的样子,也从未费尽心思讨别人欢心。她率性而活,于人生紧要处当止则止,智慧而不自恋。当别人向她讨教“幽默”的技巧时,她只是淡淡地说:“我想准是我的衣服或者我的短发或者我的单片眼镜起了作用。后来,我发觉那是因为我说的是真话。说真话是如此非同寻常,以至于人们反倒觉得幽默了。”这不妨也看成是作家毛姆的夫子自道吧——拨开毛姆文风的毒辣、幽默、世故的表层,其扣人心弦、使人会心而笑的地方,也只是因为如此这般罢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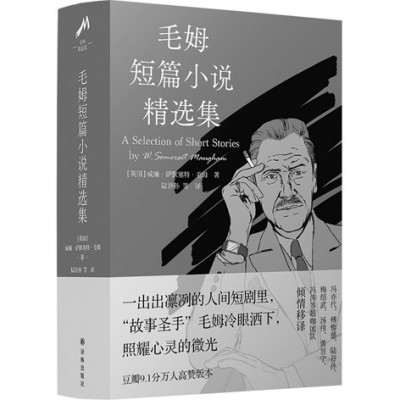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