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发现并表达了一个悖论
《逻辑哲学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悖论。维特根斯坦不仅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全书末尾明明白白地将它宣示出来。最初几位大名鼎鼎的读者对此都有深切的感受:弗雷格表示完全无法理解,罗素承认这种行文方式让他产生了理智上的不快,而拉姆齐则诙谐地将此书的内容称为“重要的空谈”。维特根斯坦本人后来也承认,他的这部早期著作包含严重的错误。不过,他并没有明确说,这些错误是不是包括他曾毫不讳言的那种悖谬性。
一代代的解读者们都试图弄明白: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又为什么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写它,而且还那么急切地把它公诸于世。他一定是想表达些什么,可是,在借助最新的逻辑学成就构建起一套精深而严密的哲学理论之后,他为什么又指出这种理论是没有意思的空谈呢?
他一方面自信满满地宣称,已从根本上解决了所有重大难题,而且已表达了确定无疑的真理,可另一方面又说,这些难题的解决带给我们的东西还少得可怜。这么说来,他似乎只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力有不逮,才只得把更艰深的难题留给后来人。要这样的话,反倒好办了:总可以期待更强大的思想者,有朝一日完成他的未竟事业。然而,让人挥之不去的,却是这样的感觉,即维特根斯坦以他的《逻辑哲学论》鲜明地展现出的这种悖谬性,恐怕永远也无法真正被克服:人类一切可能的言说方式,最终都难以说清道明宏大而抽象的论题,从而都只能留下毫无意思的空谈。
莫里斯承接并直面这一悖论
在众多解读《逻辑哲学论》的文献中,莫里斯的这本导读著作,恰恰从该书的悖谬性入手,并在这个框架之下展开细致的解读。他写道:“我认为《逻辑哲学论》包含着对如下这个结论的多个论证:任何说形而上东西的企图都必定会导致空谈。”
在创作该书时,维特根斯坦没有回避这一悖论,而在阐释的过程中,莫里斯也展现了直面它的勇气:“理解一个文本,就是将它表象为有意思的。一般情形下,将一文本表象为有意思的,就是将其表象为说了在该语境中合理地说出的东西。但如下这一点至少是这么做的最低条件:将该文本表象为字面上有意思的。这么一来,《逻辑哲学论》倒数第二节便给阐释者加上了难以承受的负担:为了将其表象为说了在该语境中为合理的东西,我们似乎不得不将其表象为什么也没说。”
莫里斯将维特根斯坦对一般哲学理论的态度,同休谟和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做了对比,并十分敏锐地指出:前者要比后二人更为真诚,也更加彻底。因为维特根斯坦不仅认为,此前所有表达抽象哲学理论的著作都只是空洞的玄想,应该像休谟所主张的那样,将它们统统付之一炬,而且认为,自己的《逻辑哲学论》也是这么一部著作,应做同样的处理。他自己的说法是,在完成了它的写作之后,要将它像一架借以登高的梯子那样一脚蹬开。
莫里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休谟和卡尔纳普只是想销毁其他哲学家的形而上学论著,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类理智研究》一书或“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也是毫无意思的空谈,从而也没有想到应该把它们一并抛弃掉。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做到了这两位哲学家没能做到的事情,或者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这便是维特根斯坦对全部哲学思考的一贯看法:抽象的形而上学思辨毫无例外地都只能带来没有内容的空谈。而这或许就是他不得不采用悖谬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他的作品的原因吧? 莫里斯总结道:“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有着与休谟和卡尔纳普大为不同的特点:他们热衷于抛开形而上学,与科学为伍;而维特根斯坦的态度似乎更富有诗意、更带着冥想的特征。”
在对《逻辑哲学论》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莫里斯时时记着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在做一件他充分意识到无法最终完成的事情,而这并未妨碍他极为真诚地探究一条既在细节上与众不同、又在总体上独出心裁的新路径。他这样来说明自己的解读思路:“维特根斯坦不断提出一些逻辑上相互依赖的、名言警句式的论断。论证的缺乏是导致该书难解的主因。所以,我尽可能清楚地表达谁都觉得可以在那里找到的论证。显然,这有损作品的诗意,偶尔还会略去生花妙笔。我尽量做到清楚明白、毫不含糊,甘愿以不够微妙为代价。我以为,这是服务于学生和学者的最佳途径。”
当“合理重构”遇上“诗意表达”
在对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的图像论的解读上,莫里斯极为重视对其中每一论断的确切意义的阐释,尤其注重准确再现文本中语焉不详的论证过程:“我一直试图如学生们需要的那样尽量清晰地展现论证的每个步骤,同时也指明同其他阐释的区别。”
为达此目的,他一方面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个关键论点所由得来的基础和前提进行清理和分析,另一方面又对这些论点之间的逻辑关联做细致的发掘、推敲和梳理。他善于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观点清晰地罗列出来,并以字母缩写作为每一论断的代号,方便自己行文时提及。这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繁琐,但对于准确重构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并系统表达作者的解读意见,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在该书导论里,莫里斯这样提醒我们:维特根斯坦所钟意的诗意表达方式,会妨碍我们对其思想的把握:“该书有些评论的抑扬顿挫的节奏,诱使我们以为知道他说的什么,而我们却真的不知道。”但阅读《逻辑哲学论》时,我们必须直面这一挑战。维特根斯坦既然将表达风格与思想内容密切结合起来了,我们便不应将二者割裂开来:“我认为,这部作品的悖谬性,乃是认为其诗意的写作方式很重要的理由之一。由于这部作品是悖谬的,所以,不能真正将它看作试图说出任何东西。而我们可用另一种方式让这里的诗性语言发挥作用,以实现不同于陈述真理的目的。”
怀疑论的威胁与人生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曾跟一位出版商明确说,他写这本书的根本目的是探究人生之意义。不过,他又坚定地认为,这种意义超越于现实人生之外,无法被言说。而这自然会引出这样的怀疑:既然人生的意义不可说,又如何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莫里斯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维特根斯坦似乎认为,哲学的难题关注于人生之意义所受到的威胁。他这里提供了一种保证:所谓的威胁不过是虚惊一场。一旦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得到解答了,就不会再留下什么未被触及的真正难题了。”
在具体解读《逻辑哲学论》的伦理思想时,莫里斯指出:维特根斯坦坚决反对将人视作“快乐机器”的功利主义,并认为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对人生的意义带来挑战,而只有超越现实功利,才有望体悟到生命的价值。维特根斯坦孑然一身,淡泊名利,完全投身于纯粹的哲学研究,但我们知道,他留下的是这样的遗言:“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这本书究竟表达了什么?
莫里斯总结说,《逻辑哲学论》尽管篇幅短小,却系统阐述了思想、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对唯我论、唯心论、实在论、怀疑论、伦理学等等难题提出了统一的解决之道:它们虽得不到确定的解答,却被表明终将完全消失。而维特根斯坦撰写这部著作,绝并不是在玩一场愚蠢的游戏。相反,他严肃地告诉我们,这是觅得这一解决之道的唯一可行的途径。
莫里斯认为,要从总体上把握《逻辑哲学论》这本书,需要变换思路。他将此前的两种解读《逻辑哲学论》的主要方式分别称作“不可说-真理论”和“并非-全-空谈论”。前者是比较传统的阐释意见,认为维特根斯坦设定了虽无法用语言表达却可以显示出来的形而上学真理,而后者则是所谓“新维特根斯坦派”的立场,他们认为《逻辑哲学论》中的那些指出其他命题全无意义的“框架命题”表达了真理。
莫里斯指出,这二者均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逻辑哲学论》的悖论。他自己则提出了“全无-真理论”这样一种更为极端的解读方式,认为维特根斯坦撰写《逻辑哲学论》并不是要表达任何牢不可破的真理,而只想把读者引向对世界存在及人生意义的神秘体验:尽管他在序言中声称把握了真理,而一旦在书末将他的所有命题(包括构成序言的那些命题)都判定为无意思的空谈之后,这些所谓的真理也便烟消云散了。
维特根斯坦以悖论的方式推出的这部著作,其实是想表明:尽管我们在不断追求真理,但看似近在眼前甚或尽在掌握的真理,终究不过虚幻一场。而当人们“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历百折而不回,誓与悖论共存亡之时,真理与意义便在其中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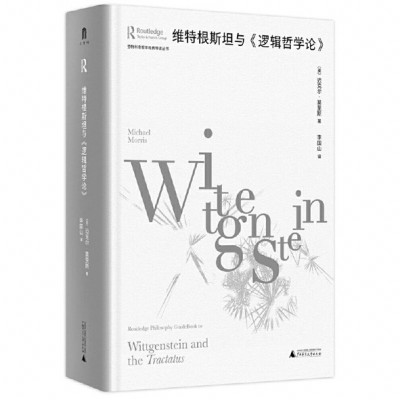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