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已经出了几本书,这次是她第一次邀我写序。为什么是第一次呢? 她说,过去出版社多次建议她找我写序,她始终没有向我张口。这次为什么开口了呢? 估计是因为她在我们的一次交谈中意外发现我重视人文学的普及工作。好像她过去一直怕我批评她的这项工作不够“纯学术”。当她发现我很强调人文学科的普及工作时,立即提出希望我为她的新书写个短序。
她想不到我会重视人文学的普及工作,大概是我的作品或为人给她的印象太认真、太严肃了? 似乎我只推崇纯学术的高头讲章?其实,我很佩服和欣赏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学界朋友,他们的学术成果能够引起大众的兴趣、理解和关注。这不仅是个人的成功,也是学术工作对社会的一种贡献,更是一个“学者”(即终生学习的人)对社会的可能的最大回报。我本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内不需要普及读物,但人文学内容很广,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比如西方语言学和欧洲历史,也需要一些普及性读物帮助自己快速完成基础性的扫盲工作。所以普及性的学术著作不仅是大众需要的,也是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有可能需要的。
我这里讲的主要是人文学的普及读物,其他领域的情况我知之甚少。所谓人文学,大约包括文学、史学、哲学、国学等。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普及工作似乎是一个专门的领域,早已得到社会重视,所以有全国性的“科普作家协会”。但是我们似乎不大可能有人文学的普及作家协会,人文学的普及工作好像还没有进入人文学者的视野。
为什么呢? 大概是因为人文学的很多内容本身就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很多小说、戏剧、诗歌都是寻常百姓可能欣赏的,不一定需要专门的普及读物。不过,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完全不需要普及作品,毕竟大众的理解各有偏好和局限,而专家的普及性或带有普及性的作品可以给一般读者的解读带来更可靠、更方便的引路灯,更能给业余爱好者和普罗大众提供指南,提供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上升的阶梯和视野,这大大有利于全社会人文水平和思维能力的提高,也会为和谐社会和人文自然的秩序提供养料。
我们不重视人文学的普及工作应该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可能是亚洲地区从美国引进的,但有些扩大化、教条化、简单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化了这种体系,但完全忽略了这种体系可能引起的弊端,忘记了、淡化了教育机构教书育人的基本目标和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相关部门往往通过行政命令或资源分配主宰高等教育的方向和评价体系,这大大限制了不同学校、不同教师的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独创性,尽管政府一再公开鼓励创新和创造。这种评价体系限制了学术普及工作的繁荣和发展,让大学脱离社会需要的内卷化竞争逐步强化,造成学术研究背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越来越远。在这个过程中,人文学的普及性或带有普及功能的作品被边缘化,很多作者也不得不改弦更张,钻进狭窄的“纯学术”的单行道,甚至走入无病呻吟的困境。
提到大学对教师的评价体系,我想到多年前杜维明先生跟我讲过,在哈佛大学,学院每三年对一个教授做一次评估,这个评估根据的是本人三年前自己制定的计划和方向,比如,以教学为主,还是以研究为主,重点是什么课题。评估时看你实现了多少,有哪些成绩和不足,同时听取你下一个三年的计划。三年后再做评估。这种对教授的评估体现了对每个教授的人格和专业的尊重和信任。我相信这是哈佛之所以是哈佛的一个重要原因。
哈佛如此,多数公立大学可能达不到这种水平,但普遍来说,政府很少给大学下达强制性指令,于是教授们也有较多的自尊和自主的空间。美国没有国立大学,公立大学都是州立大学,主要由州政府主办,但州政府也不会统一规定教授评价升职的规则或不同职称的比例额度,教授的评级主要在院系层面。就此来说,美国的大学教授享受的学术自主的空间比亚洲地区要大(当然,美国不同大学的情况不尽相同,而且也有一些变化)。当然,这不等于没有标准。学术标准必须有,但不能僵化。
由此想到,黄仁宇的博士论文《万历十五年》完成后,多所大学出版社认为不够学术,拒绝出版,而商业出版社又认为它属于学术著作而拒之门外。博士论文不能出版,就影响他寻找稳定教职,人生困顿多舛。虽然很多学术出版社标准有些僵化,但是,美国没有制定统一的出版标准,所以此书终于得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青睐,得以问世。我很理解为什么很多学术出版社不愿出版黄仁宇的博士论文,也很庆幸这样一部独特的书终究得到问世的机会。
《万历十五年》既不像纯学术著作,也不像普及读物,最终却成为雅俗共赏的畅销书,为学术界和社会大众提供了观察历史的不同视角。这样的书或许不符合通常的学术标准,但有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为什么要排斥呢? 说到此,我猜测此书能在耶鲁出版大概率与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有关,他习惯于以讲故事的笔调写历史,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很可能因为他能欣赏这样的书,耶鲁大学出版社才会出版这种书。总之,出版必须有标准,但标准不能僵化和教条化。
当然,我并不是说光华在模仿黄仁宇,也不是说光华的书已经多么完美。但是,我欣赏光华独特的笔触和探索精神,她将学术研究的成果与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借老子研究的机会,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与人生的一些洞察和动议。这种探索是少见的,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她为学术界或大众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笔调,为人文学的写作与传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至于高低得失,自有读者和市场的检验,不必由某些人一锤定音。
光华在尝试一种带有普及性的学术问题,她自有广泛的读者,我乐观其成,这是我愿意为她的书作序的主要原因。
衷心祝愿人文学的百花园有更多不同风格的鲜花竞相开放。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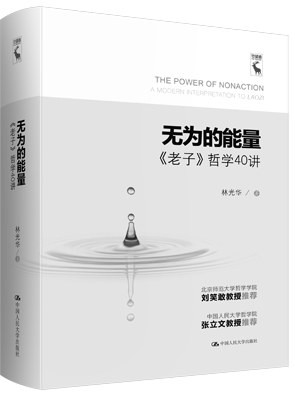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