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近日公示,《奥麦罗斯》(广西人民出版社“大雅”品牌出品)及译者杨铁军获得文学翻译奖。《奥麦罗斯》是诺奖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创作的一部史诗,共七卷八千余行,以三行体诗写成,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为原型,以渔民赫克托和阿喀琉争夺美丽的海伦为主要线索,通过众多来自现实、梦境、历史、经典的人物,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奥德修斯漫游记。因其宏大的篇幅和深远的艺术维度,《奥麦罗斯》构成了对翻译的巨大考验。译者杨铁军用多年时间数易其稿,修订打磨,他说,“对沃尔科特的译者来说,难处原来根本不在于对原文的理解,而是如何在汉语中找到一种适合他的风格”。
《奥麦罗斯》的翻译对我来说挑战性最大,下的功夫最多,收获也是最大的。当时我还在美国,每天晚出早归上班,懒散得很,什么也没做,心越空,反而越被空填满了。一早一晚,在森林里走几个小时的路,排遣排遣心情,排遣到排遣本身也需要排遣了。小龙(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在微信上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我的那个“懒我”下意识就推托了。此前也是应小龙之约,翻译希尼的晚期诗集《电灯光》,艰辛情境,历历在目。
过了一阵子,我的“勤我”鼓起勇气,质问“懒我”:“你不总是焦虑不安吗,你不经常说时不我待吗? 闲着也是闲着,这不是荒废时日吗?”“懒我”为了对得起“勤我”的良心,也为了能把自己给骗过去,只好万分不情愿地应允了。于是二我归一,事情就这样定了。虽然不管哪个我,对今后几年的大大超出预期的各种困难,并没有心理准备,也无从准备。
确实,《奥麦罗斯》作为一部规模庞大的史诗,真到了翻译的时候,便如汪洋大海,每在惊涛骇浪之中,难窥天日之时,“懒我”都会出来指责一下“勤我”。最大的问题是,在翻译过程中,我越来越对其在汉语中呈现出来的平淡、冗长深感不安,完全没有我想达到的汪洋恣肆的效果。记得翻译到一多半的时候,我已经有点丧失信心。每一行都是煎熬,每一页都加深了已经沉到最底的怀疑。但是,必须挺过这些怀疑,一步一步,蹚过晦暗不明的丛林,不可能指望奇迹。就这样,凭着残余的纪律性,慢慢地完成了初稿。沮丧之余,我在停顿了几个月后,开始修订。
在漫长的修改过程中,我反而体会到了最大的欢乐。《奥麦罗斯》采取了《神曲》的三行体,有一种一浪一浪、汹涌不绝的节奏,如何在汉语中呈现它,本来就是最大的挑战,也是此次翻译的核心所在。认识到困难所在,就等于抓住了解决的线索,我的沮丧原来都是错付。我把前面几章作为样本,反复琢磨,一遍一遍修改,大改不下六七次,小改起码有六七十次,在调整的过程中定调,在定调的过程中调整。修订伊始,我并没有什么期待,只有不能提供任何担保的过往经验可依靠,剩下的就是挣扎,似乎一切都是运气。当我终于找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自己内心其实是明白的,因为它充满了欣喜。
调子定了,就有了方向,但全诗八千多行,每一行都得按新语调重新衡量,于是就有了第一次全书规模的大改。经过这次大改,我把草稿搁置了几个月,完全不去想它。当我从头捡起,感觉还可以进一步精简,每一行都可以再减两到三个字,把意义压缩在更有张力的诗行中,效果只会更好,于是就有了全书规模的第二次大改,对每一行都做了如此的精简,梳理意义和结构,重新处理当时因“身在其中,不识真面”的含糊之处。
对短诗的修改可以是局部性的,但对长诗来说,一个句子的修改便可以影响全局。如果碰巧这个句子不在开头或结尾,那么不但后面的诗行得改,还得回过头,重新修订前面的。这个过程回环反复,似乎没有尽头,越改问题越多似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各个关键部分的句子在脑子里不断回响,失去了固有的顺序,逐渐地融为一炉,直至最后,尘埃落定。过了一个点,忽然一切都合理化了,哪怕偶尔的瑕疵似乎也不影响全局,可以放心地享受自己的收获了。回头看,这种笨功夫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的认知,我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对语言控制力的提高,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酬劳吗?
《奥麦罗斯》在国内有一种艰涩的名声,因为艰涩符合国内很多诗人对诗的期待,在了解甚少的时候,大家对《奥麦罗斯》似乎先有了美学风格的预设。其实翻译《奥麦罗斯》的困难,正如前文所述,并不在于文字艰涩,而是在于如何在汉语中为呈现它,找到一个系统的语言处理的办法,但这个办法是想不明白的,必须在不断探索中才有柳暗花明的可能。我”幸运”地找到了这个办法,一切都好像是命定的,但只有自己明白其中的曲折。在修订期间,我从美国回到中国,工作一下紧张起来,每天只有下班后的两三个小时可资利用,往往还筋疲力尽,做不了太多。但好在剩下的修订,大多按部就班便可以完成的,碎片化的时间也无妨思路。
《奥麦罗斯》的风格绝不能说是平易的。全书自始至终华丽非凡,意象的爆发让人目不暇接。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其华丽表层之下,运行的古希腊式理性。不管现象多么纷繁,都历历分明,清晰可辨。沃尔科特把握住了自己作为黑人和白人混血的独特身份,用同等重要的地位将两者映射于作品中,通过一个似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加勒比海与西方经典的平行互通结构,让诗意在错位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张力。沃尔科特因此冲出了由T. S.艾略特开启的现代长诗的定式,开辟了一个浩渺的诗学空间。这样的写作在后艾略特时代,既让人意想不到,又全在情理之中。沃尔科特拒绝循规蹈矩,拒绝在现代派的夹缝里匍匐,这个做法本身就很有意义,更不用提他的光芒四射的文本本身。
这一点对中国当代诗学是有启发意义的。艾略特的长诗,在当时是一种文体的解放,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断绝了长诗的可能性,自此之后,所有的长诗都不约而同地向《荒原》看齐,在文体上更激进一步,作为确立自身诗学的法门。包括很多中国当代诗人的长诗,都是如此。这些努力基本上都可以算失败的、无效的,尽管它们的企图,无一例外,都是纳入最当代的生命经验。这种企图最后往往沦为滑稽可笑的东西,与其庄重严肃的目的形成极大的反差。固守先锋的姿态,反而成了保守的反动。沃尔科特也许是不能效法的,但沃尔科特在长诗的“荒原”中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在此前及此后所有的失败之作中显得异常醒目,即使不能归之于完全的成功,相对来说最站得住脚,却是不可置疑的事实。希望沃尔科特的实践,能起到帮助中国当代诗人开拓思路的作用。
“大雅”书系能出版这样一批对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人文观念有借鉴意义的作品,功莫大焉。从选题到最后出版,在现今的环境下,都需要绝大的勇气和见识。我作为译者,也在翻译过程中也得到了认识上的反思,以及诗学感受力的成长。当时的惘然,都成了可待的追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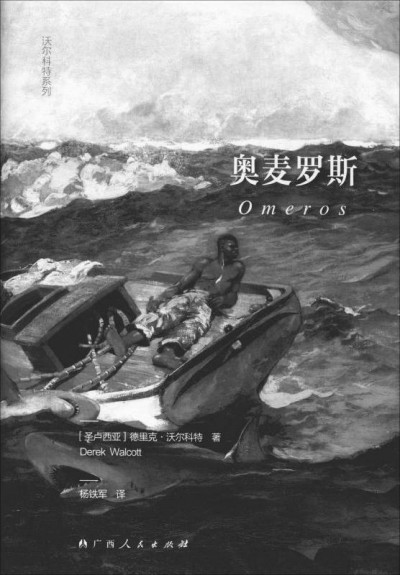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