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劈成两半”的“诗仙”
仕途之外,也还有隐逸一途。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取向,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体悟人生的真谛,获致精神的慰藉,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不介入;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冷漠成为一种性格存在状态。还有些人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磨损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实现对传统的人格范式的超越。这就是所谓“隐心”。隐心的痛苦程度,往往超过衣食无着、饥寒交迫的物质匮乏,需要战胜富贵的诱惑,勇于面对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炫耀,需要以顽强的意志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
在封建时代,即使是归隐山林,也未必就能脱离政治风险。出于内外种种原因,历代取径“出世”的人为数并不很多;绝大部分读书士子,终其一生,还是和政治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他们总是积极投身社会政治实践,奔走仕途,即便是那些大思想家、大文豪、旷世诗哲也不例外。我在《两个李白》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就是说,颇富典型性。
“诗仙”李白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居高位、掌权衡,以实现一己的宏伟抱负。他高自期许,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这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他耽于幻想、天真幼稚,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而脱离实际。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一生中,他有两次从政经历,都以惨败告终:前一次,被以“文学弄臣”蓄之,即使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只好“上疏请归”,一走了事。后一次,竟然招致一场灭顶之灾,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气壮山河、睥睨百代、雄视万夫的伟大诗人。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那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不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李白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置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缘木求鱼!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这种灵魂的煎熬,伴之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脱离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高远的视点、广阔的襟怀、超拔的境界、空前的张力。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漩涡里。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巨大的遗憾、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与“被劈成两半”的“诗仙”李白相对映,状元杨慎则是一生中“冰火两重天”。我曾以《风波中的彻悟》为题,剖析了这一场更为典型的人生惨剧。
杨慎字升庵,出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杨廷和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一朝宰辅,元老重臣,而祖父、叔叔、弟弟、儿子,也都是进士及第,有“一门科第甲全川”之誉。他在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可说是飞黄腾达、春风得意。
当时的皇帝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无兄弟,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自己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问题。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统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统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可是,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为了提高本家宗族的地位,决意打破这个成规,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奉以皇帝尊号。从宗族承嗣上看,这就意味着脱离了孝宗、武宗支派,从而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大礼议”的激烈论争。当时内阁大臣中分为两派,新科进士张璁等主张遵从上意,称孝宗为皇伯;而内阁派杨廷和、杨慎父子和众大臣都坚决反对。嘉靖皇帝断然固执己见,杨廷和以辞官归里相要挟,皇帝并不予以挽留。
于是,皇帝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升庵便纠集一些人上疏切谏;没有得到答复,他又和廷臣们跪伏左顺门外请愿。皇帝更加震怒,下令将带头抗命的八个人逮捕下狱。这就更加激起了群臣的愤慨,杨升庵年轻气盛,激动万分,高喊:“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当日有二百多名廷臣在金水桥畔、左顺门前跪伏痛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震云天,响彻宫廷。皇帝下令逮捕哭声最大、闹事最凶的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全部廷杖。杨升庵被杖击后,奄奄一息;十日后,再次廷杖,几乎死;最后,谪戍云南永昌,永远充军。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关于这场轰天动地的宫廷大案的是非曲直,后世意见不尽一致。《明史》对嘉靖帝是持批评态度的,说他将生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实在过分,这无异于肯定杨升庵等人行为的正义性。学者王文才认为,“在这次激辩中,杨慎奋抗暴君,痛击邪曲,表现其‘见义不敢后身’的政治品质”(见《杨慎诗选·序》)。而当代学者柏杨则对杨升庵予以激烈抨击,鉴于他所坚持的是宋代程朱理学,斥之为“卫道之士”的“奴性狂热”“恬不知耻”“颠倒是非”(见《中国人史纲》)。其实,这两方面的是是非非,恐怕未必存在太大的实际意义。如果说,在皇帝那边还有个切身利益与宗族地位的考量;那么,对于杨升庵来说,无非是头脑里的“礼制”作怪,那么拼命奋争,直至付出几十年的惨痛代价去较这个死劲,既不能说“奴性狂热”“恬不知耻”,大概也算不上什么“义所当为”。
当然,这是后世的评说,作为当事人,杨升庵的彻悟绝对需要时间,需要实践,其间不仅有出生入死的生命体验,还离不开数十载穷边绝塞、谪戍岁月的苦难生涯。
嘉靖皇帝登极后,二十余年置朝政于不顾,整天躲进西苑,炼丹修道;可是,却时刻记着杨氏父子的“仇口”。他曾咬牙切齿地说,他在位一天,就不让杨升庵有出头之日,真是结下了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而偏偏他在位时间又特别长,足足四十五年,致使杨升庵不要说回朝任职,即便普通的罪犯年老多病之后返回故里的“优渥”,他也享受不到。年满七十后,他从云南偷偷溜回四川故里,巡抚察知,立刻勒令“逮还”。
生活是一部教科书。当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荣华富贵,转瞬间化为乌有,由宰辅的峰巅跌入囚徒的谷底。这惨痛的遭遇,大起大落的浮沉跌宕,在给予他以沉重打击、身心折磨的同时,却使他在精神层面上获得解悟、实现升华。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解了“达生之道”,认识到瞬息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原需奉行“齐物哲学”,等同地看待荣辱、穷通,是非、得失;只要自己能够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调整视角,则对人间万事尽可弛张莫拘、淡然处之。
杨慎在晚年创作的《二十二史弹词》中,抒发了这番感悟。其中有一段开场词,调寄《临江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不要说后世的论者,即使他自己,数十年后,作为一个远戍蛮荒的平头百姓,徜徉于山坳水曲之间,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料也能够感到,当年拼死相争的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皇上称父亲为皇考还是为皇叔的所谓“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真个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实际上,这种彻悟与觉醒,不只是反映在这首《临江仙》词里。综观其后期的大部诗作,特别是《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可以说,里面贯穿了这种淡泊功名、脱略世事的蕴含。且看《说三代》里的《南乡子》: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谁弱谁强都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看得出来,这些词作既是他多年谪戍生涯、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刻画出他以秋月春风、青山碧水为伴,寄情渔樵江渚的闲情逸趣,也是诗人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超然物外,摒弃种种世俗烦恼,对个人的一切遭际表现出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帮助他度过了漫长、孤苦的凄清岁月,最后得以七十二岁的上寿,终其天年。
(本文摘自《王充闾回想录》,王充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第一版,定价:79.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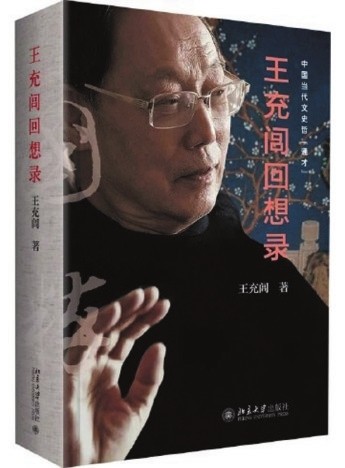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