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汉语与汉字的密切关系决定,很多形声字的声符具有揭示词源的功能。利用形声字声符的示源功能,类聚同声符形声字,归纳这批形声字相通的词源意义或探求声符与形声字之间的孳乳关系,则产生了在训诂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右文说”。“右文说”立足于文字现象,解决的却是语言问题。无疑,这一学说存在混淆字、词的问题,但前人在训诂实践中却能利用汉字的“右文”现象解决很多语言的实际问题,这说明“右文”表面上是文字现象,实质上却是语言现象。那么,隐藏在“右文”深处的语言原理是什么? 如何将“右文说”的文字表象与语言实质结合起来? 如何克服“右文说”的字形束缚? 这些问题,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近来,笔者研读陈晓强《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下文简称“陈著”),对“右文说”的局限与出路有了新的思考,故就此谈一点拙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的很多特性由其所记录的语言决定。要深入认识“右文”原理,首先需要对上古汉语的性质有深刻理解。上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词的语音区别手段有限,由此决定汉字很难依靠语音信息来实现区别,只能走依据语义信息来构形的表意文字道路。另一方面,语言需要表达的意义信息非常庞杂,而文字的数量却不允许无限增加。与之相应,据义构形的表意文字在发展中必然会出现意义内涵越来越宽泛的现象。而且,文字所记录的语言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这也会让文字的意义内涵越来越丰富。文字意义的宽泛、丰富,影响文字职能的清晰表达。为了实现文字表词职能的清晰,在汉字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就需要在旧字基础上分化新字,从而形成汉语词汇派生和汉字字形孳乳相伴而行的现象。形声字占汉字的绝大多数,正是汉语词汇派生长期推动汉字形声造字的结果。为什么汉语词汇派生会推动汉字走向以形声分化为主的造字法? 陈著177-178页指出:“与以单音节词为主的上古汉语相适应,以声符为基础添加义符的形声分化造字法,是最经济且能有效记录汉语新词的造字法。”“受符号经济原则和交际理解需要的制约,新词多在旧词的基础上分化而出;同样的道理,记录新词的新字,也大多选择在旧字的基础上造字。由此,便形成词的分化与字的衍生相伴而行的现象。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而形声造字法的原理即在于通过声符保持新词、新字与旧词、旧字的联系,通过义符实现新词、新字与旧词、旧字的区别。因此,汉语词汇派生与汉字形声孳乳关系密切,从而形成汉语同源词中最重要的类别:同声符同源词。”这些论述,从理论上揭示了“右文”现象的语言原理,进而明晰了“右文说”以形声字声符为线索探求汉语词源的合理性。
“右文说”有其合理性,但“右文说”以汉字为线索研究汉语词源的方法存在以字代词的缺陷,进而带来研究的很多混乱。近现代以来,受西方语言学字词观的影响,一些学者对“右文说”提出批评。这些批评,启发我们深思“右文说”的诸多问题:如,由于对“右文”现象缺乏全面考察,传统小学对“右文说”的讨论及应用多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例如,段玉裁注《说文解字》“陘”(为了便于显现形声字声符之间的形体关系,本文所讨论的声符及形声字全部采用繁体):“凡巠声之字皆训直而长者。”“巠”声之字,的确有很多具有直而长的意象,例如“經、莖、脛、牼、徑、頸”。直的意象与坚硬、刚劲意象相通,“巠”声字又有坚硬、刚劲义,例如“勁”为强劲有力,“痙”身体僵直而难曲伸,“硜”为刚劲有力的击石声,“桱”为质地坚硬的桱木。可见,“凡从某声皆有某义”经不起汉语、汉字事实的检验。再有,由于对“右文”现象的语言原理缺乏深入讨论,“右文说”拘泥于同声符形声字,以字代词的问题十分严重。很多情况下,声符与形声字之间的孳乳关系,表象反映旧词向新词的分化,实质却为词源意义的运动变化。陈著提出的“语根的引申”即是就这种现象而言。学界对引申的讨论,多关注词语的引申分化,而很少讨论语根的引申运动。词语的引申形成新词与旧词的点对点的照应,而语根的引申呈现为新词与旧词的多对多的照应。例如,陈著在“高”族的高义下系联“高、喬、僑、嶠、鐈、橋、趫、簥、毊、垚、堯、嶢”等词,在高大、矫健义下系联“豪、鰝、驕、獢、驍、獟、鵠、蛟、鮫、駮、狡、鵁”等词。高义和高大义之间的义通关系十分明显,以上诸词之间的关系,只能从语根引申角度而无法从词语引申角度解释。陈著105页:“马之高大、矫健为‘驍、驕’,犬之高大、矫健为‘獟、獢’,豕之高大、矫健为‘豪’,魚之高大、矫健为‘鰝’。”如果简单地从形声字声符角度考察以上诸词的引申关系,则“堯”引申为“驍”“獟”,“喬”引申为“驕、獢”,“高”引申为“豪、鰝”。这种机械地割裂“驍”与“驕”、“獟”与“獢”的研究法,显然是有问题的。由此即可看出“右文说”拘泥于形声字声符线索,以字代词的研究局限。
形声字声符是探求汉语词源的重要线索,但文字毕竟不同于语言,不是所有的形声字声符都具有示源功能;具有示源功能的声符,其词源意义也往往是多向、多层的。清人“右文说”的一大问题在于以偏概全,忽视了形声字声符示源情况的复杂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对形声字声符进行深入、全面地考察。就此,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右文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以字代词,拘泥于同声符形声字。就此,陈著67页指出:“(‘右文说’)对形声字声符线索的利用主要着眼于单个声符字形,而忽视了声符与声符之间的相互照应。形声字声符在相互照应中构成声符互通系统,以系统为背景,能使汉语同源词的系联有更多的形体参照点,而且,在系统的制约下、在系统要素的相互提示下,对同源词的系联和解释会更加客观准确。利用声符线索而不拘于声符线索,才能使‘右文说’的利用上升到语言学层面。”
上古汉语单音节词汇的派生推动着汉字的形声孳乳,由此导致形声字占汉字的绝大多数。利用形声字声符线索以系联汉语同源词、研究汉语词源的方法无疑是合理的。然而,字、词毕竟有别,利用形声字声符线索的“右文说”在发展中却深受声符线索的束缚。让“右文说”在利用声符线索的基础上又能摆脱声符线索的束缚,无疑是“右文说”在今后健康发展的出路。这是一个研究难度很大的宏大选题,非一人之力能够解决。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陈著97页提出应重视对“声符互通”现象的研究:“以‘右文说’为基点,摆脱声符形体的束缚,我们会发现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声符所参构的形声字,不仅在一个声符下可以互通,而且声符与声符之间还有另一个层次的相通关系。这种‘声符互通’现象的发掘,既发挥了‘右文说’的合理价值,又能克服‘右文说’单一形体的局限。”陈著对形声字声符互通现象有清晰而深入地讨论,并总结出利用形声字声符线索研究汉语词汇的“声符比较互证法”。理论上能对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方法上有清晰的操作流程。理论与方法互为支撑,陈著既重视形声字声符线索,又能在形声字声符的相互关联中摆脱具体形声字声符的束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利用声符线索而不拘于声符线索。这是对“右文说”的推进,从陈著所取得的成绩看,陈著推进“右文说”的思路、方法是合理且有效的。当然,“右文说”关涉到很多问题,陈著只是解决了其中一小部分,希望有更多学者关注并推进“右文说”的发展。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右文说”的发展有助于加深对汉语与汉字特殊关系的认识,进而有助于字词结合的汉语语言学的建设。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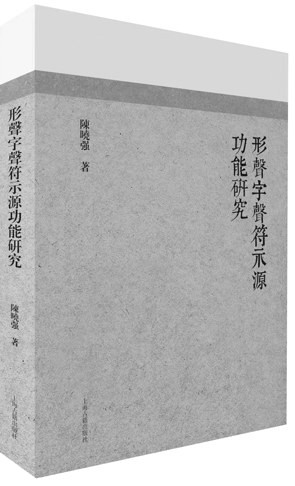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