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洁拙朴的封面、古朴简约的装帧,传统味道、传统气派、传统风格,文献、文物、图像相结合,图文并茂,信而有征,王学雷先生的新著《古笔》“真好”。
王学雷先生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善于提出经过独立思考的见解。为了呈现“早期毛笔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作者在上卷《汉唐古笔考》娴熟地从文献与文物两条途径,考察汉唐时期毛笔的演变,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颇见功力的梳理、校勘、考订,对这一时期毛笔的形制、产地、工艺、性能、功能与文化等的探讨不时有精彩呈现,对彤管、笔答、茹笔、削管等名物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介绍、论述时条分缕析,如对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从整体到笔的各部分都作了专题性的绍介。
在中卷《古笔图说》部分,作者在近200幅珍贵图片的下面都标示准确数据,进行客观描述。读者根据这些从战国到唐代的古笔图像资料(包括传世的和出土的),可以“直观地看到古笔的演变规律及制作细节”,丰富对古笔的认识。
下卷《汉唐古笔文献辑释》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校勘和注释,对文献解读的岐异之处提出自家观点,通过校释古文献使读者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古笔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大部分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而成为一个整体:毛笔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符号。在毛笔日渐淡出许多人视野的时候,王学雷带着我们品鉴不同时空中的毛笔这一重要遗产。
《古笔》没有止步于对相关史料的梳理、考证与解读,还探讨了早期书法、绘画发展及文化传播背后工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毛笔的制作、传播、使用等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内容。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历史事实隐藏着陷阱,有些虚构里包裹着真实。这就要求人们小心求证,去发现被累积的假象所掩盖的事实。王学雷在爬梳辑佚资料的过程中,哪怕只 言片字,他都会顺藤摸瓜,去发掘与勾连相关文物史料,以发现真相。比如他从尘封的文献中发现事实,还原“汉居延笔”是由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这一真相。作者还对傅振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删削马衡原文”的难言之隐给予“了解之同情”。
毛笔是几千年中华文明持续传承的参与者、呈现者和塑造者,可以说,一笔一世界。王学雷写道:“在东亚地区悠久的书写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技术制作体系”,而“毛笔的粗细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书法创作形式和风格的变化,促进了书法艺术性的发展”,不仅如此,“中国水墨画以笔法为技法要素,都与以毛笔为中国书画的工具有密切的关系”。王学雷引领我们品味毛笔的内在诗意,呈现蕴含其中的文化内涵。
王学雷“有感于古今论笔者多着眼于笔与书法艺术之关系,而笔之用于抄写之本质越来越受忽视”这一难以阻挡的趋势,将毛笔分为“写书笔”和“书法笔”,认为“写书笔”在传承中华文明方面厥功至伟,而书法笔创造 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书画艺术。王学雷先生还提出“写书者与书法家之不同,由各自所用之笔即可体现;中国文字之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区别,亦因笔之形制不同而得到体现”,显示了他对古笔以及笔文化的深刻理解
我觉得,可以沿着《古笔》和前人的踪影足迹继续前行,逐渐向历史、哲学、文学、书法、美学、绘画、壁画、雕刻、宗教、政治等领域拓展,譬如说,有些“书法笔”既是笔,又不止于笔,有遗貌取神、意在笔外的一面,我们就要用心感受附着其上的生命能量和境界。
王学雷治学态度严谨,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内容的安排。《古笔》没有对毛笔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而把重点放在汉唐。作者谦虚地说“学力和精力所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其他时期出土的毛笔实物相对较少。二、大量征引文献。三、结论建立在可信证据和严密逻辑的基础之上。他非常强调目录、版本、校雠的重要性,这是逻辑严密的一种体现。王学雷引用了蒙恬之前的文字记载,以出土文物为佐证,揭示了流传甚广的蒙恬造笔只是一个传说。类似的例子不少。
《古笔》新意频出,其因有二。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学雷先生不只是于故纸堆里爬梳、钩沉、辨析、剔抉、阐释史料,还非常注重吸纳有关毛笔的最新考古成果。书中新意大都来自这方面。其二是能够“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贺昌群语)。当然,这需要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古笔研究中的文献引用问题》一文所谈两本书所存在的引用问题就属于这方面的内容。
笔既是书写的工具,更是流淌的文化,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书写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辉煌。 王学雷说自己有“恋旧情结”,在这个人们与毛笔渐行渐远的时代,他“总希望尽力地将行将‘消逝’的毛笔文化,像捡拾散落的珠子那样,尽可能地多捡回来些”,而“有助于‘捡拾’或‘挽留’的最好方法,应该是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可以说,毛笔文化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值得也需要传承、弘扬。希望《古笔》成为人们研究、弘扬毛笔文化的又一新起点。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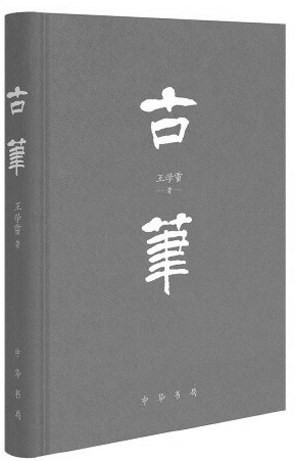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