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曾经多次远程巡行,数次有行历北边的经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又一次巡行北边。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巡。《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后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二月,诏曰:‘朕郊见上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罔,靡所获献。荐于泰畤,光景并见。其赦天下。’”《太平御览》卷五三七引《汉书》:“《武纪》曰:‘朕郊见上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不以罗网,靡所获。献荐于太畤,光景并见。’”《太平御览》卷六五二引《汉书》:“后元年二月诏曰:‘朕郊见上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网,靡所获。献荐于㤗畤,光景并见。其赦天下。”有“不以罗网”“以不罗网”的不同。
关于“非用罗罔时”
既说“行幸甘泉”,又说“巡于北边”,很有可能是循行联系“甘泉”和“北边”的直道来到“北边”长城防线。他在“北边”地方看到栖息的“群鹤”,因为时在春季,当时社会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礼俗,严禁猎杀野生禽鸟,于是没有捕获这些野鹤用于祭祀上帝时奉献。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时春也,非用罗罔时,故无所获也。”《太平御览》卷五三七引《汉书·武纪》注引如淳曰:“是时春也,非用罗网时。故无所获。”“是时春也”应是正文。
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言辞。其中说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的说法,当然是儒学的文化宣传。论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四时节”,“风雨时”。然而这其实又是值得重视的体现当时进步的生态环境观的表述。应当说在生态环境保护史上,发表了一种比较开明的见解。
《礼记·月令》中多规范了天子和官府在不同季节的作为,因而具有制度史料的意义,与主要反映民间礼俗的《月令》明显不同。其中写道:孟春之月,“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季春之月,“田猎罝罘、罗罔、毕翳、喂兽之药,毋出九门。”睡虎地秦简整理者定名为《秦律十八种》的内容中,有《田律》,其中可见关于山林保护的条文:“春二月,……不夏月,毋敢……麛 (卵)鷇,毋□□□□□□(四)毋敢……毒鱼鳖,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五)”整理小组译文:“春天二月,……不到夏季,不准……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9月版,释文第20页至第21页)以《月令》作为政策指导,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确。《汉书》卷八《宣帝纪》记录元康三年(前63)六月诏:“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春夏两季不得破坏鸟巢,探取鸟卵,射击飞鸟,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如《吕氏春秋·孟春纪》:“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礼记·月令》:“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成书于西汉中晚期的《焦氏易林》有相关内容,如《讼·暌》:“秋冬探巢,不得鹊雏。御指北去,惭我少姬。”《师·革》:“秋冬探巢,不得鹊雏。衘指北去,惭我少夫。”又《观·屯》及《革·复》:“秋冬探巢,不得鹊雏。衔指北去,媿我少姬。”都说“秋冬探巢”,似乎也可以说明“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的制度确实在民间形成了礼俗规范。
关于“时春”“非用罗罔时”的制度礼俗,汉代直接的文物证据,见于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如涉及禁止杀害野生禽鸟的规定:
孟春月令:
·毋杀幼虫·谓幼少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
· 毋杀孡·谓禽兽六畜怀任(妊)有孡(胎)者也尽十二月常禁
· 毋矢蜚鸟·谓矢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
· 毋麑·谓四足之及畜幼小未安者也尽九月
·毋卵·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中春月令:
·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也虫草木□□四月尽孟夏月令:
·毋大田猎·尽八月□
这篇文书开篇称“大皇大后诏曰”,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5期;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置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92页至第199页),时在公元5年,是明确作为最高执政者的最高指令——诏书颁布的。书写在墙壁上,是为了扩大宣传,使有关内容能够众所周知。
鹤与汉代社会生活
汉代社会生活中可以看到鹤与人类相亲近的诸多表现。汉代画象中可以看到纵养禽鸟的画面。成都双羊山出土的一件,画象中心似乎就是鹤。以“友鹤”或者“鹤友”为别号或者命名书斋和著作者,多见于文化史的记录。这一情感倾向,在汉代已经有所表现。“友鹤”行为和意致,体现出古代文人清高的品性和雅逸的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又可以间接体现人对于自然的情感,人对于生态环境的理念。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以所谓“煮鹤烧琴”表现的对反文明、反文化行为的批评。如韦鹏翼《戏题盱眙壁》诗:“岂肯闲寻竹径行,却嫌丝管好蛙声。自从煮鹤烧琴后,背却青山卧月明。”(《全唐诗》卷七七○)唐代诗人李商隐据说在被称作“盖以文滑稽者”(〔宋〕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引《西清诗话》)的游戏文字《杂纂》中,曾经说到诸种“杀风景”的行为,其中就包括“烧琴煮鹤”。〔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李商隠《杂纂》一卷,盖唐人酒令所用,其书有数十条,各数事。其‘杀风景’一条有十三事。如‘背山起楼’、‘烹琴煮鹤’皆在焉。”“烧琴煮鹤”作“烹琴煮鹤”。“煮鹤”,不仅见于意在嘲讽的幽默文字,也反映了古代食物史的实践。
传说伊尹曾经向商汤进“鹤羹”而得以拔识,《天中记》卷五八。而《北堂书钞》卷一六引《穆天子传》有“饮白鹤之血”的故事。汉代出土文物资料,可以说明这一情形当时比较普遍。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系在330号竹笥上的木牌,写有“熬笥”字样。“”即“鶮”,就是“鹤”。《集韵·铎韵》:“鹤,鸟名,或作‘鶮’。”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同类木牌也有书写“熬 笥”者。发掘报告写道:“出土时脱落,与实物对照,应属东109笥。”而《遣策》中“熬 一笥”(136)当即指此。报告执笔者又指出,“”就是“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卒屯留,蒲 反。”司马贞《索隐》:“‘’,古‘鸖’字。”(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92页)“鸖”是“鹤”的俗字(《干禄字书·入声》,《龙龛手鉴·鸟部》)。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系在283号竹笥上的木牌,题写“熬 笥”(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10月版,上册第115页)。与283号竹笥木牌及330号竹笥木牌对应的内容,《遣策》作“熬 一笥”(71)及“熬 一笥”(72)。“”即“鹄”,也是“鹤”的异写。《集韵·铎韵》:“鹤,鸟名。《说文》:‘鸣九皋,声闻于天。’或作‘鹄’。”《庄子·天运》:“鹄不日浴而白。”陆德明《释文》:“‘鹄’,本又作‘鹤’,同。”李商隐《圣女祠》:“寡鹄迷苍壑,羁凤怨翠梧。”朱鹤龄注:“‘鹄’,《英华》作‘鹤’。‘鹤’‘鹄’古通。”
马王堆一号汉墓283号竹笥及330号竹笥发现的动物骨骼鉴定报告,确定其动物个体是鹤(GrusSP.)。可知“出土骨骼内,共有鹤2只”。鉴定者指出,“出土骨骼的主要特征均与鹤科鸟类一致。”“鼻骨前背突起与前颌骨额突清晰分开,与灰鹤近似,与白枕鹤不同”,“但出土头骨的颧突特别短而钝,与灰鹤和白枕鹤均不相同。究属何种,尚难确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脊椎动物分类区系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动物骨骼鉴定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67页至第68页)然而,马王堆汉墓的发现,确实可以作为“煮鹤”“烹鹤”的实证。由此可以推知古代有关“鹤羮”的传说,也并非没有根据的虚言。《楚辞·天问》:“缘鹄饰玉,后帝是飨。”汉代学者王逸的解释是:“后帝,谓殷汤也。言伊尹始仕,因缘烹鹄鸟之羮,修饰玉鼎以事于汤。汤贤之,遂以为相也。”其中“缘鹄”,或作“缘鹤”。一代名相伊尹,竟然是因向殷汤奉上“鹤羹”而得到信用的。
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资料有关以鹤加工食品的信息,可以推知汉武帝如果以鹤“荐于泰畤”,将会以怎样的形式奉上。
“光景并见”:“灵命”的暗示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记载:“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粱禾于殿中,各顺色置其方面,先鬻鹤龀、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颜师古注以为“鹤龀”就是“鹤髓”:“龀,古髓字也。谓煮取汁以渍谷子也。”《太平御览》卷九一六引《汉书》说到王莽使用鹤的骨髓的故事。四库全书本写作:“王莽以鹤髄渍谷种学仙。”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则作:“王莽常以鹤髓渎谷种学仙。”所谓“神仙事”、“方士言”,其志在“学仙”的神秘的营作,竟然以“鹤髓”作配料。这一情形,当与长期以来所谓“鹤一起千里,古谓之仙禽”有关。可能因鹤能高翔,在汉代人的意识中可以与天界沟通。
汉武帝后元元年春二月诏言:“朕郊见上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罔,靡所获献。荐于泰畤,光景并见。其赦天下。”所谓“荐于泰畤,光景并见”,实际上是说在与上帝对话时看到了显现为“光景”的异常的吉兆,于是“大赦天下”。
“光景”,有可能即“光影”。《释名·释首饰》:“镜,景也。言有光景也。”《初学记》卷二五引《释名》:“镜,景也。有光景也。”《太平御览》卷七一七引《释名》同。然而《释名·释天》又说:“枉矢,齐鲁谓光景为枉矢。言其光行若射矢之所至也。亦言其气枉暴,有所灾害也。”
汉代文献所见“光景”,颇多神秘主义色彩。《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关于秦的祭祀体系的介绍,说到“光景”:“……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有同样的说法:“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列传·邛都夷》:“青蛉县禺同山有碧鸡金马,光景时时出见。”《水经注·淹水》:“淹水出越巂遂久县徼外。东南至青蛉县。县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马碧鸡,光景儵忽,民多见之。汉宣帝遣谏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鸡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褒《碧鸡颂》曰:‘敬移金精神马,缥缥碧鸡。’故左太冲《蜀都赋》曰:‘金马骋光而絶影,碧鸡儵忽而耀仪。’”
《太平御览》卷三引刘向《洪范传》曰:“日者昭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纪,群阳之精,众贵之象也。”日光,是“光景之大纪”。《艺文类聚》卷四二引魏陈王曹植《箜篌引》也说:“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艺文类聚》卷七四王褒《为象经序》曰:“昭日月之光景,乘风云之性灵,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则说日月天光都是“光景”。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写道:“西河筑世宗庙,神光兴于殿旁,有鸟如白鹤,前赤后青。神光又兴于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钟音,门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上乃下诏赦天下。”第一例“西河”事,“神光”与“有鸟如白鹤”并见。这种“光”或说“神光”与疑似“白鹤”的同时出现,可以有益于我们理解汉武帝诏文所言“光景并见”。所谓“神光兴于殿旁”,“神光又兴于房中”,同时又“有鸟如白鹤”,也可以理解为“光景并见”。这可能是对于汉武帝后元元年所见神异现象的一种复制。我们现在还不能准确解说汉武帝诏文所言“光景并见”究竟是怎样的情境,但是有理由推想,可能出现了与“神光兴于殿旁,有鸟如白鹤,前赤后青”类似的情形,于是使得这位垂老的帝王感觉到了某种“性灵”“神征”“祥”“怪”一类神秘的象征。而事情的缘起,与“鹤”有关。
来自“上帝”的“灵命”暗示,体现了对汉武帝“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罔,靡所获献”行为的真诚谅解和高度认可。拂去这一故事笼罩的神秘主义迷雾,可以察知当时社会生态保护意识得到以神灵为标榜的正统理念的支持。而鹤与天界的神秘关系,似乎也因此得到了曲折的体现。
(本文摘自《秦汉英雄气运》,王子今著,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定价: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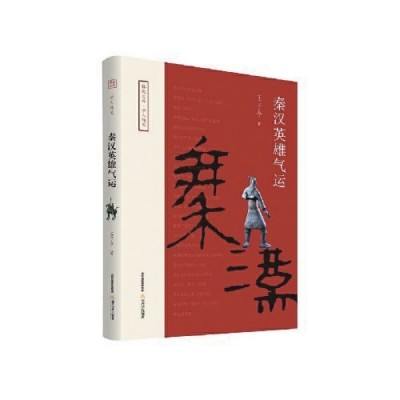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