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从事文史研究的青年人可能都曾陷入疑虑: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师“童子功”坚实,四书五经等典籍从小就背得滚瓜烂熟,而自己是到大学乃至研究生时才选定专业,这还来得及吗?
刘跃进先生撰著的《从师记》以细致翔实的现身说法,回答了这个问题:学无早晚,转益多师,夯实根柢,必有成就。
要说“童子功”的涣散、中小学的“先天不足”,大概最严重的是刘跃进先生这一代人。他出生于1958年,名字带着时代的烙印,小学、初中、高中完全处于“文革”期间,而小学多次转校,还曾在河南信阳潢川黄湖农场生活三年。因此少年所受教育的状况可想而知,他坦称:“我在小学和中学那几年没有怎么读书,天天搞运动,每天就上半天课,每个学期都要学工、学农、学军至少一个月。”(《“跃进”时代萌生的文学梦想》)
1977年恢复高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先声,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当时刘先生下放到北京远郊农村插队落户,干农活之余复习迎考,考入南开大学。当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半晌说不出话来”,“在返回大队的路上,我手舞足蹈,引吭高歌,恨不得要把自行车举起来”(《“我在 这战斗的一年里”》)。只有经历过那种岁月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激动和喜悦。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刘先生正式开始学术的入门训练。专业的选择曾经几度游移,直到1979年春天听到叶嘉莹老师讲古典诗词,“才知道古典文学原来那么美”(《从师记》),于是“吟诵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诗句”(《好诗不过近人情》),决定选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后考上杭州大学第一届古籍整理研究生班,接受科班训练,改变了读书方法,明白了一个关键问题:所谓基本功,就是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小学知识,下这些“笨功夫”就是为了夯实根柢。
在学术生涯中,刘先生有幸认识了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衡、沈玉成、傅璇琮、刘桂生、程毅中、魏隐儒、王伯祥、蒋礼鸿、陈桥驿等名师,虚心好学,每每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绝活”,融会贯通。兹据书中所记,例举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治学方法:
罗宗强老师:研究作品要注意事迹编年,“许多作品,离开具体环境、心境,是很难了解真实含义的。事迹编年在这里就显示出重要性了”。“所谓精读,就是带研究性,一个作家一个作家来,大致做这样几个工作:版本、辨伪、系年(利用已有之年谱),思考若干问题。”(《从师记》)
姜亮夫老师:继承王国维做学问的特点,重视资料编纂工作,认为“编工具书这件事,我们研究学问的人,非做不可”(《记忆中的水木清华》)。让学生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时刻注意根柢之学,要打通文史界限,要让“每个同学成为通才,而不是电线杆式的‘专家’”(《好诗不过近人情》)。
傅璇琮老师:古典文学研究如同建筑工程,分为基础设施和上层结构;基础设施包括基本资料的整理、工具书的编纂等,看似容易,其实繁难。(《斯人已逝,德音未远》)
魏隐儒老师:“版本知识,是来自实践经验。”“名家都是苦功夫熬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走。”(《“小室无忧”》)
蒋礼鸿老师:倡导“读书有限偷懒法”,即充分掌握目录学知识,事半功倍。(《从师记》)
上述方法,大约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察本源,立根柢。如果要用本书的词语概括出本书的两个关键词,或许应该是:从师,根柢。
书中最后一篇《求其友声三十年——由一场学术演讲说起》,虽然列为“附录”,但却另有深意。文章记述第一次做学术报告是1992年在曲阜师范大学。1998年在扬州大学做学术报告时,当年曲阜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周广荣已是扬州大学的博士生,再一次听刘跃进先生作报告,并相识交谈。周广荣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二人保持交往,刘先生说:“在佛教和西域文明研究方面,广荣也真是我的老师。”不但善拜长辈为师,也能以学生为师,如韩愈《师说》所说“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这才是真正的“转益多师”!
经验之谈,弥足珍贵。青年文史爱好者或可以此书为师,涵泳其中的道理,免走弯路,掌握方法,学有所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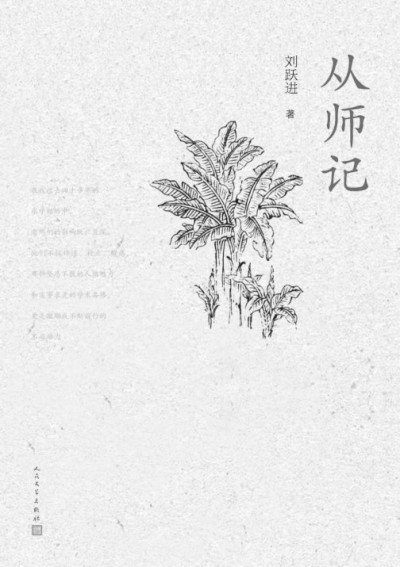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