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0日,著名历史学家、吐鲁番文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朱雷与世长辞,享年85岁。经其弟子刘进宝组织,由朱先生的生前好友与学生撰写纪念文章36篇,加上附录2篇、后记及99帧照片,编成《朱雷学记》(以下简称《学记》)一书,于2022年5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对朱先生的缅怀追念。
笔者的硕士导师齐陈骏先生曾在1979年赴武大进修,聆听过唐长孺、陈仲安先生的课程,并与唐门弟子朱雷、陈国灿、黄惠贤、卢开万诸先生相熟。齐先生与朱先生同龄、同乡,《学记》中有两帧珍贵的合影照片(174—175页)。齐先生给我们上课时多次提到朱先生,并介绍他的学问。笔者工作后在敦煌、南京、武汉、兰州、杭州等地与朱先生多次谋面,有幸亲聆教诲,领略风采;近廿年前笔者博士论文答辩,朱先生也曾评阅拙文,给予批评指正。朱先生离世后半年,齐先生也撒手人寰,两位好友同聚天国。如今拜读《学记》,再次感受朱先生的高尚学风和人格魅力,感慨万千!
《学记》中的文章分两组,前23篇为朱先生生前好友所写,涉及15家单位;后13篇为门下弟子所写,涉及13家单位,可见朱先生学友遍神州、桃李满天下。其实,他作为国际知名学者,在国外也有许多学术朋友,估计是编者不及约请撰文,致成缺憾(朱先生去世后,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会长伊藤敏雄、日本唐代史研究会及佐川英治、气贺泽保规、葭森健介都发来唁函,表示哀悼慰问)。读罢书中的文章,朱先生形象丰盈饱满、栩栩如生。
一
朱先生对待师尊的态度,常为学界所称道。他是唐长孺先生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1974—1986年随唐先生到新疆、北京、上海整理吐鲁番文书,十多年师徒相依,情同父子。有几位作者不约而同说到,朱先生为唐先生做饭烧菜、炖汤熬药,特别是唐先生眼睛不好,下楼梯时由朱先生搀扶,并且一步步数台阶以作提醒,以致后来养成下楼必数台阶的习惯。郝春文感叹道:“像朱雷先生这样,长期服侍老师,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很多具体杂务,是我至今仅见的一例。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当代尊师重道的典范。”(51页)
朱先生不仅对自己的老师数十年如一日细心服侍,恭恭敬敬,而且对学界的师长辈也同样执弟子礼,并与同辈学人保持真挚可贵的学谊。王启涛说,“老一辈学者是非常重礼数的,朱雷先生也不例外”(125页),并深情回顾了他的两位太老师张永言、项楚与朱先生之间的学谊。同龄的姜伯勤称朱先生为“师父”,正是因为称道朱先生坚守尊师重道的学术伦理,“朱雷先生正是这种伦理的一位很好的守护者和践行者,这更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总称他‘师父’的原因”(139页)。万毅回忆有次在南京开完会后,朱先生拿出三袋盐水鸭,嘱托他带回广州分赠姜伯勤、胡守为、蔡鸿生先生。万毅背着盐水鸭千里南归,背负的岂止是盐水鸭,那是师尊之间的真挚情谊,也是朱先生对同道情谊的淳朴表达。
二
朱先生对学生的关怀无微不至,亲如子女。从13位弟子及其他师友的文章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他对学生的无比关爱之情,完全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朱先生对学生是严的。有三位作者提到朱先生有个原则,即坚持不为学生的书写序。马志立回忆道:“先生以自我解嘲的口气说,自己学生写的书,说写得好有自夸之嫌,有瑕疵则应于出书前指出。”(288页)卢开万为吴成国《六朝巫术与社会研究》所作序言中说:“朱雷教授却认为,老师为学生的书写序,在外人看来不免有回护之嫌,坚持这序言不能由他来写。”(254页)朱先生唯一破例为学生的书作序,是陈翔的遗稿《陈翔唐史研究文存》。这次破例饱含了他对学生的无限哀思。难以想像朱先生在哀痛之下是如何握管落笔撰就序文的。马志立说:“面对荣誉或职位之类,同等条件下,先生不会推荐自己的学生。”(288页)刘玉堂也说:“当自己或亲近者的利益同他人发生冲突时,他选择的是退让。”(209页)吴成国谈到2019年教师节去看望朱先生,先生以颤抖的手写下一句话送他:“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第256—257页)吴成国当时已是教育部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朱先生听他汇报完项目进展后写下的文字,别有真意,既有对学生的期望,更是蕴含无声的严格。
朱先生对学生也是慈的。读《学记》可以感受到他对学生关怀备至,学习、工作、生活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吴成国回忆1987年帮朱先生誊抄文稿,抄完后获赠一本《通典》,定价23.7元。马志立也说朱先生有次在书店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兴冲冲取钱让他买回,然后说送给他。朱先生还购买多套《太平寰宇记》一一分赠学生。他对学生的关爱还延伸到学生的家庭。马志立读书时寒假回家,朱先生以问候父母的名义予以资助,还预备礼物让他带回家,却不准回赠任何礼物。马志立回家提亲前两天,朱先生嘱其四事:一嘱提亲注意事项,二替他备好礼物,三嘱另备其他何种礼物,四嘱路上注意安全。关切之情,殷殷之嘱,如对子女。他还每年为马志立的儿子准备糖果和压岁钱。对待张小刚的女儿也一样,专门去超市的进口商品柜台买巧克力之类的零食,让他返回甘肃时带给女儿。马志立和权家玉都回忆说,朱先生自己生活节俭,但每年两次邀集学生到豪华餐厅吃饭,并说“这是唐先生的做法”(289页)。
从学生们的回忆可知,朱先生是在家中给研究生上课和答疑的。这种在今天算是教学事故的教学形式,却成为学生们最深刻的记忆。崔世平说“因为是在家里上课,气氛相当轻松”,“最后一次课,朱先生特意带他们去广埠屯菜市场二楼的书 店买书”(308—309页)。魏斌也描述道,“先生给我们俩开魏晋南北朝史籍介绍课,还有每周的读书答疑,都是在家中。上课时介绍到某一本书,就直接从书架上取出,观摩翻看,非常直观。天气慢慢冷了之后,有段时间还干脆搬几个小板凳和一摞书到阳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讲课或答疑,一边翻书”,“每次讲一阵子课之后中间休息,经常谈到专业以外的内容,而且一旦开始就很难再收回来,因此每次上课的下半场,往往成为海阔天空的闲谈”(275—276页)。读孙继民的文章可知,每周一次的答疑是唐先生以来的传统,由学生提问,唐先生作答,朱先生和陈国灿先生协助检查批改读书笔记,一同参加答疑。另外,陈仲安、黄惠贤、卢开万、程喜霖先生也曾短暂加入答疑课。七位老师与两位学生的家中答疑,会是怎样的一幅风景啊! 这一家中答疑的传统为朱先生所继承,继续带领学生在自己家中走过一年又一年。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下,这道别样的风景已经难以再现。《学记》作者中很少有人谈起教室的课堂,但家中授课和不占课时的私下授受却又如此楔入人心。对比两种教学形式,岂不令人深思!
三
朱先生不仅对门下弟子宽严相济,而且对其他青年学子也热心相待。黄楼虽然毕业于本单位,但不在朱先生门下,朱先生也可以不计较不为学生之书写序的规矩,为黄著《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作序,所用“丽龟达掖”的典故,使之顿时名扬学界。
对外校的青年学子也同样关爱和奖掖有加。1990年中山大学研究生向群游学到武汉大学,登门拜访朱先生,不仅受到接待,而且朱先生还说“我考虑考虑,我需要点时间准备,理一下思路,然后给你讲一次课”(108页)。两天后在家中给向群讲了一上午课,从唐史讲到敦煌吐鲁番文书,开阔了一个年轻学子的学术视野。谷更有跟朱先生做博士后以前,先在河北师大读硕士,论文答辩时朱先生前来参加,答辩后孙继民带他去宾馆拜访朱先生,获得批注满纸的评阅论文。他说:“回到宿舍,拿出先生的评阅论文,看到那密密麻麻的、逐字逐句的修改,红色、黑色的圆珠笔、钢笔字批注,我又一次震惊了,这哪只是评阅,简直就是修改了!这本评阅论文我一直保存着,不只是为了激励,还有感恩和永远的纪念!”(268页)王启涛与朱先生是在吐鲁番开会认识的忘年交,夜里两人竟聊了个通宵,到早晨六点才稍微睡会儿,而74岁的朱先生马上又赶去新疆师大讲座。翌年,王启涛背着300万字的《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书稿,到武大请朱先生审改和写序。朱先生每天起早贪黑,逐条审改,“连在室内挪动一步都舍不得,生怕耽搁时间”(127页)。
四
朱先生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尤其在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正因此,他深深地热爱新疆和敦煌,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大西北。
《学记》书后有其论著目录,除了参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书外,还单独出版《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等三本论文集和专著《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发表60篇论文。许多人都说朱先生的论文风格、神韵最像唐先生,传承了唐先生三大治学领域中的一支,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荣新江说,“朱雷先生写出来的文章不多,更没有整本的专著”,“不过‘少而精’,朱雷先生每次出手,我想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做法,所以每篇文章都有新意,而且总是出奇制胜,读来启发尤多”;“扎实的文章中透出一股灵气”(88—89、96页)。魏斌也称其论文“允为精品”,“基于史料敏锐感和想象力的‘巧思’。先生读书多,据说连唐先生都称赞过这一点。这种广泛阅读、博闻强记,再加上秉性聪慧,使得先生的史学考证有一种灵气,巧妙处往往令人赞叹”(280页)。朱先生的论文大多发表在武大的刊物或会议论文集,校外期刊上仅在《敦煌学辑刊》《吐鲁番学研究》《河北学刊》及以书代刊的《丝路文明》《广州文博》各刊一篇。若按现今评价体系,连通过日常的考核都困难,但他却以论文的质量取胜、而非期刊的所谓档次为标准。
朱先生最初在唐先生指导下阅读敦煌文书,后来参加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历时13年。近75岁时,他再赴新疆整理文书,最终出版《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因年事已高,这次西行由朱夫人和博士后崔世平陪同前往,住在新疆博物馆对面的酒店,一日三餐就在附近的四川饭馆吃饭。寒来暑往,半年时光。他生活向来非常节俭,负责接待的新疆博物馆鲁礼鹏说:“每次吃不完的菜,都让老板收起来,晚上热一下继续吃,我听后真想哭。”(143页)
朱先生对敦煌也是热爱的,称其是“魂牵梦绕”的地方。他最早从阅读敦煌文书入手,撰写了许多敦煌学论文。他研究敦煌、吐鲁番的论文基本上各占一半,特别是利用敦煌变文研究唐代历史,别开生面,深得学界称赞。张小刚是武汉人,求学于武大,毕业后本来要留汉工作,但朱先生对他说,“如果有志于学术,就要去国内重要的学术单位,敦煌现在缺人,希望你去敦煌刻苦面壁十年,一定能取得一番成绩”,并为他给敦煌研究院段文杰院长写推荐信,于是张小刚就到敦煌工作了。后来张小刚回武大攻读硕、博士学位,朱先生说,敦煌地处偏远,人才匮乏,能够为西部地区培养一个人才,他是真心地高兴(294—295页)。张小刚明白朱先生的意思,断绝了返回武汉工作的念头,回到敦煌继续坚守。
朱先生学识广博,举凡历史、文献、考古、天文、地理、昆曲、近代公案小说、俄苏小说、民俗、掌故、革命史、武侠、中医药,无不涉及。之所以如此,孙继民透露一个奥秘,那就是朱先生随身携带个小本子,见缝插针,随时随地,记诵不辍;并说:“绝少见到如此学习记诵的人。如果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先生。”(201页)
五
朱先生生性不愿给人添麻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品质。徐少华说朱老师给广州博物馆捐书,8000多册书都是自己在家整理,花了一年多时间清点、编目。
生病住院时,初入师门的马志立去医院拜谒,朱先生严令不准携带任何礼物,也不准再上医院探视。马志立说,无论是在上学期间抑或参加工作后,朱先生生病住院都不准他到医院探视,也很少让学生帮忙取药。每次外出讲学或去新疆,也从不让学生接送。
很多人都说朱先生是一位纯粹的学者。如杨果文章的标题为“做一个纯粹的学者”(45页),刘进宝文章的小标题为“视学术如生命的纯粹学者”(226页);向群也说:“在我的眼里,朱老师是一个学术世界中的完美主义者,一个纯粹的求道者”(122页);荣新江先生称“他不是一个善于行政的人。他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88页)。这些不约而同的评价,从他者的视角展现了朱先生作为学者的纯粹性。他虽然不善于行政,但也从事过行政,当过历史系主任、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所长,深知行政工作可能占用太多时间,影响学术发展,所以他特别不希望年轻人在行政上耗费精力,而应专心于学问,做好教学与科研工作。他跟弟子魏斌谈过一次话,说“以后专心教学和读书研究,不要做任何行政工作”(282页)。这番谈话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学生在学术发展上的真正关怀。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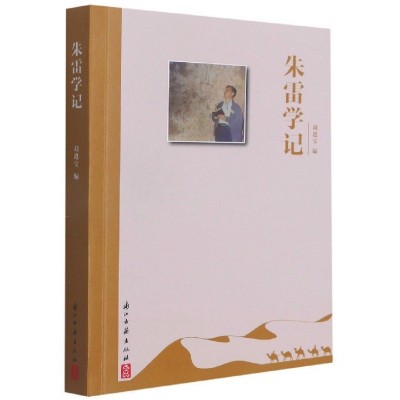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