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您认为什么样的书适合作为枕边书?
王中忱:枕边读书其实是一种奢侈,而在我能读书的时候,绝无享受这样奢侈的条件。我出生于东北松辽平原腹地的一个村庄,在我祖父那一代,整个村子识字的人屈指可数。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四叔读过师范学校,在乡村小学教学,他有一木箱藏书,平时总是很珍贵地锁着,但对我一直很慷慨,尤其是过春节的时候,还会同时多借几本给我。那就是我的节日盛宴。我哥哥比我高三个年级,他或借或买,总能搞到一些小说,读完了就转给我。
读中学在“文革”期间,学校里本来不大的图书室也关闭了,难有公开借到的书,但四叔的藏书箱仍在,哥哥也仍然有办法找到一些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几部小说名著,确实都是在这一时期读的,并且每一部都反复读了多遍。还曾走过十多里路,到一位同学家借到线装的《论语》《孟子》拿回家里抄录。不过这些书都是坐着读的,那时我的家乡还没有电,晚上点油灯睡土炕,没有卧读的条件,并且因为家里永远有干不完的农活和杂活,家长并不鼓励甚至很反感我们读闲书,我们怎敢把书堂堂皇皇地放在枕边?
读枕边书,是上了大学以后的事。中文系的学生,好像无论是哪所大学,贪恋在宿舍卧读都胜过去课堂正经听讲,我也不例外。后来留在学校教书,有了工资,生活必需开支之外大都用来买书,买回来书,大都要躺在枕边翻看一遍,然后再选必要的精读,所以,在我看来,除了大开本的图册,其他普通开本的书都适合做枕边书。而随着关心的领域和兴趣不断变化,我的枕边书也不断变化,没有哪本书一直放在枕边反复读。
给予您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撑的书有哪些?
王中忱: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我读书比较杂,从很多书里汲取到精神营养,从一般所说的经典著作,到民间故事和歌谣,都让我感到忘我的愉悦,也都曾给我不同方面的启迪,这些书综合起来形成我的“精神支撑”。但在不同的年龄段读书重点确有不同,年轻时候热衷读文学作品,后来兴趣逐渐转到理论著作,然后是历史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在经过了多学科阅读之后,最近重新回到了文学。
在现代文学研究上,您也有很多成就,比如对丁玲的研究,《重读晚年丁玲》一文曾影响很大。您经常重读作品?选择重读的作品有哪些?
王中忱:我确实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开始走进学术研究领域的,成就完全谈不上。我经常重读作品,有时是因为感到有些作品所牵连的文学史问题需要重新讨论,以前重读“晚年丁玲”是如此,最近重读茅盾的小说也是如此。但有时却不是为了直接的学术课题,而是为了一些更广泛的思考和困惑,最近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想从历史纵深和人心机微处去了解俄罗斯和欧洲。
我对您早年的求学经历很感兴趣,在日本求学的几年,您阅读最多的书籍是哪些? 您在《现代文学路上的迷途羔羊》一书中提到,自己对日本文学的兴趣缘自尾上先生。他在读书方面对您有怎样的指导?
王中忱:我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其实已经人到中年,此前在大学教过书,在文化出版机构工作多年,专业范围主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理想的职场规划应该是沿着一条熟悉的路走下去,但我这个人比较随性,尤其是在能够从日文原文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直接感受到词语和音节的微妙律动,叙述语调的曲折变化,从此就欲罢不能。在日本文学课堂上尾上先生的鼓励给了我信心,但在读书方面并没有给多少具体建议。当时日本的大学对学生基本是放养,这也适合我的个性,完全凭着兴趣自由漫读,后来集中到了左翼文学和新感觉派文学,特别是中野重治和横光利一的小说,还有前卫性诗歌。同时也一直关注二战以后活跃于文坛的作家,特别是“战后派”一脉,如大冈升平、堀田善卫、大江健三郎等。概言之,我关注的范围是日本的现当代文学。
寻求读书指导,其实并不限于所读大学的课堂之内。当时我们几位同学组织过读书会,一起研读评论家吉本隆明的《对于语言而言美是什么》,这本书迄今没有中译本,在汉语读书界鲜为人知,但在1960年代的日本读书界风靡一时,可说是一本当代的经典。
您曾获《世界文学》翻译奖(2001年),是翻译什么作品? 能否谈谈您的翻译理念? 比如选择什么样的作品翻译,有何标准?
王中忱:翻译的是大江健三郎的短篇小说《环火鸟》(日文原题《火をめぐらす鳥》),是时任《世界文学》编委的许金龙先生约稿,文字上也经过他的反复敲打。说来惭愧,尽管我很热爱文学翻译,但由于学校里各种杂务缠绕,实际很少有时间用于翻译,自然完全不敢奢谈“翻译理念”。但如果继续翻译小说,我愿意选择有思想深度且在叙述方式和语言表现上有新探索的作品。怎样把原作的“探索”在汉语中体现出来,让读者通过译本也能感受得到,这是文学翻译的难题,也是让译者保持翻译热情的动力。
上世纪90年代初,您从日本回国,托运了几十箱书,都与日本文学相关。能说说都是什么书吗? 在您的收藏中,最珍贵或最有纪念意义的是什么书?
王中忱:我1989年4月赴日留学,1992年3月回国,那时候办理护照签证等出入国手续非常烦难,充满不确定性,我不知道以后是否有机会再到日本,而我又想把已经开始了的日本文学的学习继续下去。对比日本的中国研究,当时中国的日本研究基础薄弱,图书资料也非常匮乏,我搜购的书主要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和相关的研究著作、辞书等。
我买书不是为了藏书,从收藏的角度说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可言,但在书店里,当遇到期待很久的旧书,比如梁启超、鲁迅那一代人曾经读过的版本,或者完全没有预期却让人见了就移不动脚步的新著,那种兴奋和激动,过后也难以忘却。对我个人来说,这样买来的每本书都很珍贵,有纪念意义。
中国和日本文化交流的进展超出想象,后来我多次去日本学习、教书和从事学术研究,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每次回国肩背手提的行李里占分量最多的仍然是书。而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买书的范围也从文学扩展到了思想史和文化史。2020年4月我从京都仓促回国,国际邮递因新冠疫情停止营运,买的书都放在了客座研究的机构里,最近才由研究所的朋友寄到北京。拆开邮寄纸箱,看到两年前一本一本买来的书完好归来,真是又惊又喜,感慨万千。
这些书至今还在您的书架上吗? 很想知道您如何整理书架? 那么多书,怎么收藏? 怎么清理?
王中忱:这些书分别放在家里和学校研究室的书架上,大致按主题分类摆放。因为书架已经挤得满满,也有一些书装进了纸箱里,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所以过一段时间确实需要整理一下,把某一专题的书归拢上架或下架。研究生们可以到研究室借阅,他们自行管理。总之,这些书都在用,还说不上藏。
我也陆续把一些书送给学生和青年老师,但有时担心会给他们添麻烦,因为现在大家都缺少放书的空间。书有聚有散,能够散到想读的人那里就好。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清理吧。
您对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等研究颇多,能否谈谈您和日本作家的交往? 您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是怎样的情况?
王中忱:作为翻译者和研究者,我和大江先生、加藤先生见过面谈过话,但不能说是交往。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能有机会亲接謦欬,从感性层面接近他们的思想和文学,和只读文字文本大为不同。
加藤曾长期旅居法国。大江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他们的知识背景带有浓重的欧洲色彩,但他们都尊重汉文圈的传统,如加藤在《日本文学史序说》里把近代以来被日本的文学史家放逐了的汉文写作放置到重要位置。同时,出自对近代日本“脱亚入欧”论和对亚洲邻国侵略历史的反省,他们都积极参与了二战之后第三世界作家发起的文学运动,如亚非作家会议。
加藤和大江都对鲁迅有深刻理解,大江还特别关心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我曾亲眼看到大江对照英文、法文、日文译本阅读莫言的小说,那样诚挚用心,非常让人感动。
2021年9月,您在清华大学日新书院2021级开学典礼的致辞上,曾引用《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我的几何人生》等阐述自己“人文学是具有大用途的知识”的观点。您经常会为学生推荐书吗?
王中忱:我一般不给书院学生推荐阅读书目,因为每门课程的老师都会开列书单。有时听到学生抱怨说书读不过来,我会说要注意读书方法,但也不过是广泛浏览和专精研读相结合之类的老生常谈。
基于自己的教训,我会提醒学生注意培养扎实的读书能力。书院设有《说文解字》研读、古文字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等课程,还设有拉丁文基础、基础梵语等教授欧亚古代语言的课程。先贤说:“读书须先识字”,开设这些课程,就是希望同学们在年轻的时候练好童子功,将来能够从原文直接研读中外经典。
研读经典是人文学术的基础,但读书不能也不必总是正襟危坐,我也愿意鼓励学生们凭着兴趣去广泛阅读,不预设所谓研究目的,涵养性情,全面提高素养,这同样是重要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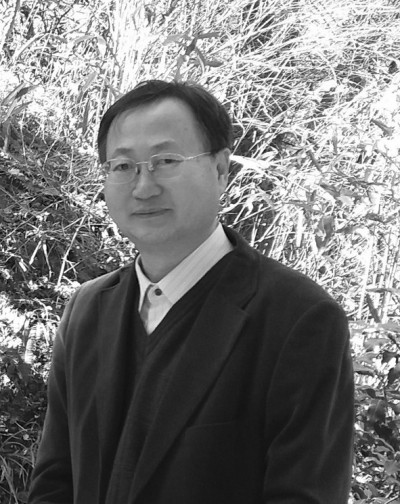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