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是作为叔本华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译者,石冲白(1911—1970)恐怕很难再唤起后人的记忆。他是湖南新邵县人,因为家世关系早年即有留德机会,1928年随父石醉六(原名石陶钧,1880—1948)赴柏林,1929年秋入海德堡大学,在哲学院(in der phil. Facultät)注册,1930年转入柏林大学。
石冲白在柏林大学的导师(Referent)是彼得逊(Prof. Dr.Petersen),另一位导师(Korrefer⁃ent) 是 胡 伯 讷 尔 (Prof. Dr.Hübner),考试导师(Prüfer)是哈同(Prof. Dr. Hartung)。这几位都是有名望的学者,尤其是彼得逊(Ju⁃lius Petersen,1878—1941),乃是著名的日耳曼文学学者,1920年起任教于柏林大学,长期任日耳曼语文学讲座负责人(Direktor des Ger⁃manischen Seminars),并于1926—1938年间兼任歌德学会会长(Präsident der Goethe-Gesell⁃schaft)。所以石冲白可当得“名师高徒”之谓,虽然他日后并未以从事专业研究为业,但其深厚的德系人文学术知识基础,则是就此打下的。石冲白也在简历中特别向彼得逊致谢:“我要向彼得逊教授致以特别谢意。正是在他富有耐心的关注下,我的工作得以完成。”
据说他在柏林期间主要研究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但完成的博士论文却是《作为心灵诗人的让·保尔:对其大型长篇小说的若干主题与性格的探索》。这篇论文被收入当时的数种西文书目,譬如《现代语言评论》等。石冲白提出的这个“心灵诗人”(Dichter des Herzens)概念颇为有趣,因其涉及如何理解让·保尔(Jean Paul,1763—1825)这个人物的诗学定位,作者开篇就称:“每一位精神伟人,无论是思想家还是诗人,在其哲学探索与文学创造中都有一个重心,由此而聚集他们的思想或感情。”可谓是高屋建瓴,起笔不凡,接着他举例说明:“如此在康德,触手可及的就是他对先验唯心主义的综合先天,在费希特就是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我’和‘非我’,在斯宾诺莎就是他对泛神论的思想和广延,在莱布尼茨就是他的绝对先验论的不可分的单子。如此在歌德就是在不忽视个体的前提下对于共同体福利的认知,正如他在《浮士德》第二部中已揭示的;在席勒就是理想人性经由审美教育通向对美的热爱,在莱辛就是对理性的自白,在诺瓦利斯就是神奇的理想主义。在每一位思想家、每一位诗人的无限财富中,一个中心点会被逐渐呈现出来,它能够而且必须被用作观察思想或文学创造之星辰大海的伸缩自如的物镜。”实事求是说,这段德语的表达真是有品位,不仅内容上纵横捭阖,对德国古典诗哲信手拈来,而且只言片语点评颇为到位,很能见出作者的见地;即便就德语语言本身,也是言简意赅、清晰明白,很能显出作者的学养和手笔。
石冲白是自己重新选择德语文学为专业的,所以他是有兴趣而且能深入其中的。这同时也涉及人文学科知识的兼通性问题,譬如他对于哲学是有自己的见解的:“哲学是一般人所共同有的,因为人人有他的行事准则,这些准则都是他或她对于人生的了解和信念所造成的。在一般人接受或保有这种信念是被动或习惯的,不再加以思索或推求,那些信念确定了他或她行事的准则,即告诉他或她作价值的判断,告诉他或她在两可之间选择。”然后他提炼出一个概念,即“信念系统”,他强调:“事实上,任何人都有他一套信念系统,无论贩夫走卒都不能例外的。”然后他就此作出定义:“对于这些信念加以缜密的推求、分析、比较,那就是哲学。推求、分析、比较的结果也可形成信念,经过许多的媒介又可影响或范铸一时代人们的共同信念。譬如宋代的理学诸大师,在他们的小异大同之间,形成一种信念的主流,中国社会保有儒家礼教不能不归功于他们。在西洋,有卢梭、陆克的哲学,经过多种多层的媒介而成为西洋人的自由观念与功利主义。”他甚至明确地指出了观念与现实的密切关系:“我们有什么样哲学的主流,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哲学与实际生活之关系有如是密切者。”此处仅是借助于评价朱光潜的一篇文章就引申出自己的思考,并能结合时代背景和历史经验提出独到的主张:“在一个旧的社会秩序解体的时候,各种信念是泛滥无归的。这种泛滥的状态如果延续下去,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也很难产生。社会的混乱可能继续下去。在社会不安定的时候,要收拾残局必得有个许多人共同承认的办法,——一个行事的准则、一个共同的信念。扰扰攘攘,它自己是不会变好的。所以,在一个文化集团中,新旧交替的时代,更应该勇于创立,或固执一种已有的信念,或哲学。”遗憾的是,石冲白归国后的著述并不多见,甚至也未成为职业学人,像这样颇富智慧和见地的论说是需要精心钩沉的。那么,究竟何以如此呢? 按照他留德完成的博士论文的水准,相比冯至、陈铨,真可以说是各有擅长,甚至未必就弱于彼,但日后的走向却迥然不同。是时耶? 势耶? 抑或自身的局限?
作为柏林时代的留德同学,冯至提到过石冲白,1934年4月9日,“收从吾信,石冲白片”。两天之后的4月11日,“发陈铨信,石冲白、从吾片”。这至少证明,冯至在留德时代是有石冲白这个友人的,而且收复信件颇为及时。在这里涉及的几位之中,姚从吾、陈铨都是与冯至交好的朋友,前者是在爱卜西卡的朋友圈中,后者则不但是同学科的学友而且也有学术和文学上的知己身份,所以估计至少在当时,石冲白应不算是圈外之人。按照相关说法:“1955年,石冲白在德国留学期间的同学冯至,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一批),一级教授和一级研究员。此时石冲白正在接受劳动改造。”这自然是在比较视野下慨叹石冲白的“怀才不遇奈若何”与“身世浮沉雨打萍”。
可如何更好地来理解那代留德学人沉入历史的真实与错综复杂状况,则确实是一个考验研究者耐心与智慧的难题。陈光琴(陈铨之女)先生曾提供过若干老照片,其中一张是在皮歇斯堡火车站(Bahnhof Pichelsberg)前的合影,其中居于中间的就是石冲白、冯至。所以可见,他们在柏林期间,是有着一定交往联系的,假日里一起出去寻幽觅胜,完全是再正常不过了。按照姚可崑回忆他们在柏林时的说法,“那时他(指冯至,笔者注)几个每逢星期日常见面的朋友,如朱偰、蒋复璁、滕固、徐诗荃等人都已先后回国,好像他们把星期日悠闲的时间完全交给了我们二人”。显然,石冲白不在这个密切交往的名单上,但彼此间有直接交往的关系则是确凿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石冲白、冯至、陈铨都应是小范围的专业意义上的同学,因为他们都参加过柏林大学日耳曼语文学讲座,彼得逊教授应是他们共同的老师。石冲白还曾做过一些社会工作,譬如翻译《第六届世界地方行政会议报告书》。此会1936年6月在德国的柏林、慕尼黑举行,姚定尘(1905—1965)是时任中国驻德使馆二等秘书,作为中国代表参会并做德文报告,该报告之后寄回国内刊物发表,译者就是石冲白。这种情况大致类似于留学生与外交官的关系。
不过有一点信息不错,就是石冲白的命运很悲惨,不但学无所用,而且历经苦难。1936年,石冲白学成归国,先后受聘于南京的陆军大学、中央军校武冈第二分校、同济大学(四川李庄)、私立民国大学等;还出任过湖南的《中央日报》总主笔、副社长、社长等;著有《生活的信念》《三民主义理论的研究·发凡》等。他虽在多个机构任职,却似乎并未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下去,期间曾于1942年辞职归乡,主要是为了侍奉老父。确切地说,石冲白未能在学院系统的常规轨迹中得以发展。
此外,时代背景的大转换和大动荡也是石冲白及其同时代人不得不面对和应对的重要语境。1950年,程潜推荐他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按理来说是在新中国获得了一个较好的社会身份;但他却在1954年被捕,理由是“进行反革命活动”,1957年被判有期徒刑五年,旋即因表现好而被提前释放。这固然是为时势所弄,是被牵连而身陷囹圄,但与其自身热衷政治或许不无关系。
石冲白对于中国历史有独到见解,在政治与文化层面上也自有立场:“中国要完成它在世界上的使命,并以自救,便须以最高度的警觉性容摄西洋文明,使之升华,三民主义指示中西文化的融合,必须先恢复我固有的民族道德,能力,智识……即我民族原有的目的性成就及精神文明,‘虽至举动之徵’,也要‘诚中形外’,然后吸收自然与应用科学,组织与技术的统治等手段性成就,手段性成就终究是比较容易的,尤其在物质方面……中国与人类的共同出路,通俗一点说,中国这个文化集团里必须有像王阳明这一类的目的性规范,配合像安迪生那一类的手段性规范。三民主义的文化,是要我们向这种目标努力去创造的:以更高度的文化容摄高度的文明。”此意虽不能完全摆脱“中体西用”之路径,但确实不无新意,尤其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世界使命”,是有眼光也有境界的。此书有署名野游老人者的一篇极为简短的代序文字称:“向来的主义,都是意图伪向某一项生活的强调;而生活固彻始彻终是不能伪向某一项的,三民主义在此一点上,有其伟大性,即综合性。此稿能利用‘四线平衡’的原则为此主义作深纯的发挥;眼光独到,主义之津梁,民族之曙光已在不远。”这里特别褒扬的“四线平衡”原则,倒是值得注意,即以一种动态平衡的路径去实现整体性的系统思考。
石冲白对中国文化传统与士阶层的使命问题也颇有思考,譬如就借着评论张东荪文章之机会提出:“士虽为官然须臾不能离‘道’——不阿附独立为人之道——所以士是一个最困难的使命。”此语可谓画龙点睛,道出了中国之士的可贵之处,即“士以载道”—“士以弘道”—“独立之士道”! 可以与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相互映照。而这与他的家庭熏陶与教育经历当然是有关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世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种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长期文化传承,对于理解文化中国而言至关重要,此在清民之际亦然。一些大家族自不必说,诸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都因政治权力的获得进而延伸出更为广阔的文化意涵,有一些兼而有之的世家如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李鸿藻(李石曾)等更是影响深远,此类如徐树铮、石醉六等都可纳入,而且他们也都是由父子血缘关系而发生文化传承,这样的情况似乎并不少见。就石醉六、石冲白父子而言,他们在文化史上的一大贡献,或许应是“一论”的发明。此书虽未传世,但其思想有相当程度原创性,所谓“《一论》就是从最大的时空研究哲学,他扩大到宇宙(空间),到地球万物的演变进化(时间)来说明世界与万物”,至少就层次来说,石醉六的立意是阔大的,他提出:“创一”即宇宙之始,世界之始或生物之始可看作“一”;“演一”就是宇宙间有了这个“一”,不是静止的而是演变的、衍生的,出现了不同星球、不同的生物物种,并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变与发展……。石醉六穷毕生精力之遗著《一论》,也可视为父子两代人的合著,因为石冲白花了极大精力去完成前人未竟之业,甚至已改定其稿,更名为《大生物学》(或《极限实践论》),足见其已经意识到此书所深蕴的学理内涵,可惜此书散入历史风尘不得存世。也或许,此书仍存于世间某个角落,等待有心人的发现和它应有的命运?
观照石冲白的一生,不由长叹一声:“千古文章未展才”! 如果冯至、陈铨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的话,石冲白的学养、见地等才华,可能连百分之一都未留存与得到施展。如今留给世人的,只有石译的那部汉译世界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Vorstellung)。此书经由杨一之(1912—1989)校译,他曾在柏林大学就读,后以治德国哲学为业。两者有在柏林交集的可能,这种学术翻译合作也是需要有一定基础的。杨一之诗云:“我伤知己逝,萧瑟北风来。”不知其中是否也包括了石冲白?此书作为叔本华的经典著作已经是广为流传,在汉语学界重译复译已近成灾的情况下,石译本仍似“一枝独秀”,既可见出该经典哲学著作的魅力,同时也显出石冲白的学术功力与翻译贡献。
终笔感慨,临到心头的,竟是一句“士耽道违时命限”,作为留德学人的石冲白,其悲欢生命与学术探索或许不仅是某个个体的终结,也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家族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宿命?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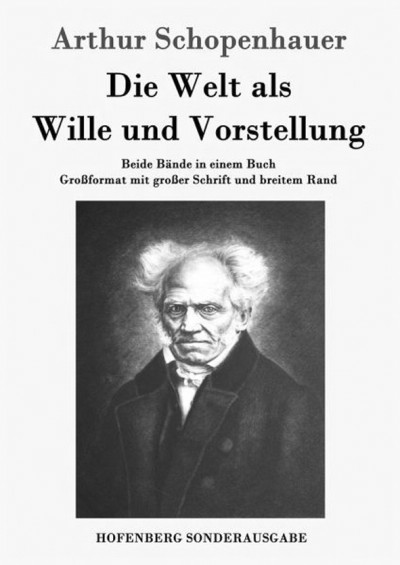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