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当清朝的统治结束以后,旗人的族群文化仍然或隐或显地在发挥着作用,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显明的部分。
在中国悠久曲折而波澜迭起的历史长河中,清朝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这是一个以少数族群为主导的政权,其不仅在中国全境建立起了统治,而且还延续了将近三百年。固然,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文化和文学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创造,但是清朝的独特性在于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融合满、汉、蒙等众多民族成分的旗籍族众在主要是满汉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还创造或者说形成了独特而又多姿多彩的旗人文化和旗人文学。这既是中国大的文化、文学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以其独有的个性丰富了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和创造。即便当清朝的统治结束以后,旗人的族群文化仍然或隐或显地在发挥着作用,而继续影响于旗籍作家的文学创作,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显明的部分。
石玉昆(约1810-1871),满洲旗人,生于天津,道光年间著名子弟书及评书艺人,长期在北京说书。其采撷故书传闻而演说的评书《包公案》,由听众记述成《龙图公案》,又在唱本《龙图公案》的基础上,产生了仅有白文而无唱词的《龙图耳录》,此书后经过其他旗籍文人的润色加工,成为《三侠五义》(所以,一般把本书标示为“石玉昆述”),至迟在同治十年(1871)已经成书。
文康(1794-1865年以前),满洲镶红旗人,出身于北京显贵的八旗世家。所撰《儿女英雄传》,署“燕北闲人著”,又名“金玉缘”“侠女奇缘”“日下新书”“正法眼藏五十三参”等。原书五十三回,现存四十回,包括缘起首回。此书可能是咸丰初年的作品。
赵焕亭(1877-1951),另有名绂章,汉军正白旗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为乡绅世家背景,是清朝初年“从龙入关”的旗人的后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武侠小说创作活跃于通俗文坛,奠定其武侠小说大家地位的是《奇侠精忠传》(正集128回1923-1925年连载于北京《益世报》,同时由上海益新书社陆续出版单行本。续集1926-1927年见诸报端。后来全书删定修改本再度刊行)。此后又有《清代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殷派三雄传》《英雄走国记》《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蓝田女侠》《山东七怪》《白莲剑影记》《边荒大侠》《马鹞子全传》等武侠小说创作,多由上海书肆出版。“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赵绂章悄然退出文坛”。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后改为葆翔),字霄羽,生于北京。王作为旗人,据徐斯年的研究,其祖辈属于镶黄旗。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谋生,1938年开始武侠和社会言情小说创作。武侠小说的创作情况是:《河岳游侠传》为其试笔之作,成名作为《宝剑金钗》,随后陆续写成“鹤—铁”五部系列(其余四部依次为:《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皆在《青岛(大)新民报》发表。另有《紫电青霜》《金刀玉佩记》发表。这些均为1945年之前的创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武侠小说创作有:《雍正与年羹尧》(1949年励力出版社之单行本改名为《新血滴子》),《风雨双龙剑》(1948年上海育才书局初版),《绣带银镖》《冷剑凄芳》(为前者的续集)、《宝刀飞》(以上三种均为1948年上海励力出版社初版),《燕市侠伶》(未完,1948年上海励力出版社初版),《洛阳豪客》(正、续二集)、《龙虎铁连环》《金刚王宝剑》(以上三种均为1949年上海励力出版社初版),《春秋戟》(1949年上海春秋书店出版)、《紫凤镖》(1949年重庆千秋书局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不再进行武侠小说创作。
老舍(1899-1966),满洲正红旗人,出生于北京。老舍为新文学作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武侠小说创作者,但他的很多作品有武侠文化因素,早期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猫城记》《离婚》中的某些人物就有侠客义士的影子。而抗日战争期间的作品,如《杀狗》《四世同堂》《康小八》等,一些人物身上的侠义因素更为明显。另外老舍创作的三部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的作品《断魂枪》(1935)、《五虎断魂枪》(1946年后1949年前)和《神拳》(1960)对于中国武侠文化的思考更为深入。作为知识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种比衬,旗籍作家老舍的有关创作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他旗籍作家武侠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
这些旗籍作家都有重要的武侠小说作品,有的作家武侠小说创作数量还十分巨大。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具有文类的某种规定性,在文学类型的内在要求规定下,不同的作家固然可以花样翻新,改写某些内容,增添新的质素,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基本规定性则是不变的。因此很多论者都把清代侠义小说作为武侠小说类型真正成形的标志。如石玉昆的《三侠五义》被认为是开今天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之门的作品,其后代作家的创作固然会与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差异性,但是在类型特征上,仍然被认为是武侠小说,这就为从整体上研究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保证。
谈及这些作家武侠小说的创作性质问题,亦即作品是文人通俗小说还是“民间文学”? 是否具有创作主体性质上的一致性? 尤其是后者则仍存在认识上的问题。胡适认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与石玉昆等的《三侠五义》,都是北方“民间的文学”,他说:
这五十年内的白话小说……可以分作南北两组:北方的评话小说,南方的讽刺小说。北方的评话小说可以算是民间的文学;他的性质偏向为人的方面,能使无数平民听了不肯放下,看了不肯放下;但著书的人多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也没有什么浓挚的经验。他们有口才,有技术,但没有学问思想。他们的小说……只能成一种平民的消闲文学。《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等书属于这一类。南方的讽刺小说便不同了。他们的著者多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经验的文人。他们的小说,在语言方面,往往不如北方小说那样漂亮活动;但思想见解的方面,南方的几部重要小说都含有讽刺的作用,都可以算是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既能为人,又能有我。《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都属于这一类。
这段论述似是而非。为了平民而写的“消闲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 南方文人写的就“往往”有“学问思想”? 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中没有作者浓挚的经验? 显然这样的论断都经不起认真的推敲。作者明显是基于启蒙的思想立场来贬低这些小说,仿佛将其降入“民间”就可以原谅了似的。
相比较而言,鲁迅的论述则要公允得多。鲁迅更是从创作风格立论,认为“文康习闻说书,拟其口吻,于是《儿女英雄传》遂特有‘演说’流风”。但仍然认为其属于文人创作,所以也明确点出“文人或有憾于《红楼》,其代表为《儿女英雄传》”。而对于《三侠五义》,鲁迅认为该书“及其续书,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儿女英雄传》亦然”,“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故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而这里的“平民文学”显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间文学”,更强调的是都市市井“说话”人的创作和创作风格方面的一脉相承。但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对《三侠五义》的创作情况当时并不十分清楚,鲁迅还是从大的派别角度进行分类,并没有将《三侠五义》与其他作品进行明确的区分,概而言之固然也说得通,但还是不能说明在晚清“侠义派”的小说中,《三侠五义》的创作成就何以远远高出其他作品。
实际上,《三侠五义》是经过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人改编加工过的,在保留原有的市井说唱艺术汁液的同时,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雅化或文人化了。
就旗籍作家具体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这一群体的创作虽然有着一般武侠小说创作的共同特征,但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性。这些作家无论其为满洲人还是汉军人,都隶属旗籍,都具有或曾经具有旗人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统治管理制度——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下的子民,旗籍身份对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和艺术风格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其族群文化意识或文化潜意识十分值得探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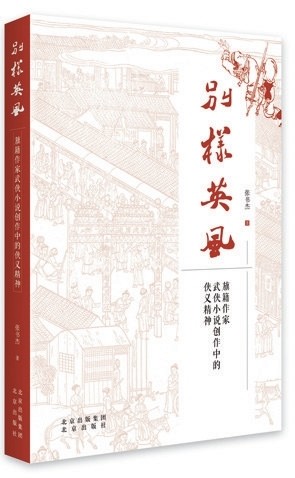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