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部编本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您为教师和学生编选、推荐书目,关于读书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您怎么看待阅读?
温儒敏: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情,要读什么书,怎么读,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功用与兴趣去决定的。真正的爱书者,他们把读书作为像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有事功的阅读,但更乐于自由的阅读,或者说私密的阅读。金圣叹所言“雪夜围炉读禁书”,就是“私密阅读”特有的享受吧,那真是读书的妙境。周作人也说过,书房是不可示人的,因为一看你读些什么,就知道斤两了。这有点幽默,但读书的确是“很个人”甚至私密的事情。
不过对于学生来说,开个书单,推荐一些经典,有些引导,也有必要,只是不宜强制。孩子也有他们的“私密”,应容许有阅读的自由。中小学语文课会指定学生接触某些经典,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凡是书单指定的,孩子不一定喜欢。经典与学生有隔膜,本来就不容易读,若又当作任务,有种种外加的“规定动作”,甚至处处指向考试,那就煞风景了。
既然“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即使指定阅读范围,也还是要给学生一些选择的空间,容许读一些“闲书”。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干脆把“哈利·波特”系列纳入推荐书目了,结果效果挺好,等于承认了孩子们可以读“闲书”——以前很多老师家长可能认为这类书是不该给孩子读的。其实像“哈利·波特”这类书非常贴近孩子,想象力超强,不说教而又有益,国人未必写得出来。孩子在奇特的想象世界中遨游,愈加爱上阅读了,兴趣也就培养起来了,有什么不好? 如果全都为了思想灌输或者考试升学,把读书的范围和方法都框死了,完全忽视孩子读书的自由,不容许有“私密”的阅读爱好,那就难于培养起读书的兴趣。
其实成年人也是这样,多数阅读都有明确的目的性,比如为了升职、炒股、理财、养生、交际、谋略,或者为了写文章发表,等等,这些阅读也许必要,但不见得能获取乐趣。人各有各的爱好,并非所有人都爱读书的。而真正的爱书人,不会随波逐流,不是哪些书走红就读哪些,他们选书总是有自己的喜好,有独立的眼光,阅读对他们是一种观望世界、涵养性情、安放灵魂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的确是功利性的阅读太多,自由的阅读太少,“私密”更谈不上,老师家长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好了,难怪许多孩子不喜欢读书。您是“四〇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小学中学,能否谈谈您当时的阅读?
温儒敏: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让人喘不过气来,私人的精神生活是被挤压的。即使那样,也还是有缝隙,有个人阅读的空间。关键是要从小就爱上读书,有这个习惯,无论多么困难,他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这跟学校教育有关。不指望学校能给学生什么读书的妙法,不压抑孩子读书的愿望就行。我是1952年至1958年读的小学,语文老师学历普遍不高,上课各讲各的,较随意,没有什么任务群、探究式、PPT等花样,但都比较尽职,重视阅读。印象深的是一位黄老师,每周都有一两节课就是讲故事,读小说。这种奇特的教法激发了我们读书的兴趣。课余很多时间就是疯玩,大人不会怎么管。总有一部分孩子是特别爱书的,那可以打开面向世界的窗户,满足好奇心,很幸运我是其中一个。阅读本身就是我童年生活美好的部分,这过程就很美,而不只是为明天的稻粱谋做准备的。我肯定会读当时流行的读物。50年代的主旋律书籍主要是苏联的作品,还有革命英雄故事。像《卓娅和舒拉》《绞刑架下的报告》《牛虻》《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我的一家》,等等,都读过了。我比较喜欢的是《三毛流浪记》,连环画,就这一本,不知道翻看过多少遍了。这种幼稚的阅读让我这个乡村小镇的孩子不断想象都市的生活,那些悲苦而又有趣的童年。而更认真读过的是萧三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薄薄的一本,很朴实的叙述,唤起我对毛主席的崇拜,佩服他的革命志向和毅力。我甚至还模仿青年毛泽东的风浴、雨浴,锻炼意志,硬是洗了五六年的冷水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是高小时读的,其中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让我感动。我很欣赏保尔的男子气概,以及崇高的使命感。他的那句“不要虚度年华碌碌无为”的名言,我至今能完整背诵,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那时的孩子有自己选择阅读的空间,真令人羡慕。能谈谈您童年的“私密阅读”吗?
温儒敏:除了读上面说的那些具有时代性的流行的书,私下里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古典章回小说。我家和外祖父家都有一些藏书,民国时期出版的,有的还是淡黄的玉扣纸印制,竖排繁体半线装,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包龙图断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说岳》《封神演义》,等等,——当然还有《西游记》。除了后者,这些小说多数思想艺术价值都不高,文学史家是不屑评论的,但民间流传广,故事性很强。我的办法是“连滚带爬地读”,似懂非懂地读,不求甚解地读。我很幸运小学时读了许多“闲书”,阅读面拓展了,自己的读书方法与习惯也逐渐形成了。这种自选动作的“私密阅读”,还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我的语文学习基础,主要是靠课外自由阅读奠定的。这些年我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从小学开始就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语文才学得好,过了初中再觉悟,就晚了。
问题是现在的孩子作业太多,没有时间读书。您上中学后还能有那么多自由的阅读吗?
温儒敏:作业太多的确是个问题,所以现在要“双减”。不过可以设想,即使不布置作业,孩子就有时间读书吗? 不见得。孩子嘛,精力无限,兴趣就是动力。没有兴趣,做什么都是拖延症,有兴趣,就聚精会神有的是时间。现在的孩子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大,但他们还是比父辈幸福多了。我不赞成“九斤老太”的说法。无论如何现在社会发展了,绝大多数孩子不存在温饱问题,而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基本上是在饥饿中度过的。若要比较,那时物质匮乏,没有现在那么多机会和诱惑,比较单纯,读书也就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时代不同,每一代都有一代的苦恼。
我上初中是1958年,接连碰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开门办学,参加劳动的时间比上课要多,当然影响学习。随后又是全国困难时期,吃不饱饭,很多成年人都水肿了。但想着电影里列宁“面包会有的”那句话,在那饥饿的岁月里仍然读了不少书,读书甚至成了转移饥饿的一种办法。这实在也是无奈的。
您是怎么喜欢上文学的?
温儒敏:大约上初中时,我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诗歌,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聂鲁达、惠特曼,等等,都找来读。我还是艾青的粉丝,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琳”。我自己也模仿着写诗,给《少年时代》《红领巾》等少儿杂志投稿。正是自由阅读充实了我的灵魂,伴随我挺过了艰难的饥饿年代。
高中我就离开小镇上的家,到县城上学了。那时高中生不多,上大学的更少,我参加高考的1964年,全国才几十万考生,录取率也非常低。但那时人们好像比较看得开,高考不像现在压力这么大,我们复习备考也不像现在这样大量刷题,老师是不太管的。我自然想考上大学,而且希望过黄河长江,离家越远越好,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我的备考不是刷题(也找不到往年的考题),而是拓宽视野,读一些比较深的书。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杨伯峻的《文言语法》,都过了一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也选读了部分。那时中华书局不定期出版的“活页文选”,专门刊载古诗文的,薄薄的册子,几分钱一本,我几乎都读过。这些阅读的目的是为了高考,却又不限于应考,毫无疑问对于我读写能力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因为读书有兴趣了,一天不读就不习惯,我高中时期的阅读面是比较广的。不光读文学,读《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革命小说,也读其他方面的书,如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史之类。
那时没有钱,买不起书,读书一般从图书馆借,或者就在书店站着读。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就很珍惜,会抓紧时间读完。记得《青春之歌》出版时,学校没有钱买那么多书,就准备了两本,每隔几天撕下十几页,正反面贴在公告栏上,让学生围着读,像看连续剧似的。现在我藏书很多,可戏称坐拥书城了,反而失去了当年对于书的那种珍惜与敬畏。
高中时期,我对于书的确有种崇仰之心,还喜欢读一些自己不太懂的书,读外国的书,理论的书,甚至还读过康德,读过天文学。天文学对我影响大,改变了我的时空观,甚至还想过要考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也不太懂,但高中生的我就有意找来读。这是什么心理? 是一种“喜欢读书”的象征吧,一种上进的力。
新编高中语文教材,我是主张安排几种“整本书阅读”的,就安排了读《红楼梦》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说现在碎片化的阅读太甚,就让高中生完整读几本深一点的名著,磨磨性子吧。前不久我给人文版《乡土中国》写了个导读,其中也就有这么一句话:“读书不能总是读自己喜欢的、浅易的、流行的读物,在低水平圈子里打转。有意识让自己读一些深一点的书,一些可能超越自己能力的经典。”
您的一些教育理念,来自学生时代的阅读经验和当下现实生活的需求。包括您提出要读一些很深、很难懂的书,当时就有这个自觉性吗?还是有人引导您?
温儒敏:好像没有老师专门教我这样。主要是自己在大量阅读中逐渐觉悟的。语文要靠长期的读书积累,靠自己去“悟”。每个人学语文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多读多写,积累感悟,可能是共同的经验。我的幸运是碰到了几位比较好的中学语文老师,好在他们自己是喜欢读书的,是“读书种子”。这就给我熏陶,潜移默化。我至今记得去高中语文老师钟川家里,潮湿阴暗窄小的屋里全是书,书架上摆着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等文豪的作品,一摞摞堆放在简易的书架上。这让我震撼。现在语文课为何那么难教? 读书少嘛。老师也不怎么读书,那学生怎么可能爱读书,学好语文?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温儒敏谈读书》中,有一篇《我的读书生活》,特别谈到对您有影响的两点,一是读书比较杂,二是在基层待过。“文革”时您的阅读并没受影响?
温儒敏:我在大二的时候,赶上“文革”。“文革”毁灭文化,但也有“逍遥派”的缝隙。那时停课闹革命,有两年我到天安门历史博物馆参加“毛主席去安源”展览工作,闲来无事,杂览群书,古今中外文史财经抓到就读,漫羡而无所归心。那是非常时期非常难得的“私密阅读”的时光。有时借“大批判”的名义,反而接触了许多“禁书”,让我感觉到历史发展的复杂、人性的复杂和政治的复杂,变得成熟一些。
“文革”时期配合运动,组织整理了二十四史。又同步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叫白皮书、黄皮书,供“大批判”用的,封面上印着“内部发行”,县团级以上才可以看,但发行量大,想想办法也总能找到。我读过而且印象很深的有《多雪的冬天》《带星星的火车票》《州委书记》《麦田守望者》《解冻》《人·岁月·生活》《第三帝国的灭亡》,以及《论语》《左传》《史记》《世说新语》《红楼梦》《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马恩选集》等等。在那个压抑的非常时期读书,会激起许多思考,有时是随波逐流的,有时是叛逆的,私密的。这都无形中进行一种思维训练吧,虽然不是很自觉的。比如读《麦田守望者》,译本前言说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青年生活的堕落,成为“垮掉的一代”,而我阅读时对书中这些青春期男孩的堕落、迷茫、上进,也能产生共鸣。前些年我曾编过一种小学教师阅读选本,就选了《麦田守望者》。老师应该了解青春期少年的苦恼,这本书美国几乎所有大学生都会读的。
您的导师是王瑶先生,他对您在读书方面有怎样的要求? 您又会对学生有怎样的要求?
温儒敏:王瑶先生是很放手的。他要求我们读书,熟悉基本作品和史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有大致的了解,但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大部分作家的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我们把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注释中列举的作品当作书目抄下来,一本一本地看。那时候研究生享受老师的待遇,可以直接进入图书馆库,一借就是几十本。研究生阶段我的读书量很大,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但也就感受了文学史氛围。书读得多了,旧期刊翻阅多了,历史感和分寸感就逐步形成了。
几十年与书为伴,反复读的书有哪些?
温儒敏:鲁迅的书读得最多,这跟我从事文学史研究有关。一百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有最深入理解的,鲁迅是第一人。鲁迅的眼光很“毒”,他是要重新发现“中国与中国人”。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论著很多,但鲁迅作品很特别,是别人不可替代的。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不是书斋里隔岸观火的学问,而是痛切的感受,是从生命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这和读一些学问家的概论和历史著作之类,是不一样的,功能和感觉都不一样。
最近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两种鲁迅的书,一是《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选了鲁迅79篇作品,每篇都有千把字的讲析,颇费了功夫。另一种是《鲁迅精选两卷集》,选了128篇作品,每篇都有题记导读。这也是我几十年学习研究鲁迅的总结吧。
如果比较私密的聚会呢,您看了那么些书,有没有想和哪位作家聊聊?
温儒敏:没有时空限制的话,想跟曹雪芹聊聊,问问《红楼梦》那些不解之谜。也想跟托尔斯泰说,我不太喜欢他作品中大量的说教,但也承认引发了许多形而上的思考,包括宗教意识,有些我是想请教他的。
鲁迅呢?
温儒敏:鲁迅恐怕很难聊天的,他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他很孤独。孤独是他创作的诱因,我不敢打搅他。
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温儒敏:到无人岛,多么艰难,如何活下去都有问题,怎么还读书? 当然,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可能也会回想《红楼梦》中那些有关色空的哲理性的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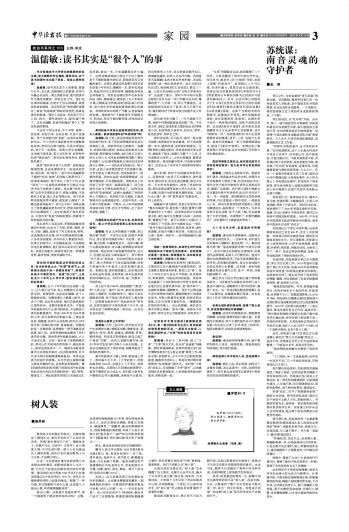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