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和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重要著作的诞生,全球史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与我国以往的世界史研究不同,全球史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叙述,而是以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作为叙事对象。全球史研究的主题多种多样,但有关商品贸易的研究无疑最能体现其特色。这是因为,全球各地区之间的关联起初主要是通过商品贸易建立起来的,全球化的历史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仲伟民教授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以下简称《茶叶与鸦片》)可谓中国学界对于国际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回应。
一、“王牌”货
仲伟民选择茶叶和鸦片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鸦片是19世纪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商品,茶叶是19世纪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商品”(《茶叶与鸦片》,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36页》)。这两种商品将19世纪的中国和英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中英两国的命运在19世纪出现天差地别式的“大分流”,茶叶与鸦片不但是贯穿始终的见证者,也是最为有力的推动者。仲伟民把茶叶与鸦片视为“成瘾性消费品”(以下简称“瘾品”),属于布罗代尔所说的“王牌”货(《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435页)。
所谓“王牌”货,是相对于粮食等大宗商品而言。布罗代尔同时代的学者指出,对于15世纪的地中海而言,在贸易方面占首要地位的不是香料和胡椒,而是小麦等“大量近距离交易”。还有学者用数据证明,“在产业革命前夕,英国对外贸易额大大低于国内贸易额”。布罗代尔认为,相对于农民和“二千万法国人”,“贵族和路易十四”等少数人往往能起“更有决定意义的作用”。香料、胡椒以及各种各样的“瘾品”就是这样的“王牌”货。粮食产量看起来庞大,但绝大部分由生产者自己消费,用于出售的粮食,“给农民、地主和转售商留下的利润十分微薄,再分散到许多人的手里,真是所剩无几”。“瘾品”等“王牌货”,则完全通过市场出售。更重要的是,这些“王牌”货的产地都不在欧洲,想要获得这些商品,必须通过“远程贸易”。在交通不便的时代,“单靠距离就足以制造超额利润”。一公斤胡椒在印度产地值1至2克白银,在威尼斯达14至18克,在欧洲各消费国则达20至30克。正是这样的“超额利润”,刺激出了15、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也催生了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超级商业组织。由于从欧洲到亚洲从事跨洋贸易,需要的资本特别巨大,不是个别商人能够承担的。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第一次航海筹集到的资金高达68373英镑,而当时英国一个熟练技工一年的收入也只有10英镑,而这笔巨款是由215名股东集资而成。(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第62页)在布罗代尔看来,远程贸易“不容置疑的优点”是它允许实行集中,从而使它成为推动资金流通和资本积累的无与伦比的动力。
与丝绸、瓷器、珠宝等“耐用品”不同,“瘾品”很快便会被消耗掉,需要再次购买。这使得瘾品的需求永无止境,瘾品贸易也永无止境。再则,瘾品的销售单位可大可小,特别是可以小到“连最穷的人都买得起”。这使得瘾品售价下跌之后,不但能够迅速吸引更多新的消费者,还能使原有的消费者加大购买量。某种程度而言,在人的身体对瘾品的需求达到饱和以前,瘾品的市场空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以英国人的茶叶消费为例。据《茶叶与鸦片》可知,英国获得茶叶的第一次记载是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荷兰人手中用4镑5先令购买了22磅12盎司的茶叶。17世纪80年代,英国开始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但一直到18世纪初期,英国人的茶叶消费都是“非常有限的”。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展示了18世纪英国茶叶“人均消费量”的增长:1700年人均0.01磅,1730年0.08磅,1760年0.2磅,1784年0.5磅。曾在非洲管理茶叶种植园的英国作家罗伊·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一书中写道:“18世纪的第一年,英国茶叶的消费量——即使加上走私茶叶——也不到10万磅;而到了该世纪的最后一年,茶叶的消费量达到了2300万磅,增长了200倍。”显然,英国人在18世纪逐渐养成了饮茶的习惯。1846年,英国输入的茶叶达到5650万磅,人均消费量达到1.7磅。英国众议院1845年的一份报告声称,“茶叶在英国的消费已经达到顶点”(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第90页)。然而,在《茶叶与鸦片》一书中可以看到,英国茶叶人均消费量在19世纪下半叶继续稳步增长:19世纪50年代人均2.24磅,60年代3.31磅,70年代4.28磅,80年代4.85磅,90年代5.58磅。这种增长趋势一直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1930年至1933年,英国年均茶叶消费量达到45214万磅,人均消费量达到9.83磅。此后,“英国人的茶叶消费数量一直维持在人均年度9磅左右”(《茶叶与鸦片》,第207页)。
二、命运交错
当中英两国跨入19世纪的大门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席卷之势,中国似乎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
英国在18世纪养成了饮茶的习惯,而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茶叶提供者。更重要的是,整个19世纪英国茶叶的人均消费量,一直都处于稳步增长中,这意味着19世纪英国茶叶的消费市场似乎是没有边界的。在仲伟民看来,“通过茶叶贸易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并融入全球化,应该说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机遇”。不仅如此,中国在19世纪之初的优势地位还体现在,英国等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而中国却不需要西方商品。出于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就采取各种手段试图建立同中国商业往来的通畅渠道”。除了1792年马噶尔尼使团访华和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之外,早在1787年,英国政府便第一次派遣使臣卡恩卡特前往中国(卡恩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未能完成任务)。英国政府给卡恩卡特的训令是,如果中国政府提出禁止鸦片买卖的要求,“你必须答应,而不要冒丧失其他重大利益的危险,来抗争这方面的自由”。这是因为,“保证茶叶供应是英国维护东方贸易的根本考虑”。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英历次冲突和交涉中,只要中方提出“停止贸易”,便可使得英方就范。
形势一片大好中,唯一的阴影大概就是鸦片。向中国输入鸦片,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茶叶贸易的需要。由于英国商品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很难找到销路,英国人最初只有通过向中国输出白银以获得茶叶。在18世纪的最初六十年里,英国输入中国的物品中只有10%是商品,其余都是金银货币。这并非英国特例,而是19世纪以前将近三百年的中西贸易的惯常,有学者称之为:“早期中西方的贸易史,主要是一种单向贸易史。”即商品单方面流向西方,中国需要的只有白银。为解决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回程茶叶所需资金的问题,英国人在印度种植鸦片并向中国输入。结果鸦片贸易在19世纪上半叶的惊人发展,彻底打破了中英之间的“贸易平衡”。1800年到1804年,走私到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3562箱,1815年到1819年平均每年4420箱,1820年到1824年平均每年7889箱,1825年到1829年平均每年12576箱,1830年到1834年平均每年20331箱,1835年到1838年平均每年35445箱。(《茶叶与鸦片》,第129页)短短三四十年,鸦片贸易的走私数量增长了近10倍。尤其是1820年后,几乎每隔五年,鸦片走私的数量就会增长近一倍。与之相应,中国在1820年代由白银净进口国变为净出口国,结束了长达近三个世纪的贸易出超的历史。在仲伟民看来,“1820年代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预示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总危机即将到来”。
仲伟民认为,茶叶贸易的演变历程,同样折射了19世纪中国面临的危机。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茶叶出口一度增长迅猛,“以1870—1874年5年平均计算,出口茶叶达176万担,价值3515.3万海关两,出口量是鸦片战争前的4倍”。1876年后,中国茶叶出口开始出现量增价减的现象:1876年出口茶叶194万担,价值3664.7万海关两;1878年出口195万担,价值3201.3万海关两;1888年,中国茶叶出口数量达到241万担的高峰,但仅值3029.3万海关两。量增价减的背后是中国茶叶出口遭遇到了严重的市场竞争。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印度红茶在英国、日本绿茶在美国都已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被挤压。以英国市场为例。1866年,中国茶叶占有96%的市场份额,印度占4%;1885年,中国占61%,印度占37%,锡兰占2%;1887年,中国占47%,印度占47%,锡兰占6%;1903年,中国占10%,印度占60%,锡兰占30%。(《茶叶与鸦片》,第66—81页)仲伟民指出,“茶叶作为19世纪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商品,最后却节节败退,充分显示出国家竞争力的衰退”。
在茶叶“商战”全面败退的同时,中国的鸦片“商战”却取得了胜利。鸦片战争后,鸦片进口同茶叶出口一样迅猛增长,1845年到1849年中国年均进口鸦片39000箱,1855年到1859年为年均68500箱。为阻止白银外流,中国开始鸦片的“生产替代”。1860年代以后,中国鸦片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全国有大批良田改种鸦片,据称四川有三分之二、云南有三分之一的耕地改种鸦片,全国因种植鸦片而被侵占的耕地达1300万亩,占到了全国耕地的7.5%。国产鸦片对进口鸦片的替代效应在186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1867年鸦片进口值达2230.4万两,而1868年仅为1853.7万两,下降了近17%。到1879年,全国鸦片的自给率达到80.12%。(《茶叶与鸦片》,第139—156页)1882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许士在贸易报告中声称,“外国鸦片不仅在华西和西南地区,而且在沿海地区也正在逐渐地让位于中国鸦片”,“中国鸦片终将把外国鸦片赶出中国,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仲伟民表示,“这可能是中国在19世纪的无数次商战中,唯一一次取得胜利的商战”,但这不过是“在用慢性自杀的方式来取得这场商战的胜利,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更为重要的是,茶叶之于英国,鸦片之于中国,分别对两国社会起到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糖与权力》的作者西敏司曾指出,糖、可可、咖啡和茶叶等“瘾品”,都有刺激性,“极适于纪律日益严格的枯燥乏味的日常工作”,其消费量的增加,“势必促使人们工作得更多、更紧张”,因而对近代欧洲的“勤勉革命”起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表明,茶叶在促进英国的“勤勉革命”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突出地表现为改善了英国人的膳食结构。19世纪后期,英国劳动阶层一般要花费其食物总开支的10%用于茶叶和糖的消费,“茶叶以及面包和奶酪构成日常饮食的核心部分”。英国学者麦克法兰指出,茶和糖的美妙结合,使千百万穷苦人在从事沉重且单调乏味的工作中能保持较为充沛的精力,“如果没有茶叶,大英帝国和英国工业化就不会出现”。而在中国,弛禁鸦片并大规模种植,使得19世纪吸食鸦片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据仲伟民估算,19世纪后期中国的鸦片吸食人数大约在200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4%—5%,其中吸食上瘾者估计有300万至500万人。(《茶叶与鸦片》,第213页)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到边远贫困地区,到处都有吸食鸦片者。这些鸦片吸食者,不分男女老幼,也不论贫富贵贱,在很多普通家庭,烟具都是必备物品。鸦片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健康,使得中国人成为世人眼中的“东亚病夫”。
三、国家力量
《茶叶与鸦片》一书认为,中国近代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茶叶生产和管理方式的落后。中国是家庭副业的小农生产模式,而印度是大规模的种植园生产模式。在中国,茶树一般种植于山坡、屋旁、田边等“畸零之土地”。茶叶采摘基本依靠家庭成员,采摘时间参差不齐,叶子老嫩齐采,不分等级。茶叶后期加工主要依赖手工,不仅浪费人力、效率低下,而且品质没有保障。在印度,英国人将茶叶种植园选在土地肥沃的大河冲击地带,对茶叶生产的各道工序进行科学实验,不断改良茶种。对茶叶采摘的时间和等级进行严格管控,如阿萨姆茶园规定采茶工清晨入园,采至11点钟止,每人只采同一等级的茶叶;每次采摘后,须经两周才能再采,这样每年可以采摘16轮。茶叶后期加工很快就实现了机械化,不仅速度快、成本大大降低,而且茶叶质量大大提高。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几乎每一磅印度茶都是上品,其制造方法在质和量方面年年都有改进”。两相对比,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命运可想而知。当时便有人指出,“印度对中国的优势,就是制造商(工业家)对手工业者的优势”,“控制着伦敦市场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而在湖北山边有着两三亩地的小农,是不能希望和它们竞争的”。
无疑,这个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然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何印度可以采取大规模的种植园生产模式? 具有典范意义的种植园模式,是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强占了大量土地后创造出来的,他们在大片土地上种植单一经济作物,如甘蔗、咖啡、棉花等,劳动力则是来自于非洲的黑人奴隶。印度的茶叶种植园,是美洲种植园经济的升级版。麦克法兰指出,茶叶种植园的经营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英国政府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因为它是阿萨姆邦的“所有者”,有权将土地授予任何想要的人。当然,能够拿到土地的几乎都是欧洲人。英国政府之下是茶叶公司,这些茶叶公司像东印度公司一样,由众多商人集股而成,如成立于1839年的阿萨姆公司首期入股资金达12.5万英镑。184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将三分之二的试点茶园移交给阿萨姆公司,租期十年,租金为零。茶叶公司招聘一些欧洲年轻人前往茶园担任经理,领取固定薪水,并从茶园发出的每一批茶叶中收取佣金。金字塔的最底层是成千上万的“苦力”,由专业的“招工机构”在印度各地市场购买而来。在茶园经理眼中,“苦力是会干活的动物,没有选择权,没有个人需求”(《绿色黄金:茶叶帝国》,第176—199页)。不难发现,英国人打造出来的茶叶种植园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对印度土地、劳动力的无偿掠夺上。
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一书中指出,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商人在英国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就已经重组了全球棉花产业和全球棉花网络。这些网络由私人资本和国家共同主宰,“它们联合在一起,创造了武装贸易、工业间谍、禁令、限制性贸易条例,它们还掌控领土、捕获劳动力、驱逐原住民”。国家通过自己的力量创造新领地,交给远方的资本家掌控,建立起一个新经济秩序。(《棉花帝国》,第54页)在重组全球茶叶产业链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英国国家力量无处不在的身影。1834年,印度总督威廉·班庭克成立了一个在威廉·乌克斯看来“富有历史意义”的茶业委员会,其动机是“鉴于茶叶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除了中国政府许诺对于茶的供给有相当的保证之外,应该建立更为妥善的保障”。茶业委员会一方面发布通告,寻找适合茶树生长的印度土地;一方面派人前往中国学习茶的栽培技术和制造方法,同时采购茶籽、茶树和雇佣中国熟练茶工。在此之前,英国人布鲁斯兄弟已经在阿萨姆发现了野生茶树,但并未受到重视。茶业委员会高度肯定了这一发现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认为这将是帝国在农业和商业资源方面的最重要且最有价值的发现,将来必定能使帝国在商业上获得丰厚的回报。”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阿萨姆茶业的起步。1838年,第一批阿萨姆茶共8箱被运到伦敦,轰动一时。1840年,第二批阿萨姆茶叶共95箱在伦敦公开拍卖。威廉·乌克斯表示,“1840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因为从这年起中国茶在英国的销路开始衰退”(《茶叶全书》,第153—171页)。可以说,正是在英国政府的精心培育和鼎力支持下,印度茶才会在19世纪迅速崛起,并取代中国茶,成为英国茶叶消费的最大提供者。
与此同时,清政府对茶叶这个19世纪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却看不到任何长期规划和相应扶持。由于19世纪国际茶叶市场需求不断增加,而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都是茶叶的唯一提供者,这刺激了中国茶农积极扩大茶树种植,“1840年后的30年间,茶叶产量增加4倍之多”。然而1870年代以后,中国茶叶遭到印度、日本茶叶的激烈竞争,出口量大减。已经扩大生产的中国茶农,若不毁弃茶园,忍受更大的损失,便只有降价求售的唯一出路。有学者因而指出,华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实际上,清政府也不可能对中国的茶叶产业进行长期规划,因为它对全球茶叶的生产和消费状况几乎一无所知。反观英国,鸦片战争后英国在条约口岸设立的领事馆,每年都会向英国政府提交年度贸易报告,汇报有关茶叶和鸦片等进出口贸易的商业信息,便于英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维护英国商业利益。诸如此类的制度设计,使得英国政府成为英国商人在19世纪经济全球化中不断开疆拓土的有力后盾。
清政府不仅无法为中国茶业发展提供助力,反而成为中国茶业发展的阻力。为保护民族产业,各国政府的惯例是,少征本国货物的出口税,多征外国货物的进口税。然而19世纪的中国恰恰相反,出口税一直比进口税高,有的年份甚至高出一倍以上,如1885年进口平均税率为5.75%,而出口平均税率为12.15%。甚至,清政府在列强的威逼利诱下,反而给予洋货诸多优惠,如“洋货运入内地,不分华商、洋商,均可请领半税单”。洋货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打开中国市场,与洋货税率不断下降,流通成本不断降低,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清政府地方官员对经过他们所辖地区的茶叶“强征任意的和税目不定的税款”,使得茶叶成本提高,“有的地方达到茶叶原始成本的50%”。1896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韩能表示:“中国的茶叶贸易一直在逐渐衰落,那些最熟悉茶叶贸易的人们认为,茶叶所缴纳的出口税和厘金税之重,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原因之一。”基于此,仲伟民认为,“传统的小农经济固然是19世纪后期中国茶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但清政府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也有极大关系”。
在鸦片贸易中,我们也能看到中英两国政府截然不同的表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英国人在印度生产鸦片的目的非常明确,“即全部销往中国以弥补贸易逆差”。英国人深知鸦片的危害,因而不仅限制英国人的鸦片消费,也明令禁止印度民众吸食鸦片。第一任印度总督黑斯廷斯认为,鸦片是一种特殊商品,不适用 自由贸易原则,必须采取垄断经营。因此,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建立了一套鸦片垄断经营制度:农民种植鸦片必须经过政府的许可,政府将资金预付给种植鸦片的农民,农民在收获鸦片后必须根据政府指定的价格卖给政府的代理机构。农民私自种植鸦片是违法的,将鸦片卖给私商也是违法的,而私商也不能随意收购鸦片,违反者要处以重罚。这套管理严密的鸦片垄断经营制度,使得印度虽然生产了大量鸦片,但并没有对印度社会产生重大危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鸦片生产和销售。在鸦片种植上,清政府任民自为,不仅使得许多农民也开始吸食鸦片,还占用了大量耕地,使得粮食产量受到很大影响,经常造成饥荒。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丁戊奇荒,造成了上千万人的死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在鸦片销售环节,清政府除了征收高额厘金外,也是一切放任不管。由于鸦片贸易是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单靠个人力量很难完成,而必须依靠群体力量和广泛的关系网。因此,近代中国的鸦片贸易往往控制在军阀、地方实力派人物、秘密会党和黑社会手中。因鸦片贸易滋生的许多地方黑恶势力,使得19世纪的中国社会更加混乱。直至20世纪,鸦片仍是各种反政府势力和恶势力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回到19世纪三十年代,那时的清政府曾经针对鸦片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问题进行过一场政策大辩论。许乃济提出,“以货易货的鸦片贸易应当合法化”,一方面可以阻止白银外流,同时可以增加税收。包括林则徐在内的绝大多数官员都认为,这一做法是明显的错误和不负责任,为了阻止白银外流,鸦片贸易必须禁止。最终,清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禁烟措施,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了两万箱鸦片。虎门销烟是被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为了应对19世纪的危机而作出的一次非常正确的自救之举。遗憾的是,英国政府在英国商人团体的请愿下,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这次战争是中英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清政府的不堪一击事实上预示了19世纪中国的悲剧命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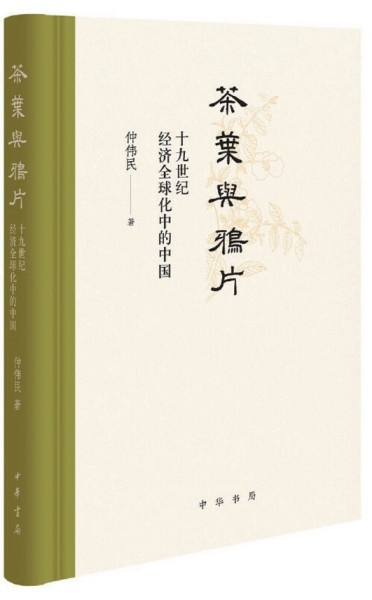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