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山东的简默,是几年前在燕山深处的一个小山庄——中国作协的上庄创作之家,和江西的散文家王晓莉一起有次短暂的聊天,聊天的情景犹在昨日——窗外是格桑花、山楂树和玉米田,聊的话题都已随风飘散。近日读到简默的散文集《时间在表盘之外》,觉得才真正开始认识简默。
简默在黔南都匀出生,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简默在创作谈里写道:“父亲医专毕业,怀揣着热血沸腾的理想,自济南乘上一列绿皮火车,历经数天数夜的辗转与颠簸,来到黔南山城都匀一个叫东方机床厂的工厂,开始了他的三线建设岁月。那时他想象不到,在长途跋涉之后的随遇而安将会给他未来的生活埋下怎样的伏笔,又将如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他以及我们这个家庭命运的走向。”童年的简默,每天走在通往大自然的路上,稻田、蜻蜓、苜蓿、映山红……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书写,应该是从这里开始孕育。14岁后,他随父母回到山东故乡。
简默这本书,是以个人的成长史、心灵记忆为切入点,写出了一个人的时代记忆,使我们在大时代的潮流中,看到了被岁月所淹没的个体生命的悲欣交集。全书分三个部分:“人间”“风物”“远方”。这三部分构成了一部回旋曲,在互文和旁证中,扩展和深化着爱与乡愁的主题。“人间”主要写生活记忆,尤其是举家北迁与父亲的早逝;“风物”写心影中的各种动植物,但都牵出了与人世相关的万般情感;“远方”写青藏高原上的所见,看似偶然,实则是命运伏笔的续写。
简默在“人间”部分里写道,日夜被乡愁缠绕的父亲,为举家北迁精心筹划和准备了十几年,生在贵州长在贵州的母亲,经过漫长的犹疑与动摇之后,被父亲说服,洒泪挥别父母兄弟姊妹们,追随父亲来到陌生的北方:“一列从夏天开出的绿皮火车,载着父亲、母亲、我和弟弟从都匀站出发,哐当哐当,一路逶迤起伏,穿桥钻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江苏时缓时快地踮着脚向后退去……地势渐低渐平,视野日渐开阔……整整三天四夜,火车最后在黑夜戛然刹车,在郭城吐出疲惫的我们。我们举目无亲,像一个个等待被认领的包裹。”
父亲确是回到了故土,从黔南到鲁南,“许多东西被默默地改变了,唯一不变的是父亲的职业,他挑头组建了卫生室……”多年后作者回想起坐在临街简陋的卫生室里的父亲,感到他的内心一定有所不甘,“他人生的半径越来越短,作为一个胸怀救死扶伤抱负的医生,他或许会沮丧与失落。在这个地方,他与千篇一律的头痛、感冒、腹泻频繁地打着交道……我们家不分时候地成为卫生室的延伸与补充,这让我们不胜其烦,父亲却处之泰然。直到他走后许多年,不少人见到我都会问,你是王大夫的儿子吧?”作为儿子,当年简默曾感到父亲生活的“平淡与呆板”,但是多年后,他意识到父亲“才是一棵树,他有自己的生长空间与叙事方式”。
回到故土的父亲,六年后却患了绝症,那时父亲正当中年,“我”正青年。父亲“像被上帝脱手扔出的一粒色子,画出一条仓促无奈的抛物线,身不由己地向下坠落,坠落,直到与尘埃一起落定”。“看得出,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与慌乱,这来源于他对疾病的熟稔和对健康的迷恋”,他努力配合手术,但还是“一点一点地脱离与人间的联系,一步一步地走向天堂”。《医院》里的父亲,或者说父亲作为医生的一生,读来催人泪下。
父亲刚走的那几年,母亲一下子适应不了生活的巨大留白,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里,夜里不开灯,也不说话,“但她唯一牢记的是在过年前后那几天,将门口的灯换成一盏红灯。它凝聚着火红的内心,在滴水成冰的寒夜,从里向外散射着热烈与温暖……对此母亲的解释是,父亲一直盼望过上红火的日子,我们请他回家和我们一起过年……红红火火的灯光照着他回家,又照着他回另一个家。”命运的伏笔就这样展开。可以说,简默笔下真实鲜活的个人生活史,是时代的标本,也是镜像,能够照出一代人的生活和情感。
作者在对父亲的追忆和生命反思里,了悟了生死,深深体验了阴阳两隔、灵魂孤苦,他从痛感和孤独感里泅渡出来,站在“向死而生”的生命立场上,去生活和写作。如他写:就在父亲离世的那家医院,那间病房,那张床上,朋友的孩子出生,“生覆盖和替代了死……至此,死和故人的气息荡然无存……”在悲欣交集的人生中,简默能翻过死的阴霾这一页,让我们看见新生命“像烛光一瞬间照耀得满室光明”。他还写到乡间送葬和迎亲的队伍狭路相逢时,总是送葬的主动让位,让喜气洋洋的队伍先行通过。
过早地体验了亲人飘零的简默,分外懂得珍惜人间的爱,懂得珍惜世间的一切生命,从人到自然界中的任何一个弱小生灵。如《薄如大地》里,躲避汽车轮子过马路的残疾小刺猬;《三脚的猫》里,趔趔趄趄走路的三脚猫保护幼崽;《蜻蜓记》里各种背景下飞翔着的蜻蜓;《在札达士林,与一条蜥蜴对视》里,“我蹲下身子,匍匐在地”,“读出了它眼中汹涌如海的神性与佛性,也捕捉到了它气吞山河的孤独”。简默在写万物时,仿佛也是在写自己充满怜爱、悲悯和孤独的心,写父辈命运里延续的感情脉络,哪怕在青藏高原上,他也看到了湟鱼们溯河洄游的乡愁,和一条蜥蜴旷世的孤独。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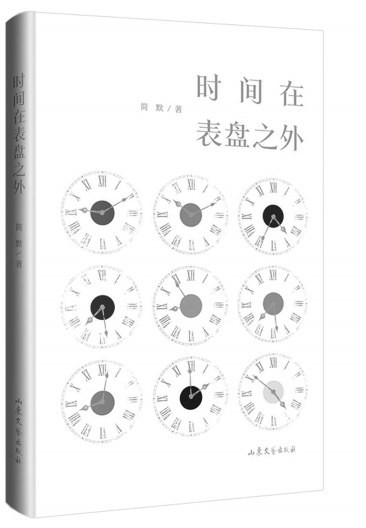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