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有关那个德文词翻译理解上的分歧是小事,重要的是,在有关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的方式上,我们始终是同道!以这种思路对马克思思想重新展开梳理、阐释和评论,确实矫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误读和曲解,也有助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现实价值。
时光在忙乱中不停地流逝和循环,转眼间又到开学季了。因我平时除上课外很少去学校,所以掌握的信息不太灵通和及时。那天进入学校网络管理系统查看课程情况,顺便浏览了一下“公告”,看到外国语学院2022年2月9日发的讣告,才知道金海民老师于2月1日去世了。想起20多年前与他参与创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的事及前后的交往,心有所感,特写篇短文寄托对他的怀念之情。
在目前的学科归属上,金老师被划在德国语言文学专业,但我想指出的是,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随着新世纪以来文本、文献研究方式的兴起,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经典作品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在这部翻译成中文将近700页的著述中,有400余页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重要成员麦克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评论,而金老师恰是后者的中文译者。所以,他的译著也成为近年来国内众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论文和著作重要的参考和引证文献。我个人认为,这是金老师对国内学术界最大的贡献。
我是1998年8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调入北大哲学系工作的。此后不久,教育部启动了新一轮全国重点学科评选。虽然北大马哲照旧入选,但那次排名比较靠后。这一学科当时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由于老教师集中退休,在职队伍严重萎缩。二是科研成果虽然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方向,但缺少聚焦点,特色不明显。对于前一个问题,系里从引进我开始着手解决,以后几年又陆续引进三位青年学者,使情况有所改观。针对第二个问题,系领导当时组织系内外专家开了好几次会,重点讨论究竟什么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统。最后大家形成基本共识:思想史(哲学史)和文献研究是我们区别于国内其他哲学系和研究机构最重要的特色和长处,而这也是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秉持的是与西方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同样的方式和思路,黄枬森等教授筚路蓝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这一领域和方向,确立了北大马哲在全国独特的地位和优势;黄老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展开的对列宁《哲学笔记》等著述的研究,从今天的角度看,就是典型的“文本、文献学研究”。这样,在几次讨论所形成的共识的基础上,由我起草了系里给学校的报告,提议成立校级研究机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
要成立“文献研究中心”,首先得搜集多个语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始文献及其研究资料。哲学系当时在静园四院办公,系领导特别指示腾出两个房间,供我们存放这些资料。我是教研室年龄最小的,琐碎的事自然就由我承担了。系领导还特别邀请德语系金海民老师过来帮助我们。这时我才了解到,金老师是“德语”和“哲学”两个领域的跨界学者。他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国语言文学专业,196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在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西语系、外国语学院等单位工作。金老师最特殊的经历是,他是国内最早到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从事学术研究并攻读博士学位的人,1983年3月至1987年9月他在那里的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工作、在特里尔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深造,最终获博士学位。此后,金老师还于1998年3月至1999年1月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
金老师帮助我们与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取得联系,那里先赠送了我们一套现在仍有利用价值的“马克思故居文献研究丛书”(50册),后来又陆续寄来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当时我们特别想得到的是一套最权威、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考证版”。位于北京西单灵境胡同西斜街的中央编译局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我自己去过很多次,还和金老师一起去过一次。编译局图书馆的老师带着我查看了他们那里的全部藏书和资料,我们协商好具体方案:如果那里的资料有两套或多套,就赠送或者卖给我们一套;如果只有一套,就由我们出钱,由他们帮助我们复印并装帧一套。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文献中心的资料有了一定的规模。当时是2000年,编译局之外,我们在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是国内高校中最齐全的。
除搜集资料之外,我们对以后的研究工作也做出了规划。为此,我们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谈好,准备出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丛书”,拟定了以后若干年推出的成果名单。金老师将其酝酿多年的研究项目《马克思与〈莱茵报〉》列入其中,我申报的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解读。
文献中心于当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之日正式成立。中宣部、教育部、中央编译局、艾尔伯特基金会和北大校、系领导,以及一些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与会并发表了讲话。金海民老师特别在会上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保存和研究情况。随后按照规划又于当年10月、次年9月以“《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为主题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金老师特别邀请了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的赫尔穆特·艾斯纳尔教授(Helmut Elsner)访问北京大学并出席了前一个研讨会。国内期刊和报纸对这些活动做了报道或者发表了综述,引起学界反响,可以说呈“一时之盛”。
我还与《哲学动态》取得联系,策划了一个“学术沙龙”栏目,由该刊记者提问,金老师、马哲教研室另一位老师和我来作答,以《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意义与方法——马克思文本研究三人谈》为题于2003年第4期刊出。这篇对谈是由我起草的,成稿后送两位老师审阅,他们表示同意后就发出了。我现在的电脑中已经没有这个文档,后来特意从“中国知网”下载后认真通读了一遍,当时代两位老师写作涉及他们的部分时话语的表达、观点的拿捏的情形还能回忆起来。这是我们之间相互理解、合作最为融洽的时期。
此后,金老师回德语系教书,我则固守文献中心,埋头于清理、消化搜集到的资料。起初金老师还偶尔过来坐坐,知其准备研究《莱茵报》《新莱茵报》,我把好不容易搜集到的一大本原始复制件,让他带回去参考,此后这套资料就一直留在他家里。2005年金老师退休了,很少来学校,也就没有再来过文献中心。
我在2005年推出《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和方法》一书后,就转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点研究。我决心摆脱传统的研究路数和方式,撇开先入为主的框架预设和思想定位,真正将其作为一个文本个案来研究。这其中对《圣麦克斯》部分的解读花费的时间是最长的。在研究中我特别注意不再仅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概括和论述去把握、理解批判对象,而是首先弄清楚后者的真实情况和思想,再比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选择和批判,看各自在意旨、思路、角度和论证等方面的差别,进而凸现出他们思想的特征及其意义。这样就需要先认真研读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老师的译本也就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是,随着研究和思考的深入,我感到困惑和问题越来越多,尽管我的德语并不好,但认为只靠阅读中译本已经很难梳理清楚进而想得透彻了。于是,我硬着头皮钻研,在解读《我的权力》部分时专门写了一节《内涵复杂的Recht的中译问题》,对照金老师译本、中央编译局译本和施蒂纳的原文对这个词究竟该如何翻译做了辨析。
我注意到,在通常的翻译实践中,有一个惯例,就是在原文中反复出现的同一个词汇,一般就选择另一语种中一个含义接近的词来翻译,而且始终采用这种译法,以体现一致性。然而,在具体的思想研究中又会发现,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不像自然科学著作那样,能够做到在不同语种之间实现词汇含义的一一对应的转换,原文中的同一词汇实际上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这样我们就需要根据不同的语境来揣摩其具体含义。
以Recht来说,翻译成中文至少有如下几种含义:(1)认为……对;(2)正确的;(3)权利;(4)权力;(5)法;(6)公道、公正。在中文中,这几种意思当然不能说没有联系,但其含义和使用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说来,金老师译本和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的译文都有讨论的空间,前者基本上都将其译为“权利”了,而后者虽然在注释中标明“一般译为‘法’,在……(个别)场合译为‘权利’、‘对’、‘有权’等等,在‘法’和‘权利’这两种含义混淆不清的组合,则译为‘法(权利)’或‘权利(法)”,但实际上又没有从思想主旨出发具体辨析其含义,因而造成了很多混淆。为此,我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四种解决方案:其一,《我的权力》第一部分的标题应译为“权利”;其二,学术用语与日常生活中的理解应该区分开;其三,出乎“我”本身的应该译为“权利”;其四,由“我”外化出来的应该译为“法”;其五,既关乎“我”又关乎“人”的(即“自在自为”的)应译为“权利(法)”。我的结论是:“上述情形表明,对诸如Recht这样的词汇的翻译,宜特别慎重,既不能只用一种译法来搪塞或替代其他复杂的含义,也不能把不相同的多种含义硬给混淆甚至颠倒了。”我将包括这一节在内的部分写成了单独的论文。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就此文的分析与金老师沟通,就把论文直接发给《现代哲学》编辑部了。我现在想不起是否有过与他沟通的想法,也可能想过,但鉴于存在一些客观情况放弃了,诸如金老师退休后很少来学校、他那时写作不用电脑(还是传统的自己先用笔写在草稿纸上,然后再去找打字工录入,我在心理系的复印店就遇到过他两次)和很少接收电子邮件等,这样我感到沟通起来可能比较费劲,所以就偷懒了。但不管怎样,我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发表此文是不妥的。
此文刊出后,据说在南方一个市级图书馆工作的金老师的妹妹看到了,就告诉了他。金老师看后不同意我的“方案”,特别是文中“对第一句话的翻译使含义不知所云”“意思不明确”“只用一种译法来搪塞或替代其他复杂的含义”等语,引发了他的愤怒。但他没有与我联系,而是告诉了我们教研室一位老教师。这位老师随即就跟我说了,我意识到自己的“失礼”,马上给金老师打去电话。电话中金老师余怒未消,不怎么听我解释,只说:“你把我逼到墙角了,我不得不回应!”我提出去他家看看,以便进一步做出说明和分析,他拒绝了。
后来,金老师写了《也谈德文词das Recht的中译——与聂锦芳先生商榷》一文。因我在《现代哲学》刊出的论文有两万余字、分为五节内容,而对Recht翻译的讨论只是其中一节,而金老师这篇商榷文章很短,所以没有对等在这个杂志上刊出,而是登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我认真看了金老师的评判,也请教了几位研究西方哲学的老师,感到我自己的理解还是有道理的。所以,在2012年出版《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时,我没有做修改就把论文原封不动地纳入了。此后,这事也就归于沉寂了。
后来我注意到,金老师退休后写了一系列短文,通过对欧洲各国语言中的俗语、谚语、特定词汇用法及其典故、来历的考证,讲解人文风情及社会变迁,透视欧洲历史文化。这些文章先是刊发在众多报纸、杂志上,受到读者欢迎,我也很爱看,后来结集为《欧洲的月份》,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金老师写作时特别注重细节,提供的有些史料很少见,比如,关于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情况,我在自己的书中还引用过。这也让我们再次感到,我们之间在兴趣点、研究方式上还是很一致的。
2015年我受邀去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和特里尔大学访学,考虑到那里是金老师的故地,我行前特别给他打了电话。但金老师态度依然比较冷淡,只应付说“挺好的”;我问他对当年与他交往过的人有没有需要转达的,或者希望我给他带些什么东西回来,他连说“没有”。因气氛不太融洽,整个通话时间比较短。我去特里尔后发现,艾尔伯特基金会已经将故居研究中心解散,由于距离金老师在那里的时间过去比较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已经不知道金老师,而与他熟悉的艾斯纳尔教授在退休后就搬到另外一个比较远的城市养老了,我也没有见着。
这之后,我们之间没有再联系过、再见过面。
现在金老师去世了,我想对他说,我们之间有关那个德文词翻译理解上的分歧是小事,重要的是,在有关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的方式上,我们始终是同道! 以这种思路对马克思思想重新展开梳理、阐释和评论,确实矫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误读和曲解,也有助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现实价值。20年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以前一同策划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丛书”计划没有执行下去。但我还是坚守这一领域和方向,特别是在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主编出版了12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如今金老师离开了他读书、工作和生活60多年的地方,我们这些人还得在此继续劳作下去。所幸的是,国内一批受过更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具有国际眼光和前沿意识、更为年轻的学人自愿加入这一行列,我也积极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在去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分会”,旨在团结更多的同行、同道,以更好的成果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告慰包括金老师在内的先驱的在天之灵。
金海民老师安息!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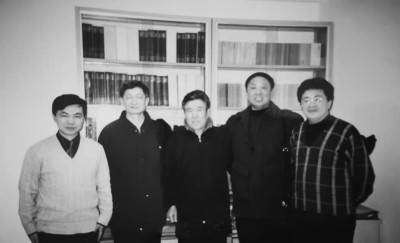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