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书中表达,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文化族群,叫“茶人”,他们爱喝茶,更爱茶的精神。茶道的核心,正是茶圣陆羽给我们写下的“精行俭德”。
时隔二十多年,继“茶人三部曲”之后,王旭烽推出了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望江南》,在翻天覆地的大时代中,写出了江南烟雨浸润中的中国人的选择和敞开、融入和奋进;在时代的激昂与风雷声中,王旭烽写得悠远低回又荡气回肠,写出了茶香和茶性,写出了江南文化的诗意和力量,写出了中国的风度、情怀和品格。
“我去高校的十多年,一天也没放下文学,只是转移到文化随笔和纪实文学上罢了。”王旭烽觉得,高校有高校的气质,相比起作协,一个为学术性,一个为才子性。她的单位浙江农林大学虽在杭州临安区,但距离一小时,几乎是从创作的西湖时代进入了山居时代。“学校为农林,所以更为脚踏实地,山气多,水气少,我从山底下爬起,一直走向专业高坡。”
小说取名《望江南》用意颇深。王旭烽解释,一是“望江南”为一味中药,疗效和“茶”非常接近,二是来自于苏东坡的一首词《望江南·超然台作》,把茶的精髓叙述得既有层次,又有温度。用作这部长篇小说的题名,已经暗含了她对茶叶时代的立场和认知。
中华读书报:《望江南》的叙事非常从容,从吴觉农到杭氏一家三代,人物形象饱满而生动,无论是主人公杭嘉和、杭嘉平,还是次要人物如婉萝姆妈这样的底层市民,皆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在刻画人物上,您有怎样的追求?
王旭烽:我的长篇小说创作,说来有点奇怪。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曾经说过“即知即行”的格言。他是上虞人,和余姚人王阳明同属姚江流域人,主张知行合一,即知即行。我的创作也是这样,不管什么体例,从不写提纲,心里有那么模糊一团,有一个人物出来了,于是开始写,每天三千字左右,肯定有一千左右是第二天写时要作废的,而人物,故事,场景,就在这样的写作中即知即行出来了。关键在于你开始身心酝酿的那团混沌之气对不对,只要对,就跟毛线团找出线头了,你只管拉,不会错的。如果不对,那就一团乱麻,那就得重写。所以这部小说我拉过三次线头,前两次都差不多写到十万字了,感觉不对再重写,第三次感觉对了。
您说的《望江南》的叙事非常从容,这使我很欣慰。因为这二十多年来的时代风云际会,眼花缭乱,我特别担心自己的文本节奏出现问题,或者文学修养已经落伍。最后定稿时我正好生了一场重病住院,在医院静下心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松了一口气。别的我不知道,但节奏是对的,是沉住气的,茶人,就是这样的人。
中华读书报:小说时人物众多,有实有虚,有吴觉农、马寅初等历史人物,也有杭家人的百态人生,杭家人中,杭嘉平从政,杭嘉和则相反。但“杭家只管茶有没有喝到一起”,这样的说法是否有所暗指?
王旭烽:人物有实有虚,是写这类历史长河小说时我的常用手法。回过头来想,可能和我专业为历史学还是有关系,自觉与不自觉中,总会渗入历史的要素。我读大学时,先生们跟我们讲《史记》,会说其为“无韵之离骚”,又说“文史不分家”。其实在茶的历史中,许多史实都是充满文学性的,尤其是人性。在西湖边喝茶,我把它理解为“可以实现的幸福生活”,而且是终极的日常的幸福生活。所有具备这种幸福目标和体验的人们,都是一类人,我把他们称之为有“茶脉”承传的人们。
中华读书报:小说以吴觉农的出场为引子,体现了民族危亡中的士大夫形象。您如何看待吴觉农这个人物,他是否是理想的中国茶人的形象?
王旭烽:吴觉农先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他早年从事过出版业,做过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家。我工作过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就是在他九十岁生日时由他倡议建立的。在中华茶界,陆羽是古代茶圣,吴觉农是当代茶圣,代表着民国以来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曾经专门为他写过一部传记《茶者圣》。
中华读书报:小说对话较多,融入了一些杭州方言,如婉罗姆妈常说的“不搭界”“安耽歇落”“贼骨头”“哭竹猫儿”等,富有生活气息,突出了地方特色。您如何看待方言在作品中的运用?
王旭烽:我一直以为,中国书面语言虽然是以一种方言为轴心而演化的。但总体说,是从各民族的方言中诞生、建设和完善的,故西汉扬雄就专门写过《方言》书,那时出现的“采风”,就包括中央政府派往各地收集方言,集中后再进入雅言的使命。经过千百年来的锤炼,文言文已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而白话文还只有百把年的经历,故还在成长之中。我从小在杭州大院长大,一直以普通话作为生活用语,直到年青时在拱宸桥最底层的工厂工作,从工友处学到了正宗标准的杭州话语。以此为参照,逐渐了解了杭州方言集北国与吴越方言的杂交优势,比较后深感兴趣,并一直在文本中探讨这种杭州方言加入普通话语系,使之超出地域进入国语层面建设的可能。至于写作过程中的使用,我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当所用方言不须专门解释就能用书面语言传递出来,使中国人一般都能意会。比如杭州人说“海威”,带有张扬呈现有力等意思,但用“海威”,即使从前没听过此词的人也会理解。汉语白话文还在创新完善过程中,杭州话将为此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中华读书报:叶子、杭寄草、杭盼的爱情在时代背景下都有些悲剧色彩,您如何看待笔下的女性角色?
王旭烽:总体而言,东方女性在数千年传统社会中,经历的不是男女平等的生活,这是小说的文化大背景。但相对而言,两浙沿海地区,人们又有特殊地理环境的熏陶,有着走向广阔世界的更大可能性。浙江码头多,集市多,商人多,女性较内地人稍多了一点点精神生活。另外,我在小说中暗自对男性作出这样一条底线:越尊重女性的男性,越像茶人。因为古代茶的特质中,有一条十分关键:不移,移即亡。古代的茶树不能迁插,不能移,只能种子下地成长。所以订婚又叫下茶,以茶比喻爱情和婚姻的忠贞。这些女性的悲剧,带着自觉和自由,有着独立人格的魅力,温柔而有韧性,是我最欣赏的江南女性。
中华读书报:小说有一个细节,专门写到杭州的茶树花,是属于被世人遗忘的花。但杭嘉和却坚持制造品尝茶树花,茶树花有何特别的喻意? 您如何看待茶人精神?
王旭烽:我们杭州人明代的高濂写了部养生专著《尊生八笺》,专门讲了冬日茶事杭州茶花,说:“两山种茶颇蕃,仲冬花发,若月笼万树,每每入山寻茶胜处,对花默共色笑,忽生一种幽香,深可人意。且花白若剪云绡,心黄俨抱檀屑,归折数枝,插觚为供,枝梢苞萼,颗颗俱开,足可一月清玩。”我想这就是杭嘉和坚持和继承的茶脉——中国文人对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表达吧。因为在温饱之中的生活艺术化,是人性中精神层面的日常呈现,具备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永恒性。所谓茶人精神,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对和平的日常生活”的坚守和体验吧。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对于“史”的追求? 是无意识的吗?
王旭烽:年轻时我曾经有过一个秘愿,要写下一个纸上的杭州。至于杭州的民俗历史等场景,更是我希望传递的内容。杭州作为故都,中国文化符号的重要承载之地,南宋文化一百多年的遗风,至今还保留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湖光山色之中,它迷人精巧深邃悲怆喜悦,有时不免颓唐,瞬间又载欣载奔,朦胧中些许暧昧,情在将许未许之间,隔空传恨,清谷听音,刹那又电闪雷鸣,慷慨悲歌,这些人类精神的珍珠,镶嵌在历史的迷径中,尚有着显现、深挖、诠释和提升的空间。我这样生活着,也想这样书写。算起来,就文字而言,我可能是写杭州最多的人之一。因为杭州是写不尽的,她是一个整理思想的地方,创造美的天堂,容我终身表达。
中华读书报:小说讲述的是杭氏家族的故事,但它展现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传达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品格和理念。您想在《望江南》种表达什么?
王旭烽:我想在书中表达,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文化族群,叫“茶人”,他们爱喝茶,更爱茶的精神和它展现出来的茶之形态。人们往往赋予茶许多品质,但在我看来,所谓茶道,就是有关茶的人文精神和相应的规则范畴。而它的核心,正是茶圣陆羽给我们写下的“精行俭德”。我希望我每一本关于茶的书,都能够传递真善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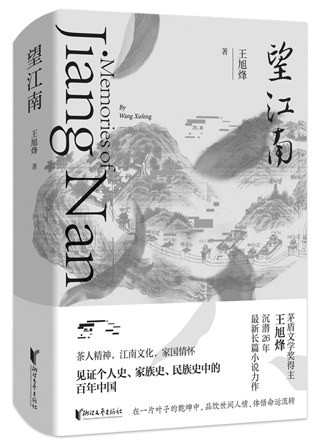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