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二十一世纪初,随着《燕行录全集》等大批燕行文献影印出版,中国学术界涌现出越来越多与燕行录相关的学术论著,新近问世的漆永祥教授三卷本《燕行录千种解题》,则可以说是这个领域一部划时代的专著,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必将带来深远的学术影响。
一、《燕行录》研究的集大成
2007年春,漆永祥教授被高丽大学中文系聘为全职教授,接触到《燕行录全集》等文献。十数年来,竟沉溺于此,先后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孜孜以求,终成此一百六十余万字的巨著。本书所收燕行文献,全而不杂,整而不乱。“综计为772名作者、1168种书目(篇卷)。”(《凡例·撰写体例与著录总数》)正编80卷为燕行录文献,而附编5卷乃中国赴朝使行记录以及其他相关或类似文献,使读者一目了然。乃迄今为止,论及燕行文献最全者,对原始燕行文献,纠谬补阙;对现当代学术论著,检验考核,可谓燕行录研究的集大成者。
2005年,邱瑞中教授“呼吁更多的人将燕行录当成研究的对象,逐渐形成一门显学,即‘燕行录学’”(邱瑞中《燕行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漆永祥教授从2007年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连续申报三个科研项目,先后在高丽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朝鲜燕行录研究”的研究生课程,这大概是全球仅见专门讲授燕行录的课程,研究为教学服务,教学又反过来推动研究的深入。
林基中、夫马进、弘华文等所编系列燕行录文献,给学术界提供了文献基础。漆永祥以此为据,参稽中韩资料,他前后翻检过的韩国历代别集与其他古籍近3000种,中国各类书籍500多种,辑佚所得《燕行录全集》等失收之零星燕行录130余种,对迄今为止能见到的燕行文献进行了精详考辨和解题。诚如作者自言:“包括《燕行录》书名卷帙、燕行过程、在馆活动、诗文内容、考误纠谬、评价影响等,为本书重中之重。凡作者出使之目的,道途所见与在馆所闻,以及诗歌、日记、游记、札记、笔谈、地图、路程记等,皆为校勘文字,考其异同,析其优劣,论其指归,长者数千言,短者不足百字,以求达‘辨章学术,考证源流’之旨。”(《凡例·〈燕行录〉解题》)既是对以往燕行录研究的纠谬、补阙、总结,又融入了作者十数年来燕行录研究的心得、教学体会。它的问世,标志着燕行录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燕行录学”的成熟。
二、中韩关系史的重要著作
本书以燕行录解题为中心,广泛论及自高丽以来,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清晰地呈现了高丽与宋、元,朝鲜王朝与明、清关系史的演变,因而是研究古代中韩关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著作。
统一新罗王朝与唐朝确立了稳定的宗藩关系,成为中朝两国随后历代王朝关系的基本模式,“使行外交”则是维系这种关系的基本方式。本书透过燕行文献的考辨,对于朝鲜半岛高丽与朝鲜两朝前往中国的使行情况,凡“燕行使出使事由、出使身份与出使时间等。使臣出使事由,有节使、别使之分(如圣节使、谢恩使),又有单使、兼使之别(如陈奏行、谢恩进贺兼冬至等三节年贡行)”(《凡例·使团概况》,第5页),清晰呈现。朝鲜使团人员有正使、副使、书状官、质正官(偶尔)、赍咨官等,每次使行人员之姓名、职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透过解题,将古代中朝关系史,综合起来考察,功莫大焉。
作者在介绍相关使臣时,将其出使次数全部呈现,十分清晰地陈述了朝鲜王朝使臣来华的情况。即如论麟坪大君李氵窅道:“朝鲜王朝数百年间,若论出使次数最多之使臣,则非麟坪大君李氵窅莫属也。”接着分析原因:“一则当时清廷,必以王亲出使,方为称意……其二,李氵窅曾为质子,与清朝皇室与重臣,多为旧识,凡出使诸事,颇便交接处置也。其三,则因孝宗护惜其弟,借燕行为其谋致富之窟也。”(第447页)“孝宗九年(1658)五月,李氵窅病逝,年尚不及四十,亦可谓鞠躬尽瘁、死于国事也。”(第449页)不仅指出李氵窅为出使最多的使臣,更进一步分析原因,其关注的问题,由燕行录解题,扩展到了整个中朝关系史的问题。一定意义上,此书可以说是一部以燕行录文献为基础的中朝关系史著作。
第895条李尚迪《癸卯燕行诗》,末论之曰:“李尚迪所交旧雨新知,或为鼎鼎中堂,或为布衣书生,或以诗文传世,或以书画傍身,要皆大江南北,一时名家,较之昔日洪大容、朴趾源、柳得恭辈所交,为多为重,乃燕行使中所绝无仅有者矣!”(第1241页)不仅对于所介绍之书,作出评价,也对其所交中土人士予以论定,从而给予整体评价。第948条李尚迪《甲子燕行诗》,乃1864年,李尚迪最后一次出使北京所写的诗。书中详考李尚迪多次入京使行情况,最后论其有他人所不及者四:“其一,李尚迪凡十三次渡鸭绿江入中土,十二次抵玉河,游北京,为燕行使家出使次数最多者……其二,……一生所职,即为燕行,返国后翌年八月即卒,而诗文亦于返国后辍绝。故若尚迪者,即因燕行而生,职尽而殁焉。其三,……李尚迪诗文,前后得到中朝友人资助……四度在北京刊行,且深受欢迎,此亦朝鲜诗家绝无仅有者也。其四,燕行使臣之入北京……亦多与中土士大夫交,然李尚迪出使前后竟三十年,所接从中朝宰相,至下第生员,祖孙父子,家属女眷,达百余人之多,亦为燕行史上所仅见……故李尚迪在燕行史上,可谓宏伟特出之第一人焉。”(第1294页)对李尚迪推崇备至,他系清代中朝关系史上的特殊人物,十二次出使,交往清人遍布中国朝廷内外,大江南北,故而书中对他进行特别的总结概括,凸显他在清代中朝关系史上的地位,这也是因书而论史评人的典型代表,体现本书的多重价值。
三、方法论上的意义
如何评判和使用燕行文献,从方法论上,本书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建议。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域外汉文文献逐步被中国学术界所重视,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葛兆光先生提出“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方法,张伯伟先生也主张要用“异域之眼”的视野,充分重视域外汉文文献的学术价值。固然十分必要,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学术影响。本书以汉文燕行文献为例,在充分肯定各种燕行文献价值的同时,也特别关注到其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书中分析其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燕行文献有相互抄袭的毛病,并将抄袭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朝鲜书籍如《高丽史》《通文馆志》《同文汇考》等书的钞录,以及对中国书籍如《大明一统志》《肇域志》《日知录》《日下旧闻考》《帝京景物略》《清会典》《清文献通考》《国朝诗别裁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与沿路各处方志如《通州志》等的抄录;一类是‘燕行录’中名著的抄袭,如金昌业《老稼斋燕行录》、洪大容《湛轩燕记》、徐浩修《热河纪游》、金景善《燕轩直指》,实际这些书也大量抄撮他人之书,后人对他们书籍的抄录就形成了两重甚至三重的抄袭现象。”本书解题时,对于抄录现象进行了大量考辨,清晰地呈现各家燕行文献的价值高低。即如第49-50条,权橃《朝天录》与任权《燕行日记》,漆永祥考辨梳理,连举数例,考明权氏日记,乃抄袭任书而成,且贪功求赏,厚诬任氏,且谓“燕行录千余家,前后抄袭不一,然如权、任二氏之雷同者,盖亦鲜矣”(第105-110页)。
漆永祥还注意到“‘燕行录’史料除了客观记述中的讹错与缺漏外,更有着严重的主观造假与改篡史实”(漆永祥《论“燕行录”创作编纂过程与史料真伪诸问题》,《历史文献研究》总第43期)。对于这个现象,夫马进、葛兆光、张伯伟等先生们,都有很多研究,发表了相关论著,值得关注。
上揭两类问题都很严重,因此漆永祥提出在利用这些史料时,“应高度重视与考辨文献资料的真伪性,寻源究委,弄清脉络,纵横交错,比观照应,既不能过度排斥,亦不可过于崇信,以为史实而笃信不疑”。如果不加考辨,不予辨析,拿来就用,那么这些所谓的“他山之石”,“不仅起不到‘攻玉’的效果,而且很可能会落入陷阱,深埋其中,变成‘他山之坑’”。这种认识无疑振聋发聩,提醒我们在大胆使用之余,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要轻信其说法,更不能为其所误。
因为“‘异域的眼光’有翳障,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与记录他们所闻所见的事物”,所以要加考辨地使用,“如果不加考证与分析地过信‘燕行录’,包括日本、越南等国人所撰的纪行录,反而放弃了 大量中国史料的运用与引证,从一隅转向另一隅,最终将历史研究引向偏离轨道的歧途与虚化的世界”。他指出,中国历史研究“本土的观察与记载,仍必须占据主导与核心的地位,否则会失去本根……本土文献与异域文献相结合,古今相较……以我为主,兼采他说,才是正确的方法”(漆永祥《“燕行录学”刍议》,《东疆学刊》2019年第3期)。这样的认知无疑更为完善,这样的方法也更加切实可行。
本书之作,揭示其抄袭,考辨其真假,即为基本态度。如对于朝鲜史籍中溢美之词,亦有冷静评断。如讲李瑈即后来之世祖入明朝之事,指出朝鲜史书“多有虚美”,《端宗实录》载其“往返辽野沿途,官民皆敬服之,宴请馈赠,诗酒不绝”,论之曰:“此等议论,事涉神怪,言多夸饰,徒为虚美,乃小说家言耳。”(第51页)直接论其不可信,体现作者有清醒头脑、客观评断。
本书还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即如在介绍每种燕行文献时,都标出其版本。朝鲜半岛古代使用 汉字为官方文字,其古代版本与 中国版本类似,在考察朝鲜版本学的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版本学的特点。书中也涉及书籍交流,有助于理解学术界多有关注的古代东亚地区的书籍“环流”现象,从而增进对东亚汉文化圈的了解。其他在文学、社会学、宗教学上,亦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恕不多言,相关方家自然能够一一体会。
可见,《燕行录千种解题》的问世,不仅标志着“燕行录学”的成熟,更是燕行录研究的检验、考察与集大成,可以说是一部划时代的学术巨著,必将对中韩关系史、韩国史、中国史、东亚汉文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学术影响。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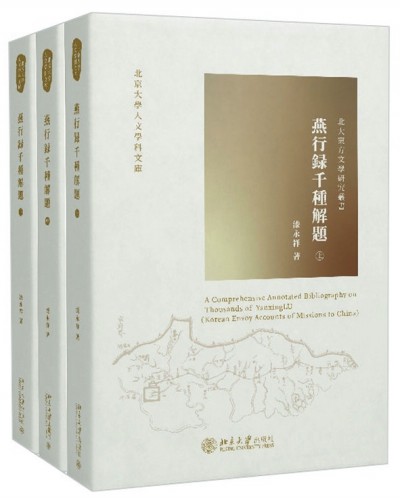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