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五年前,正是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时节,我敲开了童先生在北师大红三楼的家门。凭借报社记者的身份,本校本系学子的关系,闽西老乡的情谊,原定只是半天的采访,一篇报用人物通讯的计划,当天即确定铺陈为口述史的构想。
彼时童先生刚刚做完心脏手术,整整一个冬天都处在无人敢扰的状态。可能是我这个当年的愣头青年无知无觉无畏,也许是习惯了忙碌的童先生对“无人敢扰”的状态感到了“沙漠上似的寂寞”,总之,从白玉兰的香味弥漫整个学校,到月季花怒放在小红楼夏日的花园,每周二周五上午,我们口述的计划雷打不动地开始了。
口述史的妙处在于它是有痕的。除了头两次见面闲聊没有录音,后面的口述都有录音可循。记录显示第一次录音是2013年4月26日上午,地点在童先生家客厅,时长2小时19分,主题是童年难忘。连贯有规律的最后一次录音为2013年7月19日上午,地点在童先生家书房,时长2小时13分,主题是满门佳子弟、快友慰平生。前后集中口述历时近三个月,整二十次录音。记得2013年下半年我还来童先生家里补充录音过三次。今天大家看到的童先生口述历史,全部出自这些录音,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保真,这部书的底色,也是我的使命。
那时候的童先生的确很弱,常常前半小时还正襟危坐和我在客厅里说话,后来就疲惫地斜靠或者半躺着和我聊。童先生家客厅不大,靠着两面墙摆着两张硬皮沙发,中间一个玻璃茶几,童先生坐对面沙发,指示我也坐沙发上。有一次童先生问我为什么听着听着就不坐沙发改坐板凳了呢,我回答说坐板凳上能离童先生近一些,一来自然地想亲近一点,二来因为童先生声音有点儿微弱。童先生笑了,打后来就移师书房。果然在书房里,我和童先生都找到了自如的那种状态,他常常是半躺着和我口述的,而我的感觉也比在客厅舒服多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倾听者,但其实浅薄如我,是不配当童先生的对话者甚至倾听者的。那会儿我大部分时间忙在应付工作上,除了必不得已的功课,对童先生的了解和研究等准备工作是很欠缺的。所幸童先生极为体贴,自己做了很多准备,每次谈话之前,必定在小笔记本上写满了提纲和提示,在书桌上准备好相应的书籍,甚至已经把其中的一些签好名送给我。所以每次童先生的口述,都是极丰富而流畅,中间碰到常识性知识而我茫然无知的时候,他也从不抱怨或者小看我,而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解释,务必让我听懂听明白。后来在整理文字一遍遍听录音的时候,我才深深感到,碰到童先生这样一位负责、体贴,而且能出口成章的口述对象,对我而言是多大的荣幸。事后再回想起那时的状态,感觉就像童先生每周都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大菜,就等着这个不长心的子女回来饱餐一顿,而我真的就是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大约是2013年7月我的口述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童先生家,听到童先生接到了校宣传部的电话,大约校报副刊的“讲述”栏目,想要采访童先生,童先生很委婉地和宣传部的老师说,这里有一个他的老乡,也是《光明日报》的记者,已经开始在做并且已经快做完了,以后可以让他选取一段在校报上用。2014年初,我接到了当时的校报编辑祁雪晶老师的电话,说希望从夏天开始在校报刊登童先生口述自传,已经和童先生沟通过。于是我从给童先生的口述史初稿中先编辑了七篇,发给了童先生,请童先生审定后直接交给校报。有很长一段时间,童先生没有给我回邮件。我到童先生家问起来,童先生才和我说,因为头七篇中有三篇都是关于他的老师们的。他说关于老师们的文字,一定要准确慎重,不能像一些人的口述一样,错误很多又根本是在借老师之名自夸,这样很不合适。他又解释长久没有回复的原因是他把校报要登的内容给了他几个同学看,请他们一起给他把把关,说还真的有同学如韩兆琦就给他提出来,说关于启功给他们所上课程的名称记错了等等。
童先生对于校报刊登的这几篇文章很看重,自己编辑修改,费了不少功夫,我想也是有探探路听听反应的意思。我前后选编了十四篇,每篇两千余字。记得前几篇是祁雪晶老师负责,很快雪晶老师怀孕生产,后面就由张蔚老师接手。我记得童先生对他的修改颇为得意,有一次很高兴地和我说,我给他编的头七篇里,他给两篇改了标题。第二篇原题叫《坎坷的初中》,平淡很没有内涵,他给改成《祖母四个银元的故事》,这样就形象生动起来,人家就爱读了。第三篇原来叫《在龙岩读师范》,他给改成《在龙岩师范学校读书时》,他饶有心得似地和我说,别看这两者好像内容差不多,但是改成“在……时”,就有味道很多,我还记得他笑眯眯地和我重复一遍给张蔚老师改的这个标题,把那个“时”字拖得韵味悠长。
后来我曾逐句比对过我发给他的初稿和他修改过的见报稿件,发现童先生的确是进行了精心的再编辑和再创造,尤其是头七篇。再编辑的情况如原句是口述实录“到了开学那一天,清晨,很早,我一个人走了”,过了童先生的妙手,就成了“到了开学前一天,一个阴晦的清晨,天很早,我一个人担着行李走了”。再创造的情况,比如第二篇校报口述的第一句,我给童先生的口述实录原句是“穿着父亲给我的新衣服,我就高高兴兴地上了初中”。童先生在修改的时候,在这句之后即兴提笔加上几句,变成“穿着父亲给我的新衣服,我就高高兴兴地上了初中。一个孩子想读书,想读完初级中学,会有什么困难吗? 对于现在的孩 子来说,这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吗? 但我的初中充满艰涩的人生况味”。这种后面多出了一段很有文采的句子的情况在前几篇的修改中屡屡可见。童先生的这种修改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书稿最后的修改,但因为我的权限有限,再创造这种增加点什么东西的就非我力所能及的了。而且我对于口语色彩的保留,更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因为这样才能让读者看到文字,就立刻感觉到传主在娓娓道来,就好像童先生在对着自己说话。若是全部变成文采飞扬的书面语风格,反倒非我所愿。但总的来说,童先生编辑过程中透露出来的“爱美之心”,还是无时不刻在影响我,让我无时无刻在提醒自己要把这个口述自传做成一个“衔华佩实、文质相兼”的作品,这样方能对得起童先生的郑重其事和精心修缮。
2014年下半年有一次晚饭后,我带着爱人去童先生那坐坐,他家那会正闹蚊灾,但他老人家精神头很好,和我学医的爱人聊了很久,我私下里很为他的状态感到高兴。那年10月份我家屯儿出生,大概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和爱人抱着去给丽泽三楼年逾一百岁的卢乐山先生看看。从卢先生家出来,我们也顺道抱着屯儿在童先生家里坐了几分钟,那时候他也很热情很高兴。再后来听周云磊和我说童先生头受了点伤,我想着要去看看,结果当时忙着孩子和工作就一直没去,到2015年6月,竟然传来了童先生在金山岭遽归道山的消息,留给我的只有遗憾、内疚和无尽的哀伤。
童先生去世之后,我立刻想到了这部近三十万字的书稿,这应该是童先生一生的最完整记录,而童先生自己却还没有完整地审定和修改,因为他总是想着到八十寿辰的时候出版就可以,而相比编辑审定这部书稿,他还有比如《〈文心雕龙〉三十说》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我除了认识童先生外,几乎没有和童先生身边的师友们产生交集,童先生的突然仙逝,让我瞬间陷入了“举目无亲”的惶恐。所幸我得到了童先生的儿子童小溪和童先生的同事程正民、李壮鹰、过常宝,尤其是童先生的弟子赵勇、罗钢、王一川、陶东风、唐晓敏、陈太胜、陈雪虎等人的热情帮助。童小溪先生提供了大部分的照片,并审定了全文。赵勇老师对我有求必应,还主动帮我出了很多主意,他的热心和爽直令我感动。程正民老师对我这个福建小老乡非常亲切,解决了我的许多疑问,又给我补充了很多背景性的介绍,让我对口述内容有了更准确更深刻的了解。李壮鹰、罗钢、王一川、陶东风、唐晓敏诸位老师都对文中部分内容进行了确认。我又去拜访了书中提到的比童先生年长的杨敏如老师、聂石樵老师、邓魁英老师,也都有所收获。更有幸的是这部书稿得到了童先生生前忘年交谭徐锋先生的鼎力支持。可以说,没有谭先生的督促和帮助,该书不可能面世。
万事俱备,我却因为俗务缠身,没有时间仔细编辑处理最后一道,而将此事一拖再拖。直到2017年底2018年初,我才痛下决心,又将书稿最后修订了一番,忍痛将部分内容直接删除,又根据童先生“同期正在写博客,博客中有的内容,口述不再详述,可以参考或直接补入”的指示,选择了一部分博文插入其中进行补充或互证。需要说明的是,此书文字虽然均为童先生口述,但先生并未校订全文,文中不免也会有口误或不足之处,以这样的一个面貌公开出版,所有责任自然在我,希望各位读者有以教我,令此书不断完善。
最终,我仍选择了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将书稿交付出版社。此时距离初次在家见童先生时,北师大校园的玉兰花已经开了五次,香山的红叶也红了五遍,而童先生老家连城莒溪乡墓地边的坟草青了又青,惜乎不及见其亲口讲述的学术人生再次恩泽世人也。呜呼,愧哉!
2018年3月于北师大丽泽11楼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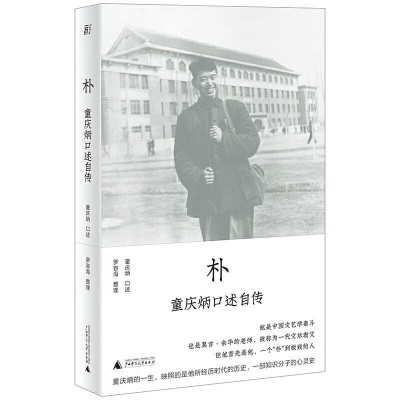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