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鸟》这部长篇以19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为背景,叙述乡村青年毕壮志进入城市打拼所经受的种种曲折、痛楚与尴尬的悲喜剧。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认为,小说的叙述角度以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作为区别只是表面的,“最重要的区别或许取决于叙述者本身是否戏剧化了”,由此可以将小说叙述分为戏剧化叙述和非戏剧化叙述。很显然,《蓝鸟》这部小说以主角的第一人称叙述,合乎戏剧化叙述的基本特征:毕壮志既是主角亦是叙述者。那么作者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叙述方式? 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对于那个急剧变迁的年代,仅提供一个乡村青年在城市打拼、挣扎的标本是不够的(纪实文字中有更多的实例),从精神上自我呈示毕壮志内在矛盾、漂泊的心理过程,并以反讽审视这个精神标本更为重要。毫无疑问,戏剧化叙述创造了作者的“第二自我”,而俞胜的目光正隐含在“第二自我”后面。
“木泥河”是这部小说的“空间”起点,同样也是农耕文化的承载体。在我看来,毕壮志从木泥河镇到县城再到哈尔滨的系列创业、求职遭受的挫折与欺辱,固然与他自身的硬实力相关,更与城乡巨大鸿沟所形成的观念、心理发生剧烈冲突相关。在“木泥河”这个地方,经数千年积淀的小农思维和体制磨盘压榨而形成的畸形自尊,笔者称之为“木泥河意识”,是造成毕壮志一轮轮受挫、漂泊的深层原因。“木泥河意识”有如下表现:固守驴碾之道、一人发财鸡犬上树、死要面子、报喜不报忧、自我浮夸、极易自卑、一条道走到黑等等。鲁迅先生在小说《阿Q正传》中所剖析的“精神胜利法”,堪称畸形自尊的极端表现。
更重要的是,处于“木泥河意识”笼罩下的并不限于纯粹的农民,还包括木泥河中学的教师宋应昌和下海经商的同学米云凯。宋应昌是毕壮志的班主任、同班恋人宋雁秋的父亲。在宋应昌身上表现出来的正统话语和家长意识贯穿了整部小说,始终如一地构成对毕壮志的精神压制。他既是毕、宋初恋的摧花者,也是两人历经曲折结婚后仍无法融解的“坚冰”。小说在开端这样描写他:“平常见了学生,脸就是阴森森的,很少有欢笑的时候,一副要吃人的模样,我还真有点怕他。”宋应昌歧视农村户口、高考无望的毕壮志倒也罢了,还瞧不起“我爹”去夹皮沟“淘金”,竟贬低为“淘石头”。这导致毕壮志与宋应昌爆发了正面冲突。于此可见,宋应昌的“家长意识”并不局限于家庭和校园,而且在木泥河镇都具有话语权。毕大毛因一次失控的冲突导致离校拒考,继而离家出走,率先反抗的正是“木泥河意识”中的核心——家长式话语权威。因此,毕壮志踏上出外求职、创业之路,也同时开启了内心的漂泊之路。
再来看看这部小说的叙述线索及结构。很显然,小说有两条线索:以毕壮志离乡去城里打拼(其实也是“淘金”)为主线,以“我爹”和“我叔”年复一年地去夹皮沟“淘金”为铺线。
“夹皮沟”对于国人并不陌生。在日占时期,日本鬼子曾在这儿挖金矿,杨靖宇率东北抗日联军曾出没在这打击日伪;在小说《林海雪原》和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它几乎与“剿匪”等值,沉淀了“解放”“革命”等语义。当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再度与“淘金”相联系,提示着时代的转换和意识形态的转型——全民奔富、个体价值、市场杠杆,是当仁不让的关键词。“我爹”和“我叔”年复一年地去夹皮沟“淘金”,沿续着一种古老而低端的发财方式,在小说中被反复叙写,而且基本是虚写,很显然具备了象征性:劳而无功、无地点、所“淘”非“金”等,都指向一种荒诞。这条辅线与主线之间,形成了结构张力和叙述节奏。在我看来,“夹皮沟淘金”叙事,赋予这部作品以现代小说的元素或色调。尽管作者没有将“荒诞”进行到底,但它无疑为这部小说增色不少。
这部小说不是所谓的“成长小说”——主角非但没有“成长”,而且最初的理想色彩也褪化净尽。这当然是一个隐秘的悲剧。读者不禁要问:毕壮志仍在重复父辈那怪圈般的命运吗? 他是否会重蹈米云凯那样的结局? 在我看来,在没有真正咬破“木泥河意识”,成为生存的自审者和精神的主宰者之前,谁也不敢妄下否定的结论。至于“蓝鸟”,作者虽然多次描写过它,有意赋予它以某种理想的色彩,但它毕竟游离于小说情节之外,显得既苍白又空洞。在此,我有个多余的建议:作者能否把小说的篇名改为《木泥河》?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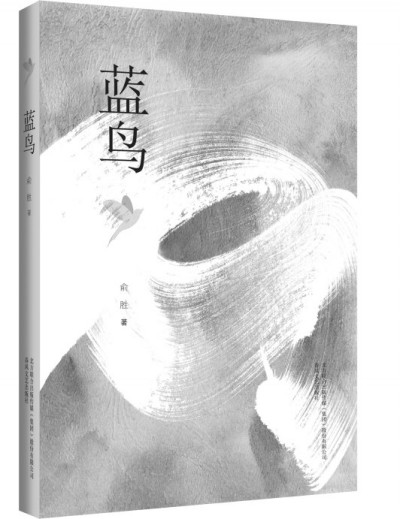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