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是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创作的《大国长剑》《大国重器》《鸟瞰地秋》《东方哈达》等多部报告文学作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这个时代报告文学的精品力作,他也因此获得了无数的荣誉。现在我们讨论的《天晓1921》,是写“寻觅党的一大代表生命遗迹”的作品,也是一部视角独特,发现边缘,饱含深情,为重大主题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可能性的作品,是一部遍访天涯觅党魂的寻访史、口述史和讲述史。在传统的重大主题写作题材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会址、参加者等,已经被书写了无数遍。这个题材如何能够写出新意,道人所未道,是首先面临的挑战。
报告文学与其说是写出来的,毋宁说是“走出来”的。在党史、革命史的写作和出版大繁荣的时代,“1921”这个年份究竟还能写出怎样的新意? 还有哪些角度没有被发掘? 百年前的人物和场景,他们的生前身后还有什么未被讲述或提炼? 归根结底一句话,究竟写什么? 这是对作家最大的挑战。
徐剑知难而上,遍访了“十三位会议出席者的诞生地、求学地、战斗地、壮烈地,乃至叛徒的死无安葬身之地,看见别人未曾看到的地方,发觉他人未曾发现的东西,激活未曾觉悟的迷障”。这既是徐剑的雄心壮志,也是对自己下的一道战书。徐剑给自己定下的写作信条是:“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东西不写,听不到故事不写。”只有亲力亲为才会发现有价值的人与事,才会发现大历史中有价值、有意义的细节。比如徐剑写到了王会悟,王会悟讲到了维经斯基(吴廷康)的来路以及他漂亮的教俄语的太太库兹涅佐娃。通过维经斯基我们知道,他是俄共中央政治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指派的。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说:格里戈里同志,派您去中国,以远东共和国达尔塔通讯社记者身份做掩护,要在那里长住一段日子,把组织搞起来。这个历史细节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不仅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不仅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同时也受到了俄共直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王会悟之所以对维经斯基如数家珍,是因为他们曾经在一起生活过。但是,如果没有别的佐证材料,只是一个孤证,那是有问题的。徐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那部被徐剑一直带在身边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又一次帮助了他,书中记载:
不久我到达上海……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女青年王会吾(原文如此——作者注)。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或者说,这个王会悟并非天外来客,她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这个细节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徐剑写作的严谨。实事求是地说,找到王会悟的材料已实属不易,把它记述下来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质疑或否定它。但徐剑为了免于孤证带来的问题,还是努力寻找到了新的材料作为补充,使这样的讲述无懈可击。
对我来说,书中另一处让我深感兴趣的,是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相见——《上海,润之深晤仲甫公》:
陈独秀与毛泽东,年龄相差十四岁。一个是日本留学生,一个是湖南师范生;一个是北大文科学长,一个是乡村老师。当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当图书馆助理员时,一个月八块大洋。而陈独秀是三百元,是当时众星捧月的人物。……读他主编的《新青年》,他掀起狂飙般的新文化运动,听他那激荡人心的演讲,在毛泽东心中激荡起来的何止是“湘江北去”“浪遏飞舟”,何止是沧浪入夔门、瞿塘,出巫峡,出西陵,入城陵矶的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可是当时他够不着他,润之与仲甫,韶山与独秀山,仅两山之间的简单的交谈,一种远距离的眺望,一个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对文学科长的高山仰止。仲甫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的位置,在陈独秀入狱后,从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创刊号《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思想界巨星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崇敬。陈独秀当时坐牢,或许看不到毛泽东的文章,但在他出狱之后,就能看到一个从湖南乡村走出来,与他一样特立独行的毛泽东,是如何对他推崇备至,甚至喊出来“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还值得称道的,是徐剑对报告文学写法的创新。比如《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刚刚出来时,写维经斯基和译者陈望道的兴奋,然后写陈望道翻译这部经典著作时的情景:
一盏油灯昏黄,将陈望道的影子投到了墙壁上,长长的,变形般的拉长,几乎覆盖了一堵墙壁。他才翻译完第一段话,便被这篇雄文点燃了,这是多么激情澎湃的句子啊,作为政治宣言书,竟然可以这样去写。他沉醉在如此优美的文字中,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暖意,尽管窗外仍是寒冬腊月,他却仿佛已经听到了春天的脚步,时代的脚步。
文字的现场感极具感染力。非虚构也是可以虚构的。从本质上说,任何历史事件一旦进入叙事,既是虚构的一部分。对历史而言,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对历史讲述而言,语言是历史讲述的载体。语言是由历史讲述者掌控的,不同的讲述者使用不同的语言,历史便一定具有了虚构性——因为历史讲述有了不确定性。徐剑的这一讲述,与被述主体翻译《共产党宣言》当时的心情极为恰切,因为那是一部关乎人类未来的经典著述。
采访中也有让我们惊讶不已的事情发生,比如他第一站——应城市刘仁静的老家,下榻的国家电网培训中心旁边就是应城市革命纪念馆。放下行囊便与馆长相谈,馆长竟不知刘仁静为何人。而是捡他熟悉的给作者讲抗日年代董必武、陈赓在此培训进步青年,进行游击战。末了,推荐了姓朱的政协副主席时,耄耋老人见到他,惊叹,四十年了,你是采访刘仁静的第二人。
还有,“在潜江市李汉俊、李书城故里,老屋早已坍塌,青蒿掩墙,野草寂寂,只有一碣碑文勒石:李汉俊、李书城出生地。问为何不建故居,党史办有关人员告诉我,邻居家为钉子户,不愿让出菜地,征作停车场。我颇为不解,李家大哥书城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房子,可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啊。家乡父老乡亲今天能过上好日子,李家兄弟功不可没啊,李汉俊甚至献出了生命。”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修李汉俊、李书城故居的一块菜地居然也征不下来? 仅凭徐剑记述的这些场景,《天晓1921》就功莫大焉。
另一方面,抒情笔调的运用,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比如:
1920年2月,海参崴(俄文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后略)仍旧蛰伏在漫长的冬天里,海山天地白,积雪掩埋了白桦树落叶,褪尽盛装的亭亭白桦,像藏在雪国中的女神,裸着臂膀,将手指伸向了天空,在湛蓝色的天幕上留下一道道抓痕。夕阳一照,仿佛整个苍穹都在流血。
海参崴城通往港口的路上积雪被雪橇碾轧过后,化作一道道坚硬的冰辙,阳光洒下来,红红的,闪闪发光,犹如大地上有一条条脉管,青筋毕露,通向海参崴港,通向远东,也通向世界。
这是闲笔,但在这抒情的笔调中,隐含了作者的情感取向,所谓借景抒情就是这个意思。总体而言,《天晓1921》,是一部发现边缘,通过边缘性材料构建强大的叙事动力,既不重复过去曾经讲述的材料,而是进一步发掘出新材料的作品。这是徐剑的一大贡献;发现问题,敢于揭示问题,在作品中也构成了强烈的今昔对比,这是需要勇气的。徐剑为重大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可能性。同时,徐剑也坚持了一些不变的策略,这就是坚持行走,坚持采访,坚持眼到笔到,坚持内心充满激情,心怀国家民族大业,在细微处做宏大叙事,这就是遍访天涯觅党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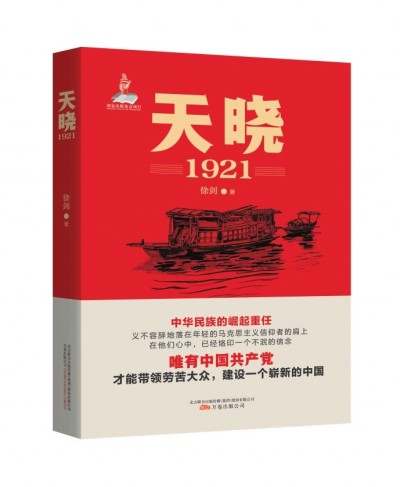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