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当代汉语诗人的个人阅读书目中,鲜少提及丁尼生这个名字,更遑论评议丁尼生的挽歌作品《悼念集》了。但我想,或许这就是真正的作品应该勇于面对的境遇,既不讨巧同时代,也不取悦它的后世,它永远只对自己和理想的读者敞开心扉。
如果没有遇上张定浩翻译的这本《悼念集》,估计我也会错过丁尼生的,至少我还想当然地把丁尼生归入过时的诗人行列。直到我读到“序曲”部分,这样的诗句一下子击中了我:你拥有这些闪光和幽暗的星球/你创造人与兽的生命/你创造死亡;瞧,你的足/踏在你所创造的头骨之上。
读到这些诗句的整个下午,心灵莫名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捕获去,这些神启般的语言令我本能地把目光投注到更远的地方去。接着是不可思议地一行接一行读下去,这些不断缠绕又解开的语言就像是古老的织布机在缝制着一件名叫声音的“衣服”。诗人借助他的“衣服”给予我某种连绵不绝的遐想、忧伤,最后归于平和。我因此开始收集与丁尼生相关的资料,试着对他的时代和个人的生活有所了解,试着去体会他诗歌的力量。
丁尼生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转型的时代,用诗人艾略特的话说,“丁尼生所处的时代许多事物似乎正在发生,铁路正在兴建,新发现层出不穷,世界的面目正在改变。那是一个忙于与时俱进的时代。多数时候,它无法把握永恒的事物,无法把握有关人、上帝、生命以及死亡的永恒真理。”在文学艺术层面上,时代的文学积淀极其深厚,大有到了大爆发的时候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前一个时代是乔治时代,那真是个群星灿烂的时代,出现了亨利·菲尔丁、简·奥斯丁、罗伯特·伯恩斯、威廉·华兹华斯、萨缪尔·泰勒·科勒律治、约翰·济慈、乔治·戈登·拜伦和珀西·比希·雪莱等小说家和诗人,这些大师们的作品在滋养着丁尼生,也为他看待世界提供了某种参照方式。丁尼生早年就是模仿他的文学偶像拜伦,但他很快就从拜伦以及他的前辈作家阴影下摆脱出来,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一生爱漫游和大海的丁尼生的声音就存在于那些远方的自然风光、往事以及内心微妙的感受里。博尔赫斯在文论中更直接地点出,“丁尼生说过,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仅仅一朵花,我们就能明白我们是谁和世界是什么”。无论是风光、美景还是往事以及以花朵作为隐喻,这都说明了丁尼生有一套独特完整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更接近艺术本身,接近人们的普遍心理感受。因此,很快,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丁尼生就成为最受欢迎也最具特色的诗人。人们赞誉他为“可能是耳朵最灵敏的英国诗人”,是韵律的大师,是表现忧郁的大师。
可如果没有《悼念集》丁尼生也许算不上是一位大师级的诗人,至少要比现在逊色很多。当时,就是向来对文学不太热衷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无比珍视《悼念集》。多年后,经受丧夫之痛的维多利亚女王对丁尼生说,“《悼念集》给予我的,是仅次于《圣经》的安慰”。维多利亚女王的这句话恰恰从某种意义上传达出《悼念集》并非局限在丁尼生个人的“悼念”情感上,而是升华到人类普遍意义的情感上,这不仅是说丁尼生的表达技巧的高超,更是说丁尼生在作品中所倾注的情感和精神力量。
对丁尼生来说,《悼念集》首先是来自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的消逝。这位死者就是他的妹夫、青年时的挚友,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按照译者在书中的后记所写的,“对丁尼生来说,哈勒姆并非一位普通的好友,他是世上的光”。哈勒姆是最早支持丁尼生出第一本诗集的人,也是第一个撰写论文来肯定丁尼生诗歌艺术成就的人,同时,还是在丁尼生经历了父亲去世、兄弟生病、退学回家等诸多变故之际,一直以一种伟大的友谊支持和慰藉了丁尼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丁尼生身后的一百多年之后,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断言,迄今为止最好的关于丁尼生诗歌的论说,依旧还是来自哈勒姆。
就是这样的一位才华超群的挚友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遭遇死亡,让丁尼生的陷入了苦痛和失语。对丁尼生来说,写诗是治愈痛苦的唯一办法。写诗也是他寻找和亡灵对话的唯一途径。唯有对话才能不断延迟死者的死,唯有对话才能一再地确认自己存在的意义,也唯有对话人类的爱和勇气以及了不起的精神才能传承下去。
难以想象的是,丁尼生为此挽歌作品投入了十七年的时间。这十七年,他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人接近自言自语地倾述渴望被聆听,在诗文中你会看到四季的变换,光线的移动,风吹草动,枝叶的婆娑、露水打湿墙体,塔楼的钟声,林间和公园的漫游者,街区的变更,时睡时醒的时分,至爱之人的爱与伤痛,永远不会中断的辩论,无尽的结伴同行……因此在《悼念集》作品中,丁尼生首先投入其中的是个人极其真挚的感情和伤痛,这其中还包括追忆往昔的欢乐时光,他如何纠缠在生与死的界限里,如何克服这一残酷事实的心迹。我读到的已经不仅是丁尼生个人的投影,而是人类的投影,人类的声音。那时而哀伤、彷徨,时而乐观、从容;那时而与残酷的苦痛对抗,时而与天地和解;那时而沉湎往昔,时而穿越未来;时而仰观,时而俯察;时而欢乐,时而忧惧;时而是人,时而是神;时而浑浊,时而纯正;时而低音,时而高亢……无数动人的细节在翻腾着,无数柔软的心事在渗透着。
但最终,丁尼生没有屈服命运和个人的悲哀,他在长篇的独白之后,心灵获得安慰:因此我的激情并没有屈从于/软弱,我发现一种安慰心智的/图景,在我的悲痛中/有一种力量得以保持。
诗人的文字表达技巧和精神力量除去信仰和个人的禀赋之外,还有他(她)的时代所赋予他(她)的。实际上一位真正了不起的诗人、作家就是要成为“同时代人”,正是“同时代”在激发他(她)的所有感受力,涤荡着他(她)的情愫,提升他(她)的眼界,最终汇入那奔腾不已的文学海洋里。也正是如此,丁尼生的作品在经历了一百多年之后,借助翻译家之手让我们感受到其作品的巨大魅力,感受到他那颗不安跳动着最终又获得平和的心。
在丁尼生的笔下,时代不仅仅是他眼下所见的那个时代,而是一个更加开阔的时代。表面上他写的是“悼念”(或者说是“追忆”),实际上他面向的是“未来”(或者说是“永生”),一如古人所写的那些招魂或安魂曲一样,写作者从未觉得那人已经离去了,而是把那人当作还存在在天地之间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可以规避对死亡的恐惧,更是传达出对爱的确认。作为物理上的人可以“失去”,作为精神上的人永远不会失去,死者通过诗人的声音对抗着茫茫黑夜。正是在这一点上,作家诗人和读者都对“挽歌”这一文体颇为熟悉,不同于一般的挽歌作品的是,丁尼生的《悼念集》超越了一般的哀悼和思念,而把它引向更开阔的路上,或者也可以说,丁尼生是在茫茫黑暗中寻找这世上的光,类似但丁在《神曲》中通过维吉尔引导着去寻找“贝亚特丽斯”,穿过悲怆的世界抵达乐观希望以及永恒的意义。
感谢译者张定浩娴雅清逸的译文,让我读到一个全新的丁尼生,一个清晰准确的丁尼生,一个我能感同身受的丁尼生。虽然是悼念作品文体,但在译文中充满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幽微缜密的诗意。通过阅读这样的诗歌,我们会重新审视自己与人与时间的关系,学会去理解他人爱他人,审视我们的时代,去感悟天地万物,或许也因此发现自己理解自己,并带着这种心情继续前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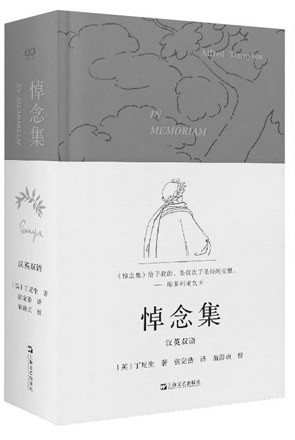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