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撰写《子午线的牢笼——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当代艺术》这本书的时候,我正在美国访学。更准确地说,我当时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我与法国相距遥远,汪洋之海将我与故土分离开来。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我才能整理自己的思绪,而这个莫名的原因也解释了我为何如此执着地前往那些陌生的边缘地带。走向远方、经常探访我们不熟悉的边缘地带有时是非常有好处的。这种活动带给我们的刺激让我们告别了舒适的固有生活,摆脱了重复的思维模式,远离了过于良好的生活环境带来的昏沉倦怠。我们应该走向别处,来告别熟悉的生活,来真正地走向世界。因为有一点我是非常肯定的,那便是只有走出子午线的牢笼,我们才能挖掘我们拥有的全部潜力。我们的文化可以向远处延伸,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曾经被视为异域的、他者的文化源源不断地注入到我们的原生文化之中。文化被纳入一个多维度的、全球化的巨大网络中,并且在边界、界限和限制之外被颠覆和翻转。作为文化的基石,我们对知识的好奇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奢侈品,而是一种必要条件。
就在不久之前,对于一个法国人或者欧洲人来说,中国代表着一种极致的异国情调。我们对其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在一部部游记或者鲁迅、巴金等人的小说中,我们接触到了中国的点滴。我们为这段历史、这个语言和这个国家所折服:我们知道,我们永远都无法读懂这个国家的谜题。在某种程度上,面对这个如此辽阔的国家、面对如此陌生的文化形态,我们束手无策,因为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认知上,我们都与中国相去甚远。意大利著名导演吉安尼·阿梅利奥(Gianni Amelio)曾拍摄了一部名为《亚美利加》(L'America)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美洲,这个现代移民想象中的理想国,已经不再是“亚美利加”(America/l'Amérique)。对于参与这次伟大航行的移民来说,美洲变成了“拉美利加”(Lamérique),一个比在海雾中消失的地平线更加遥远的乌托邦岛屿。就像所有的乌托邦一样,它只兑现了一部分诺言。同样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中国(la Chine)曾经是“Lachine”,一个建立在幻想之上的非真实的实体。马可·波罗曾经游历过中国,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也曾在1972年的电影《中国》(Chung Kuo -Ci⁃na)中描写过北京、河南、南京、苏州和上海。在他们二人到访中国之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对中国总结出的一些关键词一直都没有改变。曾经,面对中国,人们感受到的只是纯粹的惊异。中国被置于关注视线的中心,而这些混乱的视线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无法避免又多少令人绝望的异国情调。我们曾经考虑过对话沟通吗? 曾经,“中国”至多是几个知识渊博的汉学家探讨的主题。
如今的情况截然不同,一场新的革命仿佛已经到来。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难以猜透的谜题。它打开了国门,已经完全走出了封闭的状态。欧洲亦是如此。如果说昔日的欧洲曾经坚定地信奉“普世主义”的话,那么现在的欧洲对种族中心主义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并且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自己的位置。而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不是所有人——能够自由穿梭其中,并且能够发现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所包蕴的魅力。现在,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仅仅从外部、迂回地带着偏见去了解中国。我们可以从内在去认识它。在新墨西哥大学任职期满之后,勒·克莱齐奥(Le Clézio)于2013年入职南京大学。也许就在不久之前,对于一个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说,这样的一个选择还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如果选择美国的某所高校,人们也许会觉得再正常不过了。为什么是中国呢?但是现在,勒·克莱齐奥的这个选择已经变为了虽不平凡但却极为正常的一件事了。而且,这是个让人拍手称快的消息。中国不再仅仅是少数行家——汉学家和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熟稔于心的人——的研究对象。从今往后,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好奇、出于对中国知识的渴求开始关注中国。勒·克莱齐奥非常清楚这一点。他的文字丰富着文学史的书写,而文学史之所以是我们关切的重点,是因为它是社会的见证。文学史见证着什么呢?“不管我们在何处写作,不管我们用什么语言写作,我们对文学的期待都是希望它能够成为社会的见证”,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十五谈:诗学历险和文学交流》(Quinze causeries en Chine.Aventure poétique et échanges littéraires,2019)中如是说:“我们希望文学能够表达人类的整体性,能够跨越精神和地理的边界,能够创造一个新的、比过去更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关系不是建立在特权和成见之上的。我们还远达不到这个境界。这并不是我的痴心妄想。”是的,我们还远达不到勒·克莱齐奥描绘的境界,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通过这种途径来改善关系。
至于我,我曾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害怕中国,至今也依然如此,只是害怕的程度越来越小了。比如说,我在地图上看到西安和济南两座城市相距如此遥远。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我也曾对中国一片茫然。在我的脑海中,中国被淹没在一系列模式化的、多少有些刻板的形象中。总而言之,我曾经对地图有着非常肤浅的认知。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非真实的实体“Lachine”。而后来有一天,中国走近了我。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我所任职的大学与西安外国语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每年,西安外国语大学都会有一批学生来到利摩日大学跟随我和我的同事们上课,或者参加研讨课程。我们逐渐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是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我的职业是传授知识,很快地,通过我的学生们,我传递出的知识在远方得到了回响。“Lachine”逐渐变成了“la Chine”。对中国不同侧面的认知接踵而来。我曾经觉得,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走向中国的通道,即使是一个不起眼的、狭窄的通道。在我有限的认知中,我知道了解中国是大有裨益的。我继续与来自西安的同学进行交流,与此同时,我开始大量阅读中国的小说、散文和各类作品,比如王安忆、李敬泽等人的作品……我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具体,尽管中文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意识到已经错过了许多好的机会,但是我们同样学会了辩证地看待问题,不至于彻底放弃。无论如何,我们越是了解世界,我们越会明白生活中有许多令人遗憾的地方。也许文化的全球化最后把我们带向的正是这样一条充满矛盾的智慧之路。
这种对距离的思考是促使我写下本书的原因之一。在全球化范围内去思考文化,特别是文学和艺术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我们面临的第一种选择是只谈论我们知道的,或者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东西,与此同时,忘记我们曾经许下的诺言:跨越边界,甚至在理想状态下跨越所有边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我们所采用的解决方式之间有一个明显的鸿沟。种族中心主义伺机窥探。所谓的种族中心主义,就是一种文化成为全球所有文化的标杆。而“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并没有被排斥在这个危险之外。第二种选择与第一种截然相反。为了跨越我们自认为熟知的文化的边界,我们开始谈论那些我们并不了解的东西。以我自己为例,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对我来说就是陌生之物。然而这样一来,危险是巨大的。这是个明显的错误,有可能是一种更加单纯的但是同样虎视眈眈的民族中心主义。但我认为,面对全球化,我们应该更倾向于第二种选择,而不是让自己困于封闭保守的境地,这是一种更加令人失望的状态。这种选择并非没有后遗症,但是在我看来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选择,一种值得一试的选择。换言之,我们要学会——如蒙田所言——“在别处思考”。这就意味着我们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向前发展,身在“此处”却心系世界,并且承担着犯错带来的风险。除此之外还有他法吗? 逃离子午线的牢笼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人性的探险。像所有的探险一样,它是无法预知的。我们只需要带着谦卑之心和些许方法即可开始这场探险。当然,在开始这场旅行的时候,我们需要避免从局部出发,不要以高高在上的口吻给整体下定义。
在本书中,我有没有贯彻这些原则呢? 坦诚地说,我自己也不太确定。相反,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在写这本书之初,我需要将我所了解的关于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全部知识汇集起来,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思考全球文化,并且在其他文化的反照下思考我的原生文化。这个全部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开始这本书的论述来说已经足够了。比如说,我在这本书中提到,我很晚才意识到,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文学理论无一例外不是一个普世的绝对值,而是一个被地域化的人工制品。一本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著作帮助我摆脱了自己的文化中心主义思维。我甚至为自己曾经的天真想法自责不已。需要指出的是,几十年以来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学习强化了我的“视差”,或者“文化中心主义”。我是在2014年春天到2015年夏天完成的这本书。那时我还没有去过中国。但是自此之后,这个遗憾得到了弥补。致力于推动地理批评的乔溪老师邀请我前往西安交通大学,进行了为期几周的授课。在朱立元教授和陆扬教授的邀请下,我又在复旦大学进行了讲学。我还在中国其他高校作过报告。中国之行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非常美好的。我将来还会去中国,因为正如勒·克莱齐奥所说,“书籍是我们最自由最美好的一部分。正如中国人所说,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遨游”。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写的,平等沟通的海洋应该将世界上的所有文化连接在一起。因此,我还要感谢张蔷老师为翻译本书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希望我们继续徜徉在勒·克莱齐奥笔下的海洋中。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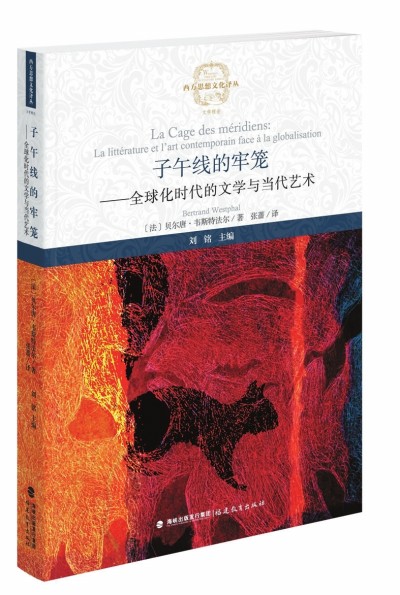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