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关系东南第一人”,集“状元”“实业家”“教育家”“政治家”等标签于一身的张謇过于传奇:农家子弟出身而在科场夺魁的他曾赴朝平叛、弹劾李鸿章、参加强学会,本可以像其师翁同龢那样无限接近权力中心。然而,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时白发老臣长跪于积水中接驾的一幕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使其愤而摒弃仕进之念,随后转而投身于实业。他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把家乡南通建成“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研究领域也并不冷清,各种传记汗牛充栋,“张謇国际研讨会”已历六届,“张謇文化艺术周”亦经七届。不过,学界研究张謇,多从实业、教育、政治、历史等角度入手,注意到张謇“诗人”身份的人并不多——毕竟他不曾在诗坛叱咤风云,其诗名亦不算高。随着南通大学徐乃为教授《张謇诗编年校注》(后简称《校注》)一书的问世,这一现象有望得到改变。
收诗1400余首的《张謇诗编年校注》堪称有史以来最完整的张謇诗集。徐乃为发现:过去张謇诗歌之所以未能得到学界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部分张诗都未能在他生前死后流传出去。陈衍、汪辟疆、钱仲联等名家主要依据的是他早期诗集《张季子诗录》,此书所收录的张謇诗歌截至1911年,仅占其诗作总量的三分之一。其实,张謇中晚期诗歌不仅题材广泛、特色鲜明,而且艺术水准更臻成熟,不乏佳作。不过,张诗毕竟典雅古奥,且喜隐曲其旨,要读懂并不容易。而徐乃为探佚索隐,为我们读懂张謇诗歌提供了可能。
徐乃为研究张謇,看似走了一条最难的路:字字推敲查出处、老老实实做编年。此书耗时十数年、堆累百万字,非对学术有执念之人不能为之。他之所以会以一人之力独自校注张诗,一方面出自于对古诗词的痴迷,一方面在于深受这位乡贤精神的感染。徐父早年在海门国学专科学校读书时曾见过张謇,徐乃为自幼就经常听到“张状元”的故事。种种机缘,促使红学家徐乃为最终成为了张謇诗集的校注者,为其付出十余年心血而无怨无悔。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云:“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此句说尽注释之艰难。校注张謇诗亦如此。徐乃为在《后记》中感慨:“篇中一字之阻,便如盘石挡道,不撼而移之,不得过也”,并把文中不留“挡道盘石”与“大致可读”视为校注的要求。注释张诗,不仅需要一一查明生僻古奥的词语与典故,把握诗人吟咏风格的隐曲度,还需探知每一首诗歌的创作动机及相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校注张诗,更有三难。
一难难在张謇情感经历丰富,作有不少隐秘诗,采用“隐曲”之法。例如,张謇与其女学生谢林风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谢氏学毕离去,张謇甚是不舍,作有《林檎三十二韵》五言排律。此诗表面看就是关于“林檎”的咏物诗,然虽无一处明写二人情愫,实际却处处相关二人情愫。注释揭隐之后此诗之意遂豁然开朗。循此而能抉出多首“涉谢诗”。此类揭开“隐饰”面目的诗,至少还涉及一个名“润”者的诗,关于沈寿的诗等等。与此相类的,还有多首寓言诗。徐乃为将这一艺术手法概括为“隐曲其旨”。
二难难在张謇国学功底浓厚,作有不少“考古阐学”的学术类长诗,极为难解。有的涉及钟馗故事、“驱鬼”、“傩戏”等习俗;有的考证寿星木公金母形象的由来以及演变,“老人星”在各时令中的位置变化,寿星使用的拐杖的转变;有的专论礼制、礼器、书法等专门知识;有的涉及中国历代各地石经的镌刻及其特点……以上种种,对于注释者而言是极大的挑战;但若不能尽明所指,恐难管窥张謇学术精华。面对这些“挡道盘石”,徐乃为亦迎难而上,一一考证,探明所指。
三难难在张诗的存稿多是手稿,其子张孝若整理时错认不少字。徐乃为将其一一辨误复正,这也需相当的功力。例如,张謇的《松花粉》一诗,中间四句是“似浮黏蝶带,偶落点人衣。蘸露愁还泥,含风看渐稀”,第三句可解为“松花粉沾露落于泥而生愁”,似乎颇通。但此诗是五律,“泥”字位须仄声字,因此,徐乃为校“泥”为其形近的“浥”,仄声,沾湿的意思,并指出意出“渭城朝雨浥轻尘”句。如此一来,便十分安妥。
诗歌是打开张謇内心之门的金钥匙,《校注》为我们理解张謇提供了新的文献。张謇的传奇人生虽然被反复书写,却依然有许多难解之谜:赴朝平乱是张謇人生的转折点,立下大功的他曾有机会在朝鲜大展宏图,却为何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关心时政的他一生中有许多在政坛上飞黄腾达的机遇,却为何偏要选择“状元办厂”这条艰巨坎坷的路? 晚清民国间政局纷繁复杂,昨日风光无两之人,明日或许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张謇却似乎是个例外,他为何能够在风浪之中独善其身,广交各派友人?《校注》的问世,为我们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提供了些许线索。
《校注》的问世,让我们得以借助诗歌触摸张謇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他既是一个个性鲜明、待人真诚的实业家,也是一个在政坛纷扰中内心充满屈辱与挫折感的敏感诗人。《校注》无疑为晚清民初的旧体诗研究增添了一份重要的文献;对于关心张謇的读者而言,则开启一个崭新的视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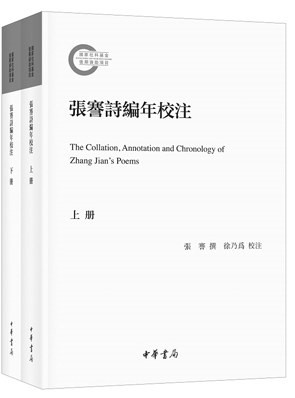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