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何谈风雅》,是陈歆耕先生的“六十自述”。我因为深爱文学的缘故,所以牢牢记得他曾经是《文学报》的社长和总编。陈先生喜欢徐渭晚年的诗,《何谈风雅》自序题为《半生落魄已成翁》,自嘲中透出谦逊,令人敬服。
陈先生行踪甚远、涉猎颇广,考证过苏州同里古镇退思园的主人行迹、海上云台山陶渊明公的遗迹,论述过老子“圣人观”形成的“触发点”、林语堂《苏东坡传》的偏见与硬伤,探讨过龚自珍儿子是不是卖国贼、乾隆年间极品美女阿扣到底对不对,膜拜着成都杜甫草堂的唐代诗人杜甫、被历史烟尘遮蔽的《新华字典》之父魏建功,但他最用功处却在北宋那片“群星灿烂”的天空。
盛世风华,文星昌耀,大宋王朝的天空确实星光璀璨,如同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最优雅的风尚和最不雅的争斗,最淡然的文艺和最激烈的政治,最真挚的友人和最凶恶的敌人,众所周知的璀璨群星和隐蔽其中的人才匮乏……尽在《何谈风雅》这本书中。叙事、论理,夹叙夹议,陈先生善用“双峰对峙”和“二水分流”之法,而贯穿全书的,则始终是风骨和风雅。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是宋人生活的“四般闲事”;香器、茶器、酒器、花器,在宋朝极尽优雅之能事。宋人朝堂的斗争哲学和百姓的生活美学一样,给后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四次被贬被罢,临终前手抚榻几郁郁长叹;“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苏东坡,被贬斥流放无数次,陷入“乌台诗案”险些丧命;“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的司马光,平生志向并非编撰《资治通鉴》,而是在庙堂之上实现政治抱负;“怊怅有微波,残妆坏难整”的王安石,一场雄心勃勃的变法终归失败,罢相后黯然退归江宁半山园。
说到北宋,绕不过苏东坡。在苏轼的交往中,有章惇这样从密友到敌人的,也有对苏轼始终“如一”的当朝驸马王诜。王诜,是西园雅集的召集人,大名鼎鼎的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李公麟、米芾、张耒都是雅集成员。宋代礼制特殊,公主和驸马接见宾客须特许,所谓“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王诜和苏轼的私交,不能不成为政治上高度敏感的事。在“乌台诗案”中,苏轼遭受了严厉惩罚,王诜也未能幸免:勒停两官、贬放外地。
大宋王朝群星璀璨,又是谁发出了人才匮乏的呐喊? 还是忧乐天下的范仲淹。“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历史证明,范仲淹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有识之士,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切肤之痛——很快,徽钦北狩,北宋灭亡。在陈先生眼里,堆积如山的歌“宋”文字,抵不上清代王夫之的一篇《宋论》。
友人也好敌人也罢,忧国也好忧民也罢,庆历新政也好王安石变法也罢,俱往矣。“春归何处? 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黄庭坚的词,说春也是说宋,写季节也是写历史,“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在历史的风云中,“百啭无人能解”,只缘身在此山中,陈先生《何谈风雅》却为我们解读历史,解开谜底,让我们“因风飞过蔷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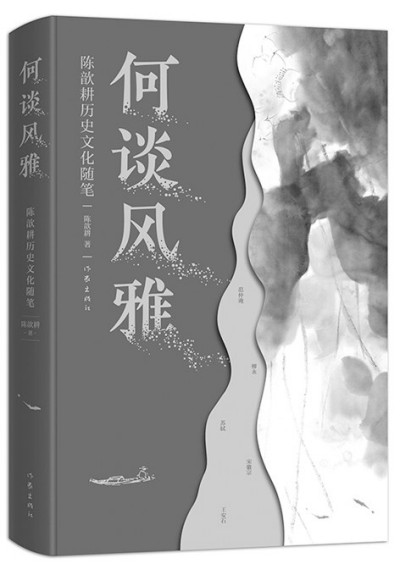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