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乡愁是属于土地、农村、农人的,尤其是远离故土的农人之后。乡愁者,乡野之思也。乡野之思是大地之思,是大地之上物候、农事、爹娘和乡亲之思,是故乡的方言之思。思而有感,感而为声,是有乡愁。
乡愁是大地文章:生长在田野中的,牵挂在农事节气上的,可以闻见芳香的泥土,可以带来温暧的柴草火光,可以聆听的霍霍磨镰声、放水开秧田声、瓜缕攀爬声、雨滴屋檐声……那都是乡愁,都是诗啊!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地”(《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很遗憾,我不认识《我们的乡愁》这本书的作者们,但我敢肯定他们是亲近本源者。
本源是大地,是大地上的草木。本书选文《与草木同安》中,作者写草木,让人动情:“草木,也是有灵魂的。”夺人心魄之开卷也。随后的议论看似信手写来,其实有深意:“草木的灵魂,带着一种素心。它不选择土地,或许它是从远方而来的一粒种子,带着异域的方言,落在陕北的大地上……”其中,“素心”的“素”字绝妙,而且还“带着异域的方言”。从大地中涌动而出的山花野草,那向着天空的言说,我们即使看不见、听不见,却感受得到。作者进而写:“草木的精神是一种善。它们潜伏在山中,看似强势,郁郁葱葱,让一座山有了灵气;其实,花枯叶落之后,就只剩下一地干柴,衍生出一缕缕炊烟。”正是草木,让人间有了烟火气,这就是生活的意义了:“从草始,归于草。一些草,注定一辈子无人问津,但它们仍遵循着节气,遵循着风水;五谷,不过是草的一种,只是被祖先从草里鉴别出来,能填饱肚子,才以粮的面目高于野草;还有些草,心怀高义,像珍宝一样被人小心翼翼地挖出来、晒干,送进中药店变成灵丹妙药,成为治病救人的符号。”结尾处,作者写到柴胡:“凡是带着柴的草木,我都格外亲近……家里的柴决定着生存,决定着温饱。炊烟袅袅,永远是乡下人理想的活法。”当柴胡成为中药材之后,“只有在山中,它们才具有草木的原始样子。”
淡泊的文字,草木原始的样子,从地下生出的乡愁,却给人予“寂静的轰鸣”之感。
辛丑端午前,我回到故乡崇明岛,友人请我在岛的西端——西沙一处农家院里闲聊。星月满天时,正在喝茶,忽然传来蛙声一片,“呱呱”地此起彼伏。我当即起身,欲寻蛙鸣处。走在林荫小道上,远近皆蛙声,只是青蛙不得见。但我又怎能忘记儿时在秧田里提着“洋灯”捉青蛙,它那鼓着肚皮鸣叫的样子呢? 朋友告诉我,再过些日子,西沙还会有萤火虫,那真是闪闪发光的向往了。还没有等到萤火虫飞,却读到了本书中的《萤舞蹁跹》:“季夏之月,腐草为萤。最美妙的当然是流萤在地、繁星在天的朦胧景象。有了这光亮的装扮,寂寥的乡村夏夜也便灿然而灵动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萤火虫是生态环境的标志——有此发光的小虫,青山绿水存焉,无它则反之。作者娓娓道来的是儿时的夏夜,是孩子们追逐萤火虫的快乐,直到把它“捧在手心”,“看那一闪一闪的小尾巴”,告诉我们“人世间有两种最美的光,一是此生不渡的美丽星河,二是触手可及的萤火。星河让人仰望,萤火给人温暖。”结尾处,是在大力治理污染后,姐姐告诉他又能“再见萤火纷飞了”,于是“我和孩子约定:今年暑假回乡,一起寻找记忆中的萤火虫。”全文不见“乡愁”二字,却处处都有乡愁的影子。
本书使我难以释卷的是文字的简炼与妥帖,尤其是文字中吐露出的境界的高远。文学创作中当今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词语的疏忽,对古先贤的炼字炼句说弃之久矣! 这里有个识字的问题。作家能不识字吗? 当然不会。但假如用字不准确、不妥帖,那就很难说是识字了。梁启超有论:“识字和闻道真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吗?”而后自问自答:“一点也不错,一个字表示一个概念,字的解释弄不清楚,概念自然是错误混杂或囫囵……所衍生出来的思想当然也同一毛病。”话题始自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一字一字地分析解读,寻根究底,震惊学界。梁启超说戴东原“自成一家言”,“以识字为手段,而别有‘闻道’的目的在其后”(《饮冰室合集·戴东原哲学》)。本书中的《乡音》,恰是民间语言在一处人居之地,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取舍,留下的文字瑰宝,并被写作者采用。作者春节返乡,与小爷爷的对话如下:“小爷爷,您身体怎么样啊?”“还占(可以),一把老骨头了。”由字及词,如“还占”,占字是方言,“还占”一词便是还行的意思。又如“我叔叔呢?”小爷爷说:“你手受(叔叔)正忙着哩。这不,你们都来了,他要待且(亲戚)啊!”这里有“道”吗? 有,乡音高贵,亲情之道也。这就告诉我们,方言或者说乡音,有烟火味,有乡土味,有亲近感,它仿佛从泥土中涌出,涌向心头。
一切文字的学问均关乎修辞学。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称:“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境的:或则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种种权变,无非随情应境随机措施。”本书中,《一犁新雨破春耕》写的是一个祖父、一头牛、一个犁铧、一处池塘,耕地放水、耕牛喝水,“同那些苏醒的农具一样,它也在等待祖父的召唤”;写的是农人对土地开耕的情景,“神情庄重,一脸虔诚”“在这空旷寂寥的田野上,祖父哒哒咧咧的口令声,像潮水一样弥漫开来,给人一种粗旷豪迈,荡气迴肠的沧桑感。”于是,土地与耕牛及老祖父,无不随情应景且情景交融。
由此引出了我的另一番感概:《人间词话》谓“词以境界为上”。岂止词,一切文学作品皆然。王国维对“境界”说的重视,可从他的反复论述中窥见,其中有“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本书的作者虽大都为业余创作者,却有情有境,且真情真境,即便是从回忆的时光中捡拾而得,无不境界毕现,得大地之思,是心性毕露。又思及当今遍地文章,境界难觅时,能不为亲近本源者点赞击节? 多好啊,如此这般的词语,“屋檐在上,檐下是家”!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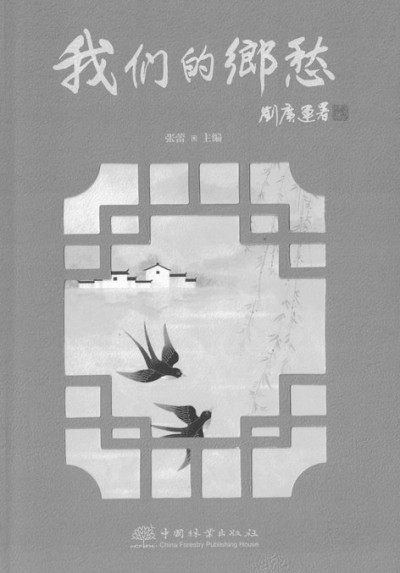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