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就与中国往来频繁,关系紧密。半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社会生活诸方面,都深受中国影响。但在学习吸收的过程中,如官僚制度、礼仪规范、文字诗赋、婚丧嫁娶等,又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表现形式。例如宗法制度中的嫡庶关系,中国虽然也有较为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但在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与供职朝廷建立功业方面,嫡庶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而在朝鲜半岛,嫡庶之间,有着极其分明的尊卑贵贱之分,有着天壤之 别。如 朝 鲜 成 宗 时 期(1470-1494)颁布的《经国大典》(朝鲜宣祖三十六年,1603年刻本)规定:
文武官二品以上,良妾子孙限正三品,贱子孙限正五品;六品以上,良妾子孙限正四品,贱妾子孙限正六品;七品以下至无职人,良妾子孙限正五品,贱妾子孙及贱人为良者限正七品,良妾子之贱妾子孙限正八品。兵曹同。二品以上妾子孙许于司译院、观象监、典医监、内需司、惠民署、图书署、算学、律学,随才叙用。
朝鲜王朝这种嫡庶尊卑制度,导致等级森严,判然两途,国中分为宗亲、国舅、驸马、两班、中人、庶孽、胥吏、常民、贱民九等。于是产生一些中国古已有之但含义完全不同的词语,即“两班”“委巷”与“中人”等。“两班”即文武两班,是高高在上的贵族阶层,亦即自皇室至高官贵族的嫡子系列。“委巷”出自《礼记·檀弓》“小功不为位也者,是委巷之礼也”。在朝鲜指住在曲巷的庶孽子弟,为两班与士大夫外之平民,委巷人相当于中人、庶孽、胥吏之泛称。朝鲜正祖十五年(乾隆五十六年,1791)冬,捕得邪学罪人(即天主教徒)郑义爀、郑麟爀等十一名,多为中人,正祖即痛斥“大抵中人辈,非两班,非常人。居于两间,最是难化之物”。
这些“所谓中人之名,进不得为大夫,退不得为常贱”。在阶级固化、鸿沟难越的朝鲜半岛,他们上不能与嫡子系列争高官显宦,难以升入朝堂治国理政,下不愿坠入埃尘,与卑贱贫民浑然一体。他们中满腹经纶而自弃才能者,沦落为“穷而能诗”的委巷诗人;而身怀绝艺者,则或成为出使路途的译官,救死扶伤的医员,丹青绘世的画员,抚琴弄鹤的乐师,谈天运筹的算学者,舞刀弄枪的“马上才”等,遂形成倔强而顽固的另一种势力,成为朝鲜半岛特有的中间阶层。
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运途?在半岛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向来对此关注者并不多见,而韩国延世大学许教授敬震先生所著《朝鲜时期的文艺复兴与中人》一书,恰好能部分地回答这些问题。该书原由韩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于2008年初版,现由许教授高足刘婧博士译注,文字清通,趣味横生,于2021年4月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使得中国读者得以拜读此书。
二
许敬震教授浸淫朝鲜半岛古代文史研究多年,著述有《朝鲜委巷文学史》《韩客人相笔话》《东亚文化交流和移动记录》等数十部。这部《朝鲜时期的文艺复兴与中人》并不是艰深晦涩的专业著述,而是一部既专业又通俗的撰述,书中附有大量珍贵的插图,因此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朝鲜时期的文艺复兴与中人》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仁王山一带过着诗意生活的文学同人》以中人阶层的诗人与诗社为主,叙述他们的诗文唱和与交游活动。第二章《描绘和歌唱世间百态的艺术家》主要围绕中人画家、收藏家、歌者与乐师等展开论述。第三章《直面阶级斗争、引领时代潮流的专业知识人》主要记载中人医生、天算学家、新闻记者、律师、棋手、天主教徒等。第四章《穿越大陆和海洋,开辟新世界的译官》论述的多为出使中国、日本的译官等。
从许教授此书,我们形象而直观地了解到,朝鲜时代的汉城(亦称汉阳、汉京,即今日首尔)划分为南村和北村,其中间地带的清溪川一带即委巷人居住地,仁王山一带也是他们寄身之所。清溪川一带居住的是译官、医员以及商人等富裕的中人,仁王山麓主要居住的是胥吏和衙前。委巷诗人,多在仁王山麓活动。又以钟路为界,王族和两班居住在景福宫和昌德宫连接的直线以北地区,昌德宫为中心的嘉会洞、齐洞等北村居住着两班士大夫;南山脚下居住着没有入仕的儒生;而中间地带,即清溪川附近则居住着译官和医员等中人;仁王山脚下居住着中央下级官吏京衙前。这种聚类而居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以清溪川为界,形成了汉城城市的居民分布格局——今日清溪川两岸,还特意建有一些悬挂岸边的贫民建筑,供人们了解昔年的市井百态与居住环境。
本书中的一个个鲜活案例,为我们了解朝鲜时代中人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诚如许教授所言,“因不属于支配阶层,他们的生平可以说既不伟大也不华丽,可是内容却有真实性、体验性”(本书第89页)。我们以许教授书中的委巷诗人和译官为例,来看看他们的职业环境与百变生活。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朝鲜中宗三十二年 1537),差往朝鲜颁皇子诞生诏书的正使翰林院修撰龚用卿,改汉城仁王山为“弼云山”,取“右弼云龙”之意。仁祖时期的朝鲜重臣李恒福建有弼云台,中人阶层的诗人常集中在这一带活动。他们前后创立有松石园诗社、碧梧社、洛社、西社(白社)等。如画员赵熙龙五十九岁时组织“碧梧社”,是因为六代为医的樵山柳最镇家中院子里的老梧桐而取名。朝鲜哲宗十二年(咸丰十一年 1861)正月十五日,画员刘淑画绘有《碧梧社小集图》,医官李基福序称“用文潞公四老会故事,证源源旧友集碧梧社,镇日欢畅,仿兰亭会,各自诗自韵例”。这种诗社活动,仿中国宋元时期的“六老会”“九老会”之类的形式,白天集中在一地,吟风诵月,较艺比胜,号称“白战”。
委巷诗人的作品,也不断被结集刊行,如奴婢出身的崔奇男编选的《六家杂咏》,就包括医员郑柟寿、南应琛、郑礼男,禁漏官金孝一,译官崔大立和他自己的作品。后来崔氏的书堂弟子林俊元等,挑选了161名815首委巷诗人的作品,编成《昭代风谣》九卷,后人又续编有《风谣续选》《风谣三选》等。
朝鲜时代著名的委巷诗人,前后有崔奇男、洪世泰、高时彦、郑来侨、李彦瑱、千寿庆、张混、李尚迪、郑寿铜等,至赵秀三而极,为委巷诗之集大成者。他们一方面继承《诗经》、汉乐府、白居易以来诗风,关注民生,讥刺不公。也有不少的委巷诗人,无病呻吟,勉强附凑,被称为“弼云风月”,即“浅溥的风月”,或者“千篇一律的诗文”之义。许教授指出,这些委巷诗人,通过诗社活动共生共存,强烈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中人阶层的诗人虽然不是政权的核心人物,却是国王的专业技术家,常常因为政权的沉浮走上流配之路。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中人之间也更为团结并且惺惺相惜,他们结社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诗文的创作,也如碧梧社的成员一样,共度人生。”(第44页)
与委巷诗人吟弄风月不同的是,译官在朝鲜半岛起着重要的外交翻译与沟通作用,他们也逐渐形成世家,代代相传。如许教授书中论述的牛峰李氏,历经九代,有三十多人在译科考试中及格,可谓是世袭的译官家族。如仁同张氏家族培养的译官共有22名,虽然占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一,但是一等合格者较多,也培养出了在政治、经济上手段极为高超的人物,形成了译官名门家族。中国观众在韩剧中熟悉的阴狠谋毒的张禧嫔,其父即译官张炯,其堂叔张炫和炫弟张灿等也都是有名的译官,在燕行队伍中常常有他们的身影。密阳卞氏的卞季良,到第十九代卞应星时通过译科考试,定型成了中人家族。卞承业家族和后代中有译官46名,包括从业者高达75名,是朝鲜代表性中人家族。十九世纪后半的开化期,卞氏家族开化派辈出,主张朝鲜和美国联合,译官卞元圭就是其中代表之一。
朝鲜被称为开化派鼻祖的人物一般指吴长锡、刘大致和朴珪寿三人。译官吴庆锡曾出使清朝13次;刘大致作为译官之子,后学习医学成了医员;朴珪寿曾任左议政。吴庆锡认识到靠中人来主导开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所以通过朴趾源的孙子朴珪寿来领导北村的两班士大夫子弟进行开化活动。吴庆锡在北京购入的世界各国的地理和历史、科学、政治等相关书籍,通过刘大致、朴珪寿传授给了金玉均、朴泳孝为首的北村青年,从而在朝鲜形成了开化派的政治革新势力。其子吴世昌,后流亡日本,入天道教,作为舆论焦点人物,即爱国开蒙阵营的指导者,活动频仍,引领一时。
这些动辄被朝廷高官训斥的译官、医官、诗人等杂科中人阶层,不能端居庙堂,把持朝政,但却是各个专业领域的王霸与开拓者——与其如许教授所说他们引领和主导了朝鲜时代的“文艺复兴”,不如说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们厥功至伟。而在朝鲜王朝末期,中人阶层活跃异常,向垂死的王朝政治发难宣战,成为革新图变的关键人物。
三
读罢许敬震教授《朝鲜时期的文艺复兴与中人》一书,对于我们了解与研究朝鲜半岛历史,提供了诸多的启示:
其一,就朝鲜时代出使中国的使臣而言,正使、副使和书状官皆为贵戚显宦,他们中有的非常愿意前往中国,有的却百般逃避,尤其不愿去已是“夷狄之国”的清朝。但如朴趾源、洪大容、李德懋、柳得恭诸人,多为庶孽出身,他们对中国充满了向往,如朴齐家称“仆常时非不甚慕中原”,“天性乃能自好中原”,因此希望自己一生能够有“真友真游”,除了饱览大国风光的因素外,就是因为中国士大夫嫡庶间无鸿沟之限,无论游宦神州,还是居处乡里,都是各凭本事,大显神通,平居宴饮,也无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尊卑之别,这种平等自由的空气,最为朝鲜半岛所缺乏,令他们艳羡不已。因此,他们往往以军官的身份,混迹于使团之中,就是为了到中国广交名士,“直欲仙仙轻举,飞落燕邸,望颜烧香,顶礼而返”。在这种愿望得到满足后,遂狂呼“今日始逢天下士,百年长作梦中人”,所谓“人生贵知心,百年当一日”。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在北京长长的抒了一口压在胸腔的抑郁之气,获得了理解和慰藉,得到了短暂的平等与自由。
其二,许敬震教授引用韩国学者的研究统计数据,称迄今为止得以确认的朝鲜时期的杂科合格者有6122名。其中译科有2976名,医科有1548名,阴阳科有865名,律科有733名。算学在杂科之外,合格者在1627名以上。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杂科的合格者413个姓氏中只有1名合格者的有一半以上。而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只有28个姓氏中才有1名的合格者。“也就是说,杂科已经被几个姓氏家族垄断。而被垄断的杂科职务又通过代代相传,强化了其专业性,他们为了这个特权也会采取相应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第427页)“中人身份阶层一般都是家族世代从属于同一个职业,这样也导致了他们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自己家族之间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职业上的既得权力”。(第102页)这意味着,中人阶层,虽然进入不了最高统治阶层的行列,但是他们却垄断了译科、医科、律科、阴阳科、算学、书画、乐坛与棋艺等,形成似铁板一样固化的中间层,他们貌似很难与贵族权贵阶层平等对话,或决一死战,但上至国王下至嫡族显宦的命运,却往往掌握在中人手中。比如燕行使团到了北京,往往是译官与中国通官勾结,行贿纳垢,买卖渔利,使行返国日期,一延再延,完全由译官说了算,正、副使与书状官不谙汉语,就成了瞎子聋子,任译官摆布,因此诸家《燕行录》中对译官的描述,基本上都是贪黩无耻之徒,这其中一半是事实,一半是嫡族高官们的抹黑与愤恨而已。
其三,如前节所述,到了朝鲜时代末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国王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面对洋枪洋炮,张皇失措,计无所出,唯有死守保命。但译官不仅出使中国、日本,还通向欧、美,他们带来了西风欧雨,吹响了改革号角。许教授总结,初期天主教中,中人和平民比重占有优势的原因,就是“南人学者从新文化运动已经转换为民众宗教运动了”。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朝鲜时期,译官的身份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较为狭隘,而在社会变革时期,因为他们的视野更为开阔,所以他们有能力发挥其主导性的作用”(第174-175页)。这个被压抑了数百年的中间阶层,终于喷薄而出,成了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不仅如此,还令我们感慨的是,在已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今日韩国,仍然能够强烈感受到传统政治与文化的反作用力与制衡作用。韩国仍然存在着贵族、中人与贫民的血统歧视,存在着强烈的地域歧视。韩国的民选总统自李承晚(1875-1965)以来,鲜有能终养天年者,这种明面上政治、文化与财团利益冲突的背后,仍然如幽灵般地存在着强烈的党争色彩,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朝鲜时代党争的别样表现形式与延续而已。
在《朝鲜时期的文艺复兴与中人》书中,还有一些断句标点之误与错讹之字。如“少选、幼选偕李君鼎运、沈君逵,使从者佩壶”(第32页),“少选、李涟川赤胄、睦余窝万中”(第34页),此两处的“少选”意思为“一会儿”“不多久”,而不是人的字号,应改顿号为逗号。又如“而小臣则不知针法。渠辈所言,如此故启之矣”(第203页),当断为“而小臣则不知针法。渠辈所言如此,故启之矣”。又“须速发,勿为逼遛也”(第232页),“逼遛”应为“逗遛”之误。又第428页注②“麟坪大君,名李氵窅”,当为“名李氵窅”等。凡此之类,书中尚有,希望在将来再版时纠正可矣。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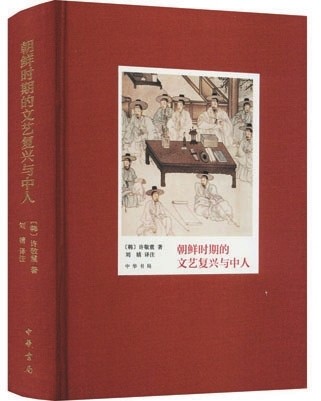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